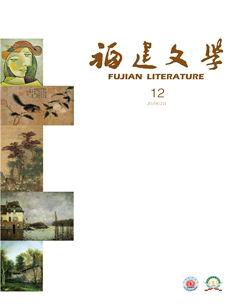乡愁时代(组诗)
高凯
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
——题记
火车站
村口
越来越大了
像村子自己撕开的一个伤口
长着一棵大槐树的村口已经绝迹
出去回来只有一个火车站
守着起点和终点
火车的尖叫
撕心裂肺 躺在脚下的道路
都是从城市奔往城市的冰冷的铁轨
离家的路上
每个人像一根硬硬的枕木
被铁轨一路枕着
而回家的路上
一个个就成了让铁轨一路枕着的
软软的枕头
运输乡愁的十万趟火车
在大地上来来去去轰隆隆轰隆隆
碾压着乡土的疼痛
白乌鸦
太让人惊奇了
终于有一群乌鸦大白于天下
在眼前一大片黑黢黢的文字里
我突然看见一群白乌鸦
飞来飞去
一只 两只 三只
一群命里就雪白雪白的乌鸦
因为没有背负一身沉重的乌黑
而飞得那么轻松快乐
甚至幸福
乌鸦原来不全都是黑的呀
或者黑乌鸦也有把自己变白的时候
我不是一只苦难的乌鸦
但我像乌鸦一样
为乌鸦兴奋不已
在文字的密林里
白乌鸦真实的白是那么突出
即使飞进深沉的黑暗中也是雪亮的
即使落在白皑皑的雪地上
也是雪白的
想起了补丁
周围身上长补丁的人
几乎没有了
从前
一个人从小到大从里到外
都是缝缝补补的
那些形形色色一块摞着一块的补丁
其实是生活留下的伤疤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为什么一想起补丁
里面就疼
心里长满补丁的人
还活在人世
乡间的吹手
过红事 终于笑出了声
呜哩哇啦的
过白事 终于哭出了声
也是呜哩哇啦的
看上去是在为别人又悲又喜
但心里 往往喜的是自己
悲的也是自己
人就活了一口气
一旦放开嗓子 一杆铜唢呐
和一杆铜喇叭都呜哩哇啦的
一个比一个痛快
阳世上的吹手
像每一家知心知肺的亲戚
贫富不嫌 一世放不下的大喜大悲
经那么呜哩哇啦一吹
就不知不觉放下了
那些能把魂儿都吹出来的吹手
身后几千年余音不散呢
山山峁峁沟沟洼洼
呜哩哇啦回响
关于手机
天下似乎都在掌握之中了
一部手机充满玄机
一串古老的阿拉伯数字
锁定了每一个人 小小的键盘
不通往过去也不通往未来
只通往现在
在自己的状态下活着
一个人会大声响铃或轻声响铃
或静音或振动 或已经关机
或不在服务区没有信号
咫尺之内一片盲音
凶险总是在悄悄逼近
深夜 一部突然响作的手机
就像一个暗藏杀机的特洛伊木马
杀伤一片宁静
身边的世界真实存在
但仍然有很多的人着魔地埋下了头去
孤独无依 致命的病毒就是这样
先死死咬住一个人的大拇指
然后才吃掉一个人
冬虫夏草
谁个在冬天里是一只虫子
夏天里就是一棵小草
谁个在夏天里是一棵小草
冬天里就是一只虫子
到了春天呢
到了秋天呢 两个对应的季节
虫子和小草各自去了哪里
谁个在春天里错过了春天
魂断秋天的又是谁
呀—— 今世怎么同根却不同命
夏天小草还把虫子藏了起来
冬天虫子就被吃掉了
核桃记
核桃有脑黄金之称
没有脑子的人和不会思考的人
男女老少都喜食之
核桃树粗枝大叶
但果实却心思缜密
个个高挂树枝 一旦成熟
必须以棍棒敲击
落地的核桃 外裹一层青皮
像一件厚重的寒衣 极其苦涩
扒去这层武装 又有一木质硬壳
似一个小小的人的秃脑袋瓜儿
有俗语以此喻人——
格格核桃砸着吃
一块完整的核桃仁极似人的脑回
仍是铠甲护身 巧手解下方可获得
但还要脱去一件米黄色的外衣
和一件贴身的白衬衣
总而言之
核桃树的生长是自己动了脑子的
每一个核桃都知道保护自己
在黄河流域
核桃树不计其数 而每一棵树上
又长了很多有思想的脑袋
责任编辑 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