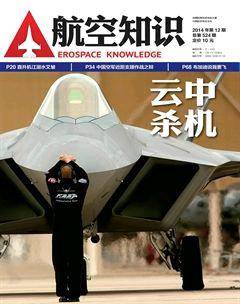一次试验与一颗药丸
邢强

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引发了美苏在冷战时期最激烈的对抗。在这期间,一个由14架超声速战斗机组成的编队跨越太平洋直奔美国本土加利福尼亚州,而另一个由13架飞得更快的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则试图横跨大西洋直取美国南卡罗来纳。这会是苏联方面派出的核打击力量么?
一次大胆的试验
答案是否定的,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场,这两个战斗机编队里面则都是美国人自己的飞机,他们正在执行最早的长距离跨海飞行航空医学生化试验。
飞行员在驾驶飞机(尤其是战斗机)时要在同一个身体姿态下保持精神高度集中。这种状态持续过久之后,就会产生疲劳。身心俱疲的飞行员对飞机状态的判断变得迟缓,对飞机的操控能力下降,为各种事故埋下了隐患。有报告指出,所有飞行事故中有五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地与飞行员疲劳有关。
为找出飞行员在执行长距离飞行任务后的身体变化规律并摸索出一套检测飞行疲劳程度的量化方法,美军831战术医院、乔治空军基地和美国航空医学院生理学分部等部门在1962年联合进行了一次航空医学试验。该试验由空军上校马奇班克斯博士组织进行。试验对象被分为三组。
A组有14名驾驶F-100战斗机的飞行员,平均年龄28岁,平均飞行小时数1 282小时。他们原本正在执行一项持续15天的飞行训练,计划从菲律宾群岛上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在关岛和夏威夷希卡姆空军基地短暂停留后飞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空军基地。马奇班克斯选取了这次飞行训练的最后一段航线来进行试验。
午夜0点,14名飞行员全部进入熟睡状态。早上6点,他们被叫醒,在希卡姆空军基地里准备了3小时后开始起飞。在4 250千米的航程中,飞行员们在狭小的飞行座舱内忍受了持续5小时45分钟的耀眼阳光,并完成两次空中加油任务,在东太平洋上空自西向东划出一条长弧线。F-100是美国空军“百字头”战斗机的首款机型,也是美国空军第一款能在平飞状态下进行超声速飞行的量产型战斗机。驾驶这种对舒适性要求不高的空优型战斗机进行长距离飞行并不轻松。从夏威夷到加利福尼亚的这段航线几乎整个都在东太平洋上空,直到降落前15分钟,飞机才终于见到了陆地。单调的舱外景象和炫目的海上阳光增加了飞行员的疲劳感。
B组有13名驾驶F-104战斗机的飞行员,平均年龄29岁,平均飞行小时数2 426小时,飞行经验几乎是A组的2倍。他们在西班牙执行了4个月的临时任务后,被叫来参加这场飞行试验。他们计划从位于大西洋中东部的亚速尔群岛起飞,飞越大西洋后降落在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默特尔比奇空军基地,在北大西洋上空自东向西飞出一条长弧线,航程4 534千米。
他们在凌晨3点起床,在亚速尔基地待了2个半小时后起飞。这些飞行员的睡眠时间大多比A组要短,有11名飞行员只睡了4个小时,只有2名飞行员睡足了8小时。在6小时的飞行中,他们进行了3次空中加油。脾气暴躁的大西洋让B组吃尽了苦头,飞行报告指出这期间有至少2个小时的天气状况极不利于飞行。F-104是美国空军第一款能以两倍声速飞行的战斗机。该机一改美军战斗机“结构重、装甲厚、马力强”的特点,开始走轻盈路线。让这种有着“寡妇制造者”和“人操导弹”之称的轻型战斗机执行跨洋飞行任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好在阴翳的大西洋夜空还没来得及给B组染上悲剧色彩,他们就已在阴霾散尽后的晨光中安全降落了。
C组是来“打酱油”的对照组,有12名战斗机飞行员。基地给他们放了一天假,以便他们执行睡个懒觉后起床随意逛逛的任务。
为了探索能够准确反映飞行员状态的生化指标,试验团队从三组飞行员身上采集了大量血液和尿液样本。检测项目几乎涵盖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生化指标,如钠钾含量、尿液酸度、肾上腺素、类固醇等激素的浓度。试验人员分析了机型、天气、飞行经验、任务前睡眠质量等多种因素对疲劳的影响,开启了用生化指标来测量飞行疲劳的量化航空医学时代。
一颗神奇的药丸
试验的组织者马奇班克斯博士曾经是美军第一个黑人飞行中队“红色机尾”的随队医生。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没有浪费掉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学习机会,在二战战场上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生。被认定为飞行疲劳测量理论创始人的马奇班克斯并不满足掌握测量疲劳的方法,他想要做到主动控制疲劳。他以首席航空健康专家的身份加入了阿波罗太空计划并参与了宇航服和舱内显示系统的设计。在1973年去世时,他留下了大量试验数据和呼吁消除种族歧视的文章以及一个没能研制出抗疲劳药物的遗憾。
不过这之后不到十年,能够对抗飞行疲劳的药物便已能在实战中发挥作用了。
美国海军安全中心统计了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飞行纪录,发现有300多起人为错误造成的A级空难均因飞行员在失事前24小时的睡眠不足8小时。于是,对抗飞行疲劳的药物开始集中应用在改善飞行员执行任务前的睡眠质量上。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爆发,英国飞行员要执行从基地到马岛往返超过1万千米的超远航程。在持续多日的跨时区飞行任务中,飞行员的生物节律被严重打乱,但英国皇家空军航空医学研究院提供的一种名为替马西泮的催眠药则保障了他们的睡眠质量和执行任务时的精神状态。
美军则采用了催眠药和兴奋剂联合应用的方案。1986年4月,美空军成功突袭了利比亚。这场军事行动发动得很突然,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们在14日下午接到消息后被马上要求服用司可巴比妥入睡。当天下午6点,他们被唤醒后马上投入到了长达13小时的飞行中,在完成了空中加油任务后,困意袭来的飞行员们立即服用了早就准备好的苯丙胺兴奋剂,药物使他们在较为亢奋的状态下完成了投弹任务并于15日顺利返航。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直接改变飞行员体内的生化指标来影响疲劳状态的药物开始走向成熟。法国Lafon制药公司研制的中枢兴奋剂莫达芬尼能够让飞行员长期保持精神高度集中状态。该药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首次应用在法国飞行员身上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服用该药后,飞行员能够保持48小时的持续清醒。这对处在敌后地区、危险丛林或广袤大洋等环境中等待救援的飞行员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后来,莫达芬尼作为遇险应急装备藏入了飞行员的座椅中。
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B-2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对伊拉克进行轰炸。这条航线需要B-2持续飞行35.3小时,对只有两名飞行员的机组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为了确保完成轰炸任务,这些飞行员大多都服用了一种名为右旋苯丙胺的兴奋剂。虽然在战争规模升级后,美军专门为轰炸机建立的基地让航线缩短了一半,大大减轻了飞行员的负担,但是在持续16.9小时的较短航线上,仍有97%的飞行员服用了被称为“神奇药丸”的右旋苯丙胺。
责任编辑:王鑫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