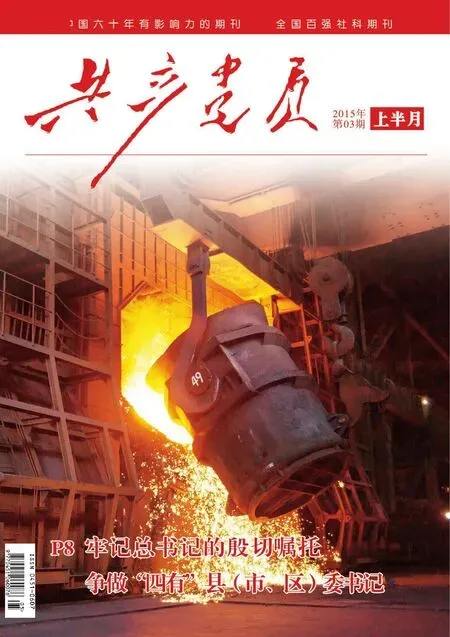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治理
文/杨菊华
出生性别比是一个简单的人口学指标,但其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时期面临的一个事关全局和事关未来的现实问题。其潜在后果具有极大的危害:可能威胁21世纪的全球形势,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主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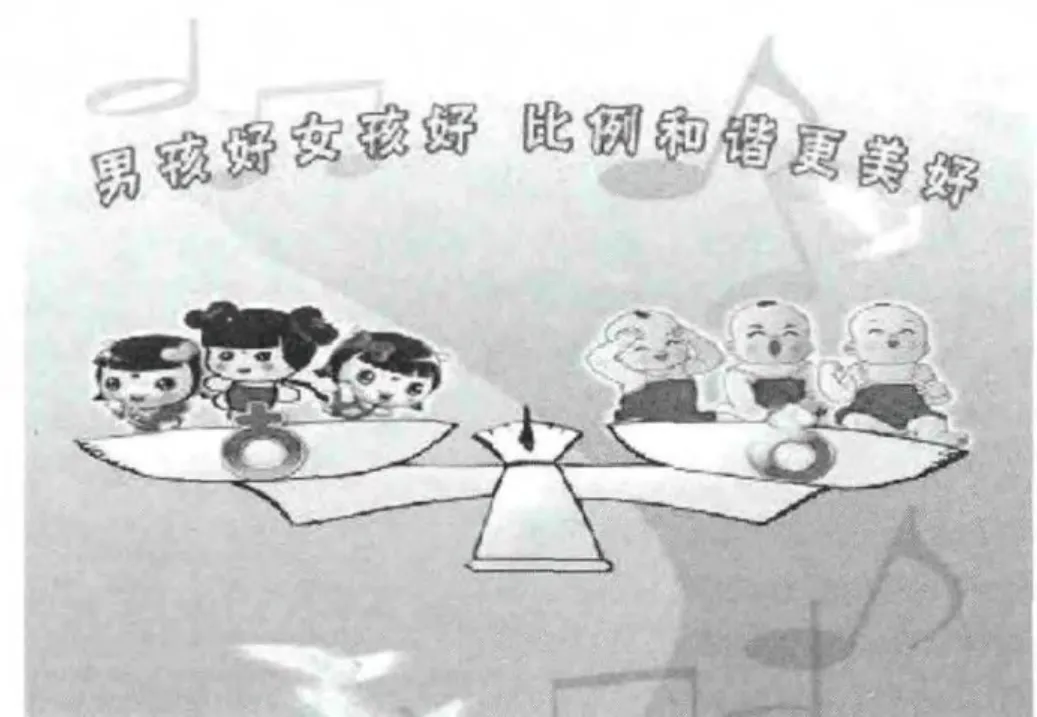
出生性别比反映新生儿的性别结构,通常是指在1年内,每100名出生的女婴总数所对应的男婴总数,正常范围大约是每102-107个男婴对应着100个女婴。虽然出生的活产男婴多于女婴,但由于男婴和男性青少年的死亡率高于同龄女性的死亡率,至结婚年龄段的性别比将大致平等,形成均衡的性别结构。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任何较大程度的与正常范围的偏离都暗示着某种形式的人为干预,也都将产生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
由于依旧强烈的男孩偏好,中国同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越南、印度等)一样,在生育观念转变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中国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该问题的国家,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失衡的程度之深在国际上都是独一无二的:1982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超过108,开始失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大大超出正常范围的上限值;尽管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治理措施,但2013年依旧高达117.6。
出生性别比是一个简单的人口学指标,但其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潜在后果具有极大的危害:不利于女性婚姻的稳定和安全,可能造成大量的非意愿性独身男性(即“光棍儿”),破坏家庭的生、育、养功能,增大家庭不稳定性风险,破坏人口的安全与发展,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一、男孩偏好、生育挤压、便捷技术与出生性别比。中国和他国的实践经验一致表明,出生性别比失衡源于三个要素:一是男孩偏好,二是生育挤压,三是便捷技术。其中,男孩偏好是本源性因素,生育挤压是催化性因素,便捷技术是可行性因素。虽然不同地区各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但各地学者达成的共识是,没有性别偏好(或性别偏好尚不影响生育行为),出生性别比通常不会失衡,即便技术可及、生育挤压等条件都有呈现;同样,当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上下且男孩偏好并未得到有效缓解时,出生性别比似乎总会失衡,已经失衡的比率也难以复归平衡。中国的情况因为严格限制性生育政策的存在而显得更为特殊:政策不仅带来生育挤压,而且暗含无意识的性别歧视或短视,故而使得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在各地区之中是最深的。
二、治理出生性别比的现实误区。缓解出生性别比就需要针对这几类要素,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既要堵住出口,也要掐断中间,更要疏导源头,而关键在于疏导源头。的确,针对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势,中国政府采取了综合措施,一方面严厉打击“两非”,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关爱女孩行动”等旨在保护女胎生命权、保障女孩生存权、促进女性发展权的多项措施,这些措施无疑是受欢迎的,且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的势头得到了遏制。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微降趋势。如果普遍的二孩生育政策能够得到推行,将不仅缓解生育挤压,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消除隐藏在1.5孩政策中的性别盲视,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降低出生性别比。
然而,虽然当前政府、社会和学界对出生性别比问题十分关注,但现存的学术研究、政府治理措施仍存在以下几大误区,从而降低了治理措施的效果:其一,从男性立场出发,忽视性别失衡对女性群体的不利影响。目前,在讨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时,主要考虑“失踪女性”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很少涉及该现象对女性及其家庭、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出生性别比失衡虽然是一种个人、家庭生育行为的选择,但它是社会性别发展失衡和两性文化发展失调的结果,可能进一步加深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弱势。不仅不少女胎的生命权被剥夺,而且反复的选择性流产还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伤害——出生性别比失衡牺牲的是女性的心理与生理健康;大量女性的缺失还会导致女性早婚、早育、性侵犯、家庭不稳定等不利于女性发展的后果;此外,男性多于女性等于间接增加了劳动力资源的供给量,加重社会的就业压力,可能打破经济秩序与格局,造成劳动市场的紊乱和社会不稳定,挑战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并最终冲击女性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地位的获得。然而,虽然有大量的研究分析、预测“失踪女性”将可能造成多少“光棍儿”,但该现象对女性的潜在不良后果却几乎没有深入研究。这一特点本身也表明,目前,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性别盲视,从男性本位视角出发,体现了男性中心和男权文化。
其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轻视从女性生命历程视角进行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虽然是出生之前的问题,但反映的却是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两性地位的失衡和女性权利的贫困。然而,虽然方方面面意识到从生命历程视角进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且也有所行动(如关爱女孩行动、利益导向),但目前的治理政策、措施、项目主要还是针对孕妇。但是,对个体和家庭而言,与儿子的有无相比,利益导向机制的效用十分有限;而且,随着教育“两免一补”制度的推行,对女儿户家庭的关爱亦显得微不足道;同样,随着国家养老保障政策的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补助也黯然失色。相反,在市场化过程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越发明显:就业困难、职业的性别隔离明显、“主内”的身份得到强化,等等,这些时时刻刻发生着的日常现象反复提醒人们,儿子比女儿好。因此,只有在生命历程的全过程中两性地位趋于平等,男孩偏好才可缓解,出生性别比也才有望回归平衡。这意味着,失衡的治理措施必须着眼于整个生命历程。
其三,从政府和学者的视角出发,忽视妇女及家庭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后果的认识。目前,不管是学术研究、国家干预项目,还是基金支持项目抑或是其他项目,多是从学者、政府或社会的立场进行,所言所做的都是非直接当事人认为是对的东西,难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实际上,群众对未来可能有多少“光棍儿”并不关心,更不认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和儿子的婚育。
我们在多个地点的定性访谈中发现,不管是妇女还是家人,都没有人认为男孩多了会有问题。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没有意识到婚姻挤压问题。部分被访者的儿子很小或将要生孩子,当下只是希望家里添上男丁,娶妻之事太过遥远,尚未考虑,也不知婚姻挤压问题。二是虽然知道男孩比女孩多,也听说过婚姻挤压的说法,但不足为虑。部分人认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年轻人接触的圈子大了,找对象的机会也就多了:外出打工的男孩可以从外面带媳妇回来,去经济稍差的地方找(如山区),或去国外找洋媳妇。因此,他们亦未将娶媳妇之事当作是难题,何况现在人们看到的主要是“剩女”而不是“剩男”。三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们多从家庭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认为孩子个人条件(如长相、学历、未来从事的工作)和家庭经济条件(如给即将娶妻的孩子盖一幢像样的楼房或者去城里买一套商品房、置办像样的家具)才是能不能找到对象的关键。只要这两个条件都好,儿子就不会娶不到媳妇,娶不到媳妇之事“落不到自己儿子头上”,无需担心。“找不到媳妇?怎么可能?只要我儿子优秀,哪能找不到媳妇呢?”
三、治理出生性别比的有效出路。为更有效地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除继续推行现有项目外,还须针对上述困境,采取相应的措施。
其一,加快成果转化,唤起人们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对女性及其家庭的潜在危害的认识。
其二,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项目,关注女性的终身发展。
其三,拓宽宣传视野,纠正目前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后果认识的误区。最后,调整生育政策,取消1.5孩政策以头胎的性别为二孩生育条件的限制,消除政策的性别短视与盲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