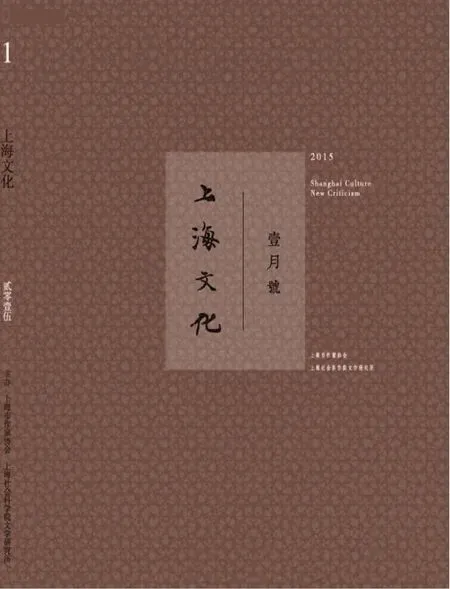德日进与中国
魏明德
德日进与中国
魏明德

命运之旅:从法国中部到中国天津
德日进在中国的每一项探索都是寻向根源的探索:地球的生命之源、人类的进化之源以及人类看待自身历史的意义之源
克莱蒙费朗市(Clermont-Ferrand)位于法国中部奥弗涅(Auvergne),该区地处古生代形成的火山地带与海西褶皱高原。法国作家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论及自身在奥弗涅花岗岩高原上郊游时,如此写道:“这几乎是一次很神秘的旅程,踏上通向沐浴神光的心灵小径。在奥弗涅这片恒远的土地上,在古老月光曾经照耀的法兰西心脏,我找到了我的第二个故乡。”这里就是德日进1881年5月1日出生的地方。家里十一个孩子,他排行老二。母亲是伏尔泰妹妹的曾孙女,父亲是一位酷爱学习的乡绅农场主。
仿佛正是奥弗涅的峻峭风光滋润了形上学的禀赋:在德日进之前,17世纪初期,帕斯卡(Blaise Pascal)也在这里诞生。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兼数学家曾经对两个“无限”做了冥思观想,人类无可避免地在这两个“无限”之间摇摆:
让人类认识那些最细微的东西吧!让微小的寄生虫让我们学习到一枚微小身躯的各个部分吧——双腿的关节,双腿里的血脉,血脉里的血液,血液里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里的蒸汽。把以上事物再加以分割,让人类在这类概念上竭尽能事吧!让人类所有可能达到最后的东西作为我们现在讨论的对象吧!他或许会想,这就是自然界中微小的极致吧!我要让人类从中看到新的深渊。我要向人类描述的不仅仅是可见的宇宙,而且还有人类从原子略图的基础上所构想的自然无限性。让人类从中看到无穷的宇宙,每个宇宙都有其自身的苍穹、行星、大地,其比例和可见的世界一模一样。在每个大地上也都有动物,最后也还有寄生虫,人类将发现都和初始的生命一样。人类更在其他向度发现无穷无止的事物,让人类在渺小如同巨大一样惊奇的奇迹里面迷失吧!因为谁能不赞叹我们的肉身,有时它在宇宙中令人无法察觉,它自身在全体里面无从觉察,现在却因与我们无法到达的虚无相比,瞬间成了一个巨灵、一个世界,或者不如说成了一个全体!
许多年以后,帕斯卡的同乡,德日进在“极大”及“极小”这两种无限上,增加了第三种无限的反思,即繁复之无限。
物理学到现在还只是在两种无限上兜圈打转。可是如果我们要在科学上涵盖经验的全部,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去端详、琢磨宇宙中另一种无限,与其他两种无限一样的真实存在:我所说的就是繁复性这种无限……为什么不在原则上说明意识就是质料状态的独特属性,就是那种卑微价值观引导下难以觉察且容易忽视的属性,但在繁复性这种高尚的价值观引导下逐渐显现并最终决定一切的属性呢?
像前辈帕斯卡一样,孩提时代的德日进既醉心于自然科学,又迷恋人类命运的谜团:人终一死这项宿命让他苦恼不安,因此他收集着石块、铁块这类坚硬的东西。即使周遭东西不断变化,然后最终迈向衰亡,他仍面对上帝的奥秘中的永固永存性。1901年,德日进决定要去普鲁旺斯省爱克司市耶稣会初修院时,家人一点都不觉得诧异。当他转向宗教研究的领域时,他方能继续探索并调和科学以及灵修两个维度的综论。
初修结束之后,他去了靠近诺曼底海岸的泽西岛(Jersey)学习哲学,后来又被派往埃及从事教学三年。在那里,他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啊,多么炫目的东方,透过它的智慧、植被、百兽、荒漠,让人贪婪地品尝、欣赏这种美妙。”
埃及之行以后,他前往英国学习神学。时间、人必有一死、世界及万物之转化,这些他从小早已投注热情思索的问题使他转向研究柏格森(Bergson)的哲学,柏氏对意识如何感知有许多深入的研讨。与此同时,德日进对于古生物学,这种着眼于大地的时间绵延,而不是定位于人的绵延的方式越来越感兴趣,后来便成为他的科研专业。不过,德日进拒绝把自己拘囿于某个单一领域,他集科学、哲学以及神秘之学于一身。
1911年8月24日,德日进晋升为司铎。随后他回到巴黎,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师从马·蒲勒(Marcellin Boule)教授学习地质学。1913年,他与考古学界的伟大先锋布鲁耶院长一起实地考察了西班牙西北部的史前洞穴壁画。随后爆发的世界大战,打断德日进的科学事业。他被征召入伍,成为一名担架员,在战地呆了四年,由于表现英勇而先后被授予荣誉奖章及军事奖章。同大多数人一样,战争大概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思想转变,使他思考了“荒谬”,也让他产生了对人的失望。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面对荣誉和无意义,德日进选择去相信人类的能力,相信物种的精神进步,相信它们可以超越一切:“我不得不承认,谜样的自我喜爱执着地往前迈进:投入探险与研究的‘我’,朝往世界的极限,为了取得崭新而难能可贵的眼界,为了陈述何为‘超越’。”
正是因为身处这样吊诡的体验,他勇敢地写出以下的字句:
历经漫漫长年,地球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生命表征;然后又是一段天荒地老,地球只是在自己坚硬的或者水溶的表面一层组织化质料层中显露出自发性或者无反思意识的信号。最后,在较为晚近的岁月里,自发性和意识终于在地球上人类生命圈里取得了追求独自发展和个体独立的特质。人知人之知;人在行动中出现了,又在一定范围内把握行动,虽然范围不是很大。于是他可以抽象思维,引申归纳,最后预见未来。
战争结束后,1922年德日进在索邦大学济济一堂的阶梯教室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地质学论文答辩,随后他在巴黎天主教学院任职,教授地质学。此时的德日进四十一岁,是耶稣会士,博学饱读,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这时候,他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开始了,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他写了一篇关于原罪的论文,这篇论文大概使圣经叙事的史实性遭到了质疑,并且表现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好感。为了避免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恶化,耶稣会法国省只好指派德日进前往中国进行科学考察。1923年4月10日,德日进在马赛港启程前往天津,多年的流浪开始了。而此时,他还不会想到这次流浪时间持续之长,竟会贯穿其整个后半生。
德日进拒绝把自己拘囿于某个单一领域,他集科学、哲学以及神秘之学于一身
火焰与宇宙:综合思想建立灵修体悟
德日进的姐姐之前在上海当修女传教,后不幸在沪早逝。德日进在北上途中下船扫墓,并祈祷姐姐在天国之灵赐予他力量和勇气。德日进与其他大多数耶稣会士不同的是,他来中国并非出自本意,他不是另一位利玛窦神父。德日进对他的中国科考工作同事殷勤有礼、关心有加,他用英语和他们交流,不过从没有学习过汉语。他认为自己身负科考使命而无暇他顾,但他在内心里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天津德日进必须配合桑志华(Emile Licent)神父工作,后者是一位旧时代的传教士,他的坏脾气众所周知。1914年他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地质博物馆,即黄河白河博物馆,又称北疆博物馆,就是今天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为了丰富馆藏,桑志华神父在一年内跋山涉水,行程达三千公里之远;为了博物馆的安全,他在馆建筑周围安装了倒钩铁丝;睡觉时枕边也备有左轮手枪,防止小偷溜进来……德日进和桑志华性格截然相反,两人的合作难以协和,但桑志华的安排使得德日进有机会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进行一系列的考察活动。
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开始了他们的探险考察旅程。他们第一个发掘目的地位于宁夏银川六十公里外的水洞沟,直到今天,这里还进行着相关的发掘研究工作。一个月后,他们骑驴到达了三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谷,他们在那里让一大批化石和打磨石器得以重见天日。也就是在鄂尔多斯沙漠里,德日进写下了他诸多神秘主义色彩作品之中的一篇《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La Messe sur le Monde)。没有饼和酒,德日进无法每天奉献弥撒,可是他不忘向天主奉献弥撒。于是,他身处的高原就成为他的祭台,全宇宙的物质就是他向天主敬献的祭品:
在那里,在地平线上,太阳的光芒刚刚从东方的天际绽露,又一次,在这团运转的火球下,充满生命力的地球表面慢慢苏醒,晃动起来,再次开始其令人敬畏的艰辛劳动。噢!我的主,在圣盘内我要放上这新的一天劳动所得的收成;在爵杯里,我将注入所有今日自大地的果实所榨取的新鲜汁液。我的圣盘和爵杯是一个向所有力量开放的灵魂深处,那些力量即将由地球每个角落飞扬升起,汇聚于圣神。愿新的一天光明所唤起的人们,愿他们的记忆和他们本身的神秘存在来我这里!
德日进深入了沙漠腹地,也就是在沙漠深处,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思想的“火焰”给活体质料赋予了灵性生命。
好了。又一次,火进入了大地。……
它没有像雷电那样霹雳地烧向树端。主人回家需要破门而入吗?
无震撼、无雷声,火焰从内到外照亮了一切。从最微小的原子之核心到最具有普遍性规律之力量,它如此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我们宇宙的每个元素、每支发条、每处连接,以至宇宙好像自燃起来。
(……)
主啊,我的全部喜悦,我的成功,我生存的理由,我热切活下去的期望,在您贯穿宇宙的视野下是那么无足轻重,不足挂齿。让权高位重的人来钦服赞叹您伟岸无边的纯粹精神吧!至于我,我与生俱来的心弦召唤着我,包围着我,我只想,我也只能说是您的存在的化身通过质料一望无际地无限延伸;啊,天主啊,我也只会说在我们周围一切身上浮现的是您的伟大肉身。
德日进透过大地之火的意象传递灵修情感,正是巴黎赛伏尔大学教授马德南(Henri Madelin)描述德日进透过综合思想所建立的伟大原则:
我想强调的是德日进是个具有综合思想的人。德日进所建立的伟大原则,我们可称作阿尔法与奥米茄原则。奥米茄,也就是人类的终结,德日进称为奥米茄点。奥米茄总结前面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就是综合万事万物原本具备的所有特性。但是,德日进伟大的论点也谈到,若没有阿尔法存在,我们无法理解奥米茄。而在阿尔法之中,早已蕴藏通向奥米茄的种种。换句话说,奥米茄证明阿尔法确切属实。而最伟大的验证就是物质与精神,但是他对物质与精神不作出区分,因为他透过圣歌赞颂物质。在物质内部,在原子内部,在粒子内部,已经存在着综合原则的作工。
德日进从鄂尔多斯沙漠神秘旅程归来之后,于1924年10月返回法国。但他从他的上司那里得知他的思想极不见容于罗马教廷,而是否该回到中国,埋头自己的科学工作,他游移不定。这让他遭遇了一次精神危机,而被这个难题纠缠了数次:他是不是应该离开耶稣会独自工作呢?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人应该在既定的位置上继续工作,好比宇宙中质料的原子并不否定自身的位置和标的,此时他遇到的阻力比他当初离开时还要强烈,他自己所属的教会也深受这种阻力的影响。因此,1926年4月5日,他再次启程前往中国。
1927年,经过了几次精神危机的考验之后,加上在中国这个他居住国家的启发,他完成了自己灵修思想之作《神的氛围》(Le milieu divin)。德日进的坚定信念,在于宇宙的意义渗入人类骨髓,它最终将转变人类,使得人类合成为一。他这种宇宙意识的关照让人觉得与神秘的道家某些直觉观念有些神似。
我将宇宙精神称之为或大或小的“亲合性”(l’affinité),这种亲合性让我们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相互连结。亲合性这种情感的存在毋庸置疑,并且它比思想的起源还要古老久远。自从人类面对山林水泽、江河湖海、日月星辰之下的那一刻起,宇宙精神即刻诞生。从那一刻起,宇宙精神的痕迹展现在我们所感知的一切伟大又难以定义的种种事物中,例如在艺术、诗歌,乃至宗教信仰中。宇宙精神让我们对感知世界的统一性作出回应,正如我们用眼睛感受光亮一样……同样地,在物质的最下限,科学向我们揭示出一种不断释放的能量,从中产生出万物;而在圣神的最上限,我们会发现有一处神秘空间,在那里一切沐浴神光,聚合为一。
科学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确认工作
频繁的舟车生活,加上内心精神危机的起伏激荡,让德日进的生活纷扰不定,但是这些纷扰的日子却是德日进科考事业决定性的一段时期。他受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担任名誉顾问。从1926到1935年,他参与了五次中国地质考察;通过这些考察,德日进帮助中国政府完成了第一幅完整的中国地质图。
周口店地处北京东南方向四十二公里,1921年起瑞典地质学家安德森(J.G. Anderson)在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此处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古人类的牙齿,1929年10月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又发现了一块完整的人头盖骨。这些发现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使得早期人类的年代学重新被讨论。“北京猿人”又称为“中国直立人”,生活在距今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之间的更新世中期,他们掌握了火的使用,也使用了大量的打磨石器。随后,关于这些发现研究的确认工作,德日进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931年,也就是他五十岁那年,他确认“北京猿人”是“Homo faber”。
1931年到1932年,享有一定声誉的德日进以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雪铁龙公司(Haardt-Citroën)“黄色远征”(croisière jaune)中亚之行。他在北京西北方向的卡尔甘加入了远征队中国组,该组最后在阿克苏与帕米尔组会和。在乌鲁木齐他与几个朋友停留了几个月。在吐鲁番他给朋友写了如下这封信: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蛮荒寂寥之地。自从进入新疆省的地界以来,视野是越来越辽阔无边了。我坐在书案上,向外眺望,目光越过吐鲁番绿洲的杨柳树林,一直可达天山山脉的东部延伸段,那就是白皑皑高耸的博格达雪岭。真是美不胜收啊,让人喜出望外的还是当我们知道这片地区是历史学与地质学的圣地时,真是太激动人心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虽然中国的政局不稳定,但德日进还是进行了多次的探险考察,先后到长江流域、四川、广西、广东等地。他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做考察,如1928年他去埃塞俄比亚,1935年去印度,1936年去爪哇,1937年去缅甸……从这一连串的考察旅行之中,德日进组织了一个国际性探险队网状组织,使得德日进继续考察东亚大陆……
召唤未来:思想从磨砺走向成熟
1937至1938间,德日进回了一趟法国,这时候他不幸患病,情绪低落。这期间,他从上司那边得知他还是不怎么“受欢迎”,他调和基督信仰与进化论的努力还是没有得到理解和认可,当局还是不允许他谈论神学问题……为此他十分痛苦,多次忧郁症病发到极点。与此同时,他的手稿大量转抄流传,虽然教会始终禁止刊行,在年轻一代的耶稣会士中却反响热烈。德日进实际上促进了另一种理解基督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向宇宙思考开放,并连接了当下开拓的科研工作,也与其他各洲陆的灵修来往交相辉映……德日进的耶稣会朋友纷纷鼓励他,劝慰他。德日进终其一生朋友众多,男性和女性的友谊环绕着他,彼此书信往来不绝。
1939年德日进又回到了中国,此后他一直留在北京,直到1946年。他挽救桑志华神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品,并与他的朋友耶稣会士罗学宾(Pierre Leroy)神父共同创建地质生物研究所。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并且完成重要著作。德日进从没有放弃自己作品的思辨,他绝对不是在纯粹的科考工作中逃避隐逸自己。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完成大家公认最重要的作品:《人的现象》(Le phénomène humain)。可惜的是,这部作品直到他过世之后才得以出版。
该作品描述的是物质演化延续过程中“人的现象”的出现,以及关于地球上生命的出现这两种现象的恢弘画面。
反省是意识反思自我所获取的一种力量,自我掌握,就好像掌握物体的坚实性与特殊价值。不只是认识,而且也是认识自我;不只是知道,而且是知道人们知道的事物。
但是,问题还是必须探究所谓的“人的现象”如何召唤未来……
直到现在,对于人,我们只认识人的个体架构,即藏有千百万颗神经核的肉身躯体。但是人,也就是一个具有自我的个体,相较于新而高层次的综论,难道不是代表着某种元素吗?我们认识了原子、原子核、电子、分子、原子核团、细胞、分子团……我们的未来,难道不是寄托于成形的人类,一个有机体的总和吗?反思存在,通过回头自我审视,它随即寄望于一个新的空间里自我发展的可能。实际上,这正是诞生了另一个世界……人类在以松散的社会化组织形式布满地球之后,它自己也便在以一种不断加速的节奏向自身收敛……“爆炸式的世界”,今日人们如此思考,也如此表达。但为什么我们不以更准确的角度,说明这是一个收拢聚合、一个向内反省的世界呢?
这也是在不稳定中保持平衡的世界,因为世界正在移动。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一些人称德日进为“全球化的先知”:
朝向地平线成熟的临界点正快速增加,人类将因此达到世界极致。若我们要给与“经验”一个意义和连续,朝往这个方向将不可避免地最终面对地界思想的出现,我称之为奥米茄点。
对德日进而言,所谓奥米茄点,就是在所有对物质的努力所得之收获之中,在自世界开始的人类和生命之中,人类(或者人性)在此点与共同思想中收拢为一。这也是时间终结之时基督出现的景象。基督像田野里的篝火一样照亮世界的内心。这样的视野推展不间断的对话,不间断的对话滋养科学家与信徒的内心深处:
透过教育与知识学习,我学习当一个“上天之子”,但是透过心性与专业研究的熏陶,我变成一位“大地之子”。置身于两个我熟识的世界中心,置身于熟知的体验、理论、语言、情感,我体会到无止境的内在。但是我让两股相异的力量在内心深处自由地相互影响。然而,历经三十年投注于内在合一的旅程,我感觉到两股力量自然而然运转并形成综论。一股力量并没有摧毁另一股力量,两股力量反而相互巩固。今日我更加相信上主,而且甚于世间。
《人的现象》这本书写作时间涵盖德日进在中国的整个驻留期,即1922年到1946年间。在这期间他还不时离开中国回到欧洲,同时也去了亚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最为关键的就是,在中国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考察探险这段时间里,穿越沙漠和河谷追寻生命和人类痕迹的考古发现这一过程之中,德日进的思想走向成熟。他所到之处形态各异的风景以及各式各样的文明都给了他思想充足的养料。虽然他肯定没有深入这个国家的人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中去接触他们,也没有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他仍然感觉到这里的人民内心深处暗藏着人类神秘和普遍精神,他由此看到在形成的生命大乐章的线谱占有一席之地。1927年,他在给他的朋友爱德华·勒鲁瓦(Edouard Le Roy,数学家和柏格森派哲学家)的一封信中就这么评述当时的中国政局:
我正目睹着一个巨大的人类转型过程在一片广袤无边的大地上铺展开来。但愿这样的转变不致使得东方与西方之间迈向分歧!。
1940年代,他经过多次的会遇与发现,他在上海向记者克劳德·里维亚(Claude Rivière)吐露:
对我而言,中国成为收养我的国家,高度认可我的国家……中国巨大形象的国度,延伸、滋养我的思想,直到星球意识的向度。就科学的层次而言,我在这里找到工作与探索的初始地。来到中国,我才能完成北京猿人的考古研究。因此我有各种理由爱上这个国家。
复活节之愿:无所住的神秘派基督信徒
德日进的晚年岁月过得格外艰辛。1948年的罗马之旅并没有解决他与罗马教廷之间的问题。随后,病痛首次阻扰了他的南非考察计划,直到1951年才得以成行。同年,他最终到美国定居,任职于一家古生物学基金会。他于1955年4月10日复活节那天逝世。八天过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死于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比德日进早两年出生。爱因斯坦的贡献对后世来说史无前例,他和德日进的探索显示出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与思想的行进。
德日进过世前一年曾经向他的朋友们诉说了他的愿望:“我多么希望我是在我主复活的那一天死去啊!”
他整个一生都感觉到神圣的能量在每一种事物之内发挥着作用,他努力去确认这个神圣能量的完成度,后来他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健康的恶化,因此在去世前不久他曾经这么写道:
我的上帝啊,我感觉到我自我完备的同时,也增加了您在我身上的牵引,在努力的过程中的感觉多么温暖……今天,我的时刻来临了,就是认识您各种不同威力的时刻,每一道威力都是陌生或有敌意的,看起来将摧毁我、排挤我……对我而言,未来的前方越像是眩晕裂口的幽暗通道,假使我冒险追随您的圣言,那么我越是有信心交付给您,不论迷失或沉于深渊,被耶稣基督您的肉身所同化。
终于,在“神圣的中界(中项)”之中,德日进也加入了眩晕的终极下沉之旅,通向生命的涌泉:
从此,或许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虽说我每天默想)手提着灯,离开那看来光明的日常职务的层面或与人来往的关系中,第一次降到自我的最深处,进入一个我感觉我行动的权柄所迸射的深渊里。当我愈离开大家惯常以为明确、表面照得通明的社会生活时,我才发觉我失去了与自我的联系。每往下走一步,内在就出现另一位人物,我无法用确切的名字叫他,他再也不听从我的指挥。当我已前无去路而只得停止探索时,在我脚前出现一个无底深渊,从那里涌出一股不知来由的、我称之为生命的洪流。
另外一位耶稣会士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曾就神秘主义提出有名的定义:“神秘主义者就是不能停止往前的男性或是女性,神秘主义者知道手上无法掌握何谓确定,知晓每个地点以及每个东西都不是实相,人无所住,而且不能以此自足。”米歇尔·德·塞尔托曾多次强调,神秘主义者是“站在侧边”的人,瞬间置身在众多机构的边缘,但是边缘会将他自身推向新的空间。由此看来,德日进无疑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不仅在空间中游历,而且跨越不同学科,跨越内在的迷宫,同时他也在地球历史的洪流中与生命的乍现中游历。另一个说明他何以如此亲近往昔神秘派基督信徒的特色:他年轻时就进入宗教体系,虽然历经内部制度的刁难,但从来不曾离开过自身所属的宗教体制。他证明他有能力生存于体系的内部,而且保有自身的自由。他的自由借着文章的撰写以及不间断澄清自身的立场传达而出,但从来未曾导致任何严重的冲突。他明了体制运作的困难,不曾试图挑衅,但是他不会因此囚禁自身的极限。迈向高峰的路途需要脚踏实地、自我平衡的能力,以及过人的胆魄。随着对中国空间与时间的探究,德日进踏出并实现每一趟充满平衡与胆识的远行。
❶Julien Gracq,LeGrand chemin,Paris,José Corti,1992,81页。
❷《思想录》,Br.174,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
❸Oeuvres de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Paris,Seuil,1955-1976,t.11,183-184页。
❹《La nostalgie du front》,septembre 1917,in Écrits du temps de la guerre(1916-1919).Paris:Grasset,1996,201,205页。
❺Oeuvres de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t.3,Seuil,227页。
❻圣盘和爵杯专指神父在弥撒中所用的礼器。
❼❾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La Messe sur lemonde”inOeuvresdePierreTeilhardde Chardin,t:13,17页;17-20页。
❽参见《若望福音》十1-2:“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不由门进入羊栈,而由别处爬进去的,便是贼,是强盗。由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⑩魏明德与张俐紫(导演),《德日进与中国》纪录片,2014年,22’56-24’23。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