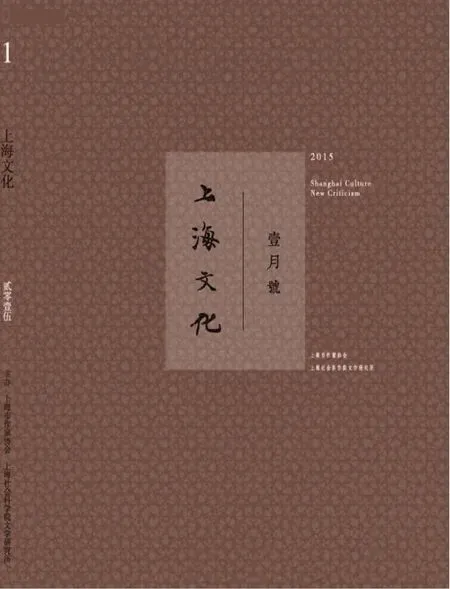徽章的力量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项静
徽章的力量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项静
一
每一个人之于这个“全世界”来说,都是飘荡的碎片,但它们拒绝成为漫长而有教益的人生故事
张嘉佳铺排华丽而揉捏到位的文艺腔调,孤注一掷坦白给世界看的风格,废话流般让人没有喘息空间的语速,让我们在集体妄图现实主义的焦虑中放了个风。如果我们把张嘉佳的作品称为小说,小说的本体论人物就在于为我们重新找回昆德拉漂亮地称之为“生命的散文”的东西,而“没有任何事物像生命的散文如此众说纷纭”。
一旦被列入生命的散文这样宽泛而没有现成章法的体裁,就会发现张嘉佳的小说世界也是丰满而又诱人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一部后青春回忆录,是一部掺杂了七情六欲的青春奏鸣曲,他的“全世界”从作品来看,就是爱情、青春、友情、游历、放荡、豪迈、不羁等等,形形色色的主人公到处串场,转身却又不见。有温暖的,有明亮的,有落单的,有疯狂的,有无聊的,也有莫名其妙的,还有信口乱侃、胡说八道的,每一个人之于这个“全世界”来说,都是飘荡的碎片,但它们拒绝成为漫长而有教益的人生故事。
迈克尔·伍德在论及昆德拉的小说人物时说,不管在小说里还是小说外,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需要对我们而言是否真实,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他们的人生。所有令人难忘的小说人物,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历史的片段,是搜集起来用语言重新创造的历史的片段,所以他们像我们见过的人,而且比这更好的是,也像我们还没有见到的人。
“他们的需要对我们而言是否真实”这个标准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用毛姆的话说,可能就是人物的个性。他们的行为应该源于他们的性格,决不能让读者议论说,某某人决不会干那种事的,相反,要让读者不得不承认,某某人那样做,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次,还是一个“他们是怎样的人”与“他们是谁”之间的差别,很多专注内心的小说一直缠绕的问题是他们是怎样的人,而有纵深感觉的小说才会关注他们是谁的问题。张嘉佳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怎样的人?我们可以简单组合一个群落:他们有过微时的落魄,他们说着废话流抵御着生活中的那些伤害,分手或者离婚;他们有过赚钱的幻想,被打击了之后沉迷于游戏;他们爱着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姑娘,用全部的心血和热情,但有的成功共同回忆往事,有的失败完成自我成全;他们爱着自己的狗伙伴梅茜,他们知道不是狗离不开他们,而是他们离不开那只狗;他们爱着那些消失了的人:姐姐或者某个让你心动的姑娘;他们离开脚下的土地,去放开那个被捆缚住的自己。他们是一些面目不甚清爽、真实生活着的青年人,他们的生活因为张嘉佳的叙述而有了一种戏剧性,但万宗归一,他们就是《那些细碎却美好的存在》中玄虚而言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存在者,“不想那些虚伪的存在,这世界上同样有很多装逼犯,我偶尔也是其中一个。如果尚有余力,就去保护美好的东西”。
如果所谓的“历史”是重大事件的话,这一代人几乎没有进入过“历史”,张嘉佳不是去复制经历过的生活,而是来营造一种与其说是差强人意的历史感觉,不如说是一种熟悉感。世纪之交的这一段时间,异地恋的校园电话卡这种时光渐逝的见证物,初恋的兵荒马乱的情绪,还有那些具体而又潜藏着共同记忆的生命中的时间,制造了一种熟悉感——比如“1999年5月,大使馆被美国佬炸了。复读的我,旷课奔到南京大学,和正在读大一的老同学游行”;“2000年,大学宿舍都在听《那些花儿》。九月的迎新晚会,文艺青年弹着吉他,悲伤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去呀,她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2001年10月7日,十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战胜阿曼,提前两轮出线,一切雄性动物都沸腾了,宿舍里的男生怪叫着点燃床单,扔出窗口”;“2002年底,非典出现,蔓延到2003年3月。我在电视台打工,被辅导员勒令回校。4月更加严重,新闻反复辟谣。学校禁止外出,不允许和校外人员有任何接触”(《末等生》)。
他们像我们见过的人,而且比这更好的是,也像我们还没有见到的人
接下来一个更需要追问的话题是,而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可能是来自东北的一个姑娘,可能是江苏的某个小城市男孩,与当代中国电影电视剧中的小镇青年面目相似。他们所归属的是城市的中等阶层,如今他们有着不错的收入或者还是一些来历不明无需确证的富二代,他们能够转身就离开困境,下个决心就能去周游世界。比如在《骆驼的姑娘》中,朋友失恋了,就可以劝他,老在家容易难过,出去走走吧。他点点头,开始筹备去土耳其的旅行。这不是一个普通凡俗的人可以拥有的选择,他们非常便利地追寻和享用旅行的意义,“意义不是逃避,不是躲藏,不是获取,不是记录,而是在想象之外的环境里,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从此慢慢改变心中真正觉得重要的东西。就算过几天就得回去,依旧上班,依旧吵闹,依旧心烦,可是我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就算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至少,人生就像一本书,我这本也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美景和美食》)。他们笃信“美景和美食,可以抵抗全世界所有的悲伤和迷惘”(《美景和美食》)。
张嘉佳的叙述是直白而坦诚的,这些人在流行文化中长养着,并被流行文化塑造了人生和世界
张嘉佳作品中的人物基本都接受了大学教育,无论对这个制度是嘲讽还是无动于衷,他们基本都坦然接受了大学教育。除此之外,看不到更多的明晰的文化背景,或许从小说中人物的自我“坦白”可以瞥见某种端倪。《旅途需要二先生》中提到过早年看的《大话西游》和美国公路片,和泪共唱的《一生至爱》。《河面下的少年》中则有一大段关于我们青春的排比堆砌的各种流行文化符号,“我们喜欢《七龙珠》。我们喜欢北条司。我们喜欢猫眼失忆后的一片海,我们喜欢马拉多纳。我们喜欢陈百强。我们喜欢《今宵多珍重》。我们喜欢乔峰。我们喜欢杨过在流浪中一天比一天冷清。我们喜欢远离四爷的程淮秀。我们喜欢《笑看风云》,郑伊健捧着陈松伶的手,在他哭泣的时候我们泪如雨下。我们喜欢夜晚。我们喜欢自己的青春”。张嘉佳的叙述是直白而坦诚的,这些人在流行文化中长养着,并被流行文化塑造了人生和世界,它们是这一代人的文化基础,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基础,也是他们情感共同体的入场券。男欢女爱的模式,对情感的态度,还有自我解脱的方式,戏谑而无奈的语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种流行文化的滋养。
张嘉佳的作品不是这个时代的孤例,可以推而广之。韩寒的一个APP,他新拍的电影《后会无期》;新媒体上的非虚构写作“记载人生”、“果仁小说”等;写《谁的青春不迷茫》、《你的孤独,虽败尤荣》,以“坦白说”作为口头语和个人标志,分享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捕获大量在校生拥趸的刘同;《最小说》中厉害的写手安东尼,写作从来不加标点符号,擅长从平淡生活中发现闪光点,捕捉生活小情趣,笔下文字自成一统,充满童话梦幻色彩。他们都可以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归为同类。如果从“同时代人的写作”最表面的意思来看,他们的确是在制造一种半径最大的共同体情感,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爱恨情仇,我们的粗糙与不经,不悔与悲壮,寻找与迷茫。刘同的读者在给他的留言里说:“《孤独》却让我深受震撼——正在经历的孤独,是迷茫;经历过后的孤独,是成长!青春是一本书,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或悲伤,或愉悦、或留在记忆里成为不想触碰的红色区域、或成为随时都想与朋友分享的光辉事迹……不论是什么样的故事,都离不开亲情、友情、爱情的主题。”他们是以平等分享的方式来面对自我经验的。长期以来我们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基本基于如下的原则,不是它能在哪些方面服务于我们,而是看它让我们摆脱怎样的思维定势。但张嘉佳们是逆行于这一原则的,它首先是服务于读者的,是体贴入微的写作,更重要的,他是跟你在一起的。尤其是对1980一代人来说,他非常朴素地唤起了一代人的共同生活图景,当然那也只能是一个曾经非常朴素的生活时代,才能在目下煊赫的时代,引来念念不忘之回响,“在空闲的时候,我和大家说睡前故事,从来不想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告诉你活着会有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每个人都不同,所以不需要别人的教导。只需要时间,它像永不停歇的浪潮,在你不经意的一天,把你推上豁然开朗的海阔天空”(《写在三十三岁生日》)。
当然张嘉佳几乎每一个故事的最后必然有一颗对世界的炽热之心,拒绝指向虚无与悲观,这反而与严肃文学或者说文学杂志上的文学有一道明晰的界限。几乎所有文学期刊上的人生故事,都沉浸在一种青年失败者的氛围中,“这个时代有点糟”,“我们是一群失败者”成为难以克服的最终反应。他们在强力的时代洪流和宏大的社会运转中,没有获得先机,于是随波追流,陷入平庸与重复,跌入虚无的深渊中。在《猎头的爱情》中,猎头的女友崔敏曾经被人怀疑偷了钱,他们打工赚钱,想还给被偷的女孩,让她消除错误的猜测,但等到他们攒够钱,彼时女孩已经转校。十年之后的聚会上,猎头的男人誓言是,“一旦下雨,路上就有肮脏和泥泞,每个人都得踩过去。可是,我有一条命,我愿意努力工作,拚命赚钱,要让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和艰涩,从此再也没有办法伤害到她”。虽然这个故事里面有命运的无常,生活中淡淡的艰辛,但张嘉佳始终让整个故事没有离开既有的跑道,这个无常并没有改变他们生活的本色,他们依旧有着回忆时刻的万丈光芒。张嘉佳这种毫无遮蔽之意的文字,大概是在这个时空中所能做到的最不虚无的,虽然这些文字的底色说到底还是虚无的,人终有一死。或者如奈保尔《河湾》的开首语,“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在人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方法的时候,或者说这个部分是个人努力与奋斗所无法触动的铜墙铁壁的时候,这些可口的文字是精致包扎后送到跟前来的一个看上去完美但又粗糙、简单的生命“解释”:“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帝会让你付出代价,照顾好自己,爱自己才能爱好别人。如果你压抑,痛苦,不自由,又怎么可能在心里腾出温暖的房间,让重要的人住在里面。如果一颗心千疮百孔,住在里面的人就会被雨水打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帝会让你付出代价,但最后,这个完整的自己,就是上帝还给你的利息”(《写在三十三岁生日》)。
纳博科夫说,风格与结构才是一部作品的精华所在。张嘉佳当然形成了自己的简单粗浅的风格,他喜欢机关枪一样的语速,乐在其中,奇异的排比句,句子的空洞而炫丽,说过好像没有说过一样,可能他们与读者的快感全在于说出的这个华丽丽的过程。那些呢喃的话语的确具有按摩治愈的疗效,死于列车出轨的朋友多艳,就是靠着这种排比句,从悲痛、愧疚转而消弭到青春无悔的模式去中了,“纪念2008年4月28日。纪念至今未有妥善交代的T195次旅客列车。纪念写着博客的多艳。纪念多艳博客中的自己。纪念博客里孤独死去的女生。纪念苍白的面孔。纪念我喜欢你。纪念无法参加的葬礼。纪念青春里的乘客,和没有返程的旅行”(《青春里没有返程的旅行》)。
张嘉佳几乎每一个故事的最后必然有一颗对世界的炽热之心,拒绝指向虚无与悲观,这反而与严肃文学或者说文学杂志上的文学有一道明晰的界限
张嘉佳的语言文字以及唯美的故事容易让人沉迷,以至于我们会暂时搁置这一代人不言自明的生活语境,憧憬着有一种生活如他们一样绽放或者放浪。他们无一例外都不谈时代的艰难,没有腐败、矿难、贫富差距、自我囚禁、时代板结,没有彻底的绝望,庞然怪物般的空虚。当然他们也很少以正面的方式谈论历史、政治,这些几乎都是一种简单的装饰性背景,是作者不管如何回避经验都无法摩擦干净的历史痕迹。比如“文革”,以他习惯的“镶嵌”方式出现在一篇故事中。一个老三届的妈妈,教训年轻儿子不敢表白爱情,“我上山下乡,知青当过,饥荒挨过,这你们没办法体会。但我今儿平安喜乐,没事打几圈牌,早睡早起,你以为凭空得来的心静自然凉?老和尚说要见山是山,但你们经历见山不是山了吗?不趁着年轻拔腿就走,去刀山火海,不入世就自以为出世,以为自己是活佛涅槃来的?我的平平淡淡是苦出来的,你们的平平淡淡是懒惰,是害怕,是贪图安逸,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女人留不住就不会去追?还把责任推到我老太婆身上!呆逼”(《老情书》)。沉重的历史、残酷的往事,以一个老太太戏谑的方式拉平到爱情的俗套上。这是时下多数文学的通病,只不过有病理深浅的区别。
现在的张嘉佳是一个定制版的综合体,我们可以在张嘉佳的暖男体小说中时时遇到熟悉的声调、故事
有一种说法,在一个涌动着无数暗流、贫富差距每天都制造不同故事的时代,如果不涉及现实,不主动担负起历史责任就是不道德的。而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这种道德基本是针对严肃文学的,也会在许多偶然时刻,比如它们太招摇过市时,成为挥向通俗文学的定制武器,虽然结果都是各说各话。从经典文学的角度来衡量、蔑视、忽视甚至鄙薄通俗文学是容易的,就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历史传统,也有鲜明案例。而现在鸡汤文的命名是最便捷的方式,只要被归入这个范围,就像刺上红字的奸夫淫妇,愿意吐上一口骂上一句固然是正常的人类选择,最高傲的方式莫过于“转过头去视而不见”,当然这也是一句非常流行的鸡汤文。
无论我们如何谈论通俗流行文学,也或者避而不谈,都不能阻止这种文学的突然疯狂成长,或者一直成长。张嘉佳的睡前故事大概是今年最为畅销的文学类书,据说在上海书展期间销售量仅次于郭敬明。当有大约二百万的人都在阅读一个80后作家絮叨睡前故事的时候,加上王家卫拍成电影,这个数量还会以更狂暴的方式上升,还是有一种壮观的即视感。参加过这一次张嘉佳的见面会,一个城市里凑起来的人群,大部分是年轻的女人,年纪相差在五岁左右的范围,有过共同经历的一代人,当然还有一些老的小的文艺青年。伴随着柔和轻缓的音乐,饱含午夜电台文艺散文朗读腔调的女声,驾轻就熟地读出张嘉佳的那些与狗狗梅茜的故事——《给我的女儿梅茜,生日快乐》:“我们要沿着一切风景美丽的道路开过去,带着你最喜欢的人,把那些影子甩在脑后。去看无限平静的湖水,去看白雪皑皑的山峰,去看芳香四溢的花地,去看阳光在唱歌的草原……去远方,而漫山遍野都是家乡。”一个爱护动物又不是激烈的猫狗平等主义者,一个情贴心灵的麦田守望者,一个敏感不屈满怀热情的灵魂,一个历经沧桑初心永葆的大众暖男的作家形象,呼之欲出。
销量和影响大到成为现象的此类通俗大众文学,改革开放以后是从琼瑶风靡开始的,历经岑凯伦、安妮宝贝,知音体、读者文、张小娴、连岳、陆琪等,其实我怀疑村上春树、昆德拉部分也是被以通俗文学的方式接受的,在这个名单上似乎还可以加上王朔、王小波、石康等。不管是经典作家,还是二流段子手,在大众读者接受的角度上可能都是被扯平了的,都是我们心灵的按摩师。而不得不说的是,现在的张嘉佳是一个定制版的综合体,我们可以在张嘉佳的暖男体小说中时时遇到熟悉的声调、故事,有波拉尼奥式漫游的不羁,有王朔式的痞气,有青春的粗糙杂乱,也有周星驰式的戏谑无厘头,有琼瑶爱情女神的执着,有连岳、陆琪的鸡汤风范,还有韩寒电影中的类似的“没有看过世界,怎么会有世界观”的行动哲学,还有许多其他面目熟悉的二手哲学。总之,这个张嘉佳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慢慢浸染中成长出来的一颗饱满硕大的果实。
张嘉佳的小说几乎没有特别鲜明的都市志痕迹,城市只是他小说故事的发生地
三
张嘉佳,198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的姜灶乡,典型的南方小镇,母亲是教师,父亲是公务员,典型的中国小康家庭的唯一的孩子。张嘉佳的个人生活,除了学习成绩忽上忽下无奈去复读外,看起来没有什么坎坷。他不是众多文学作品中那种备受压抑、心绪发达、内心敏感、带着痞气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典型小镇青年。张嘉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小镇神童,三岁时候就通过识字卡片认齐了基本汉字,开读《神雕侠侣》。小学之前,把小镇上能找到的金庸小说都读完了。虽然母亲是数学老师,但张嘉佳的数学却很少及格,母亲甚至有时帮他做作业。四年级时,学校举办书法、围棋、作文等各种各样的比赛,张嘉佳说:“第二天升旗仪式,所有比赛(我)都是第一名,在小镇出名了。”小镇生活留给他的另一部分回忆就是,稻田、河流、村庄的炊烟、金灿灿的油菜花;抓知了、摸田螺、偷鸭子,率领三百条草狗在马路上冲锋……小镇是张嘉佳心中的童话世界,日后在自己的小说里反复出现。而张嘉佳在小镇上的人生以升入大学划上逗号,跟所有当代中国的小镇青年一样,他们都迅速融入城市的生活圈子。但张嘉佳似乎并没有经历过从城市与乡村的巨大的心理差距(至少从他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看不出来),而这种心理落差几乎是近五十年来当代文学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母题,并且成为支撑起当代文学半壁江山的故事原型,从《霓虹灯下的哨兵》到路遥的《人生》、李佩甫的《羊的门》,甚至80后作家韩寒这种上海周边小镇出生的作家,也都先天有一种反抗都市的意味在作品和言谈中。另外,张嘉佳小说中也没有都市在地青年的那种天然的存在感,以及故意声张的“地方志”心态,这些东西日后都以迷茫自恋(怜)、沉溺式的都市青春小说的方式发泄出来。张嘉佳的小说几乎没有特别鲜明的都市志痕迹,城市只是他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除了几个南京地名,我们很难看到他对都市生活巨细靡遗的细节性的热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城市生活本身的表述。由此,那种寓居都市生活的屈辱、奋斗、挣扎的心态都可以略去不表,都市生活文学呈现的陈词滥调省略不说,这就造就了一种极为简洁、流畅,语速极高,具有速度美的故事流线和抒情语流,也为他小说中的自由随意的心态提供了一种合理性,为小说的轻逸摆脱了多重负累。连人物形象他都开始拒绝往人性深处伸展了——这几乎也是当代文学的另一个母题(人性的复杂、人心的暗夜等)。他的小说人物都是那种具有“飞蛾扑火”式美学意味的人物,他们说走就走,不计得失,甚至没有了现代人的算计,离婚的男人动不动就净身出户,以表示对曾经爱情的尊重;暗恋的女人们也都深埋爱情,为那个感受不到爱的男人付出到底。这一切让在现实中翻滚的人们看来,的确是一个具有诱惑力、幻想性,并且因为小说中生活语境的铺陈又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类“仙境”。
我们都在诉说自己,对忠实地想象他人的生活,失去了兴趣,或者丧失了这种能力
四
在严肃文学(或者说杂志、出版社文学)之外,当代中国一直有一批拥趸众多的作家,他们很难说属于通俗文学,但他们属于和鸣最多的作家。他们轻剪人们心翼上的星点,有时候也不过是蹈常袭故,但他们始终是体察时代人心的一条明晰的线索。从张嘉佳到刘同、安东尼,以及新的微信写作,好像我们都在诉说自己,对忠实地想象他人的生活,失去了兴趣,或者丧失了这种能力。莫里斯·迪克斯坦特别关注美国文学中20世纪60年代作品中的坦白趋势,这种趋势试图把文学从某种停滞不前的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使之接近于个体的体验。张嘉佳类似的创作倾向当然无法与美国1960年代文学倾向类比,但大体的历史情境颇多类似之处。我们也面临某种停滞不前的文学形式,作家们延续着重新模拟事实发生的世界,并由此模仿前辈作家们的思想承担,并幻想获得道德和责任上的光荣与梦想,对现实发出一种声音。此外,新的文学形式比如网络小说等以乖张庞杂的形式吸引了大量欲与欲求的读者,但这又很难获得渴望精神食粮的青年一代的芳心。张嘉佳们的作品拒绝、回避承担透视生活的窗口的作用,它是写给自己和同类的,就像公众微信号“记载人生”的口号,“和对的人在一起”。相对于想象他人的生活,为自我构想一个可能的人类情境,这些作家更在意自己同类人的世界。在形式上,他们的作品更像是随笔或是小品文而不是小说式的叙述,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故事要诉说,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情感要倾吐。
“唯我一代”可能是由于作者的懈怠,过于关注自我,或者缺乏想象力而造成的,但也可能和某种文化氛围有关,贬低技艺和创新、鼓励自我表达的文化氛围。将创作者代入作品,可以消除幻想和对生活的平庸模仿,使得读者听众更加关注形式。坦白式的写作方式,不需要辛辛苦苦地设计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和周遭环境,也不需要提出曾经让现实主义小说荣耀一时的历史洞见。按照莫里斯·迪克斯坦的意见,这些小说的作者“仅仅是作者自己,而不是就现实和再现的关系提出问题,进行反思。他们没有让我们走到幕后,去看艺术创作的过程,看作品在表述中如何观看自身,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虚构出来的人物,拥有无限可能的神秘和意外,他们只是写作的人: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将那些素材写下来,尽管他们也让故事的主人公陷入爱情与战争,但人物角色只可能生活在作者无处不在的光环之下”。
郭敬明为安东尼《陪安东尼度过漫长的岁月》写过一个序言:
他一直有一只玩具兔子,他取名字叫不二,走哪儿都带着,一直带去了墨尔本。他会和兔子说话,和它聊心事,和它分享心情,为它拍照(……),带它出去散步(……),并且在我有一次称呼不二为玩具的时候,和我闹了一个星期的脾气。
他甚至养了一棵像是食人花一样的植物,并取名字叫GUZZI(好像是这个名字吧,忘记了)。他也会和它说话……他有一天告诉我GUZZI心情不好,我问他:“GUZZI是你女朋友啊?”他说:“不是啊,你看!”于是他开了视频,把摄像头转向他房间的角落,于是我看见了一棵心情不好的食人花……
这是一段非常呆萌的文字和一个让人无法自矜的形象,让人萌生出促狭短暂的爱与温柔,为了一只玩具兔子闹一个星期的脾气,又或者跟一株植物说话。这都是唯我的气息,我们可以体会那种短暂的气息停留与眼神顾盼,或者也竟能付之于荡气回肠的爱与战争。最重要的是,它们就是生活与空气,即使外面的人一直呐喊着要戳破生活的假象与幻影。但他们所写下的爱情故事,细节的真实,萌动的思绪,还有大城市夜晚的每一条街道,广袤世界的任何一个为我而存在的地方,都是一枚掷地有声的徽章,散发着它微小而顽强持久的力量。奈保尔说,每个作家都是带着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给予他的安全感来写作,他被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所保护、所支撑,他永远也做不到像海明威那样去写巴黎,带着探险家的自得其乐去描写狂热去描写狂斟豪饮和性奇遇,却从不涉及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海明威能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简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而奈保尔却无法把自己放在一个类似的位置上。他心里清楚,在1930年代,一个像他这样出身的人绝无可能去到巴黎,就在这样简单的层次上已被拒绝。张嘉佳他们当然也是在许多简单层次上已经被拒绝的作家,依靠着自己的安全感来写作是许多作家没有选择的选择,它只能是袖子上的一枚徽章,不会成为一具躯体,但我们能看到它各个角度的闪亮。
罗兰·巴特说过,自己的任务是探索一种文学记号的历史。他讲过一件轶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论家埃贝尔在写作时,总爱用一些“见鬼”和“妈的”这样的字眼。这些粗俗的字眼并不表达什么,然而,这种写作方式却是当时革命形式的需要,它把一种语言之外的东西强加给读者,形式的历史表现了写作与社会历史的深层联系。张嘉佳们的小说、散文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记号,或者是肩膀上的徽章,或许正是靠着他们所提示的形式,才会指引下一次文学形式的变革,如果还会有变革的话。小说家卡萨塔尔不只把作家看作艺术家,也看作见证者,看作有偏见有人性、愿意学习的人,他认为我们需要从关心这个世界的人身上反观这个世界。但从唯我一代这种写作倾向的作家身上,似乎看不到对世界的关心,却有享受的热情和耐心。在平滑、鲜亮、炙热、奶白色的光韵之外,伸展的是一片雾气和不安的深渊。但有时候,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大城市夜晚的每一条街道,广袤世界的任何一个为我而存在的地方,都是一枚掷地有声的徽章,散发着它微小而顽强持久的力量
编辑/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