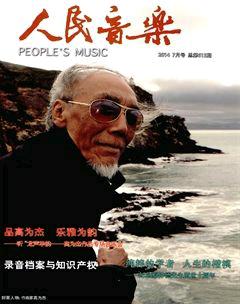声词相从声意相谐
孙伟
沈括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他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宋史》中称赞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沈括晚年居住在镇江,并建梦溪园,写成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该书是他根据科学实践和平生见闻著成,内容涉及数学、天文、音乐、历法、气象等数十个方面,被英、法、美等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瑟博士称《梦溪笔谈》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并盛赞沈括是“整部中国科技史中最卓越的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席文认为《梦溪笔谈》“是每一个研究早期中国的考古、音乐、文艺批评、经济理论和外交的文人所必须参考的”。
沈括对乐律颇有研究,根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曾著有《乐论》、《乐律》、《三乐谱》、《乐器图》等书,可惜都已失传,唯一留下的仅是《梦溪笔谈》和《长兴集》中的相关论乐篇章。沈括的音乐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二是对音乐美学的研究;三是对声学原理的研究”。关于沈括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笔者认为主要包含音乐表演美学思想和音乐创作美学思想两部分,而本文主要探究的是沈括的音乐创作美学思想。
北宋时期,民间艺术昌盛,“音乐创作与表演,已不再为贵族少数人垄断,音乐活动在城市经济发展及其市民阶层壮大,文化政策宽松的环境下,向民间化转型,音乐民间化表现形式多样”。各种民间演艺场所如勾栏、瓦肆、瓦合、酒楼、茶馆等兴盛,诸宫调、鼓子词、唱赚、货郎儿、陶真、杂剧等各种民间音乐创作形式丰富,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沈括在对当时多种音乐创作形式做了深入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对民间音乐创作做出了精彩的论述,在我国音乐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笔者通过对相关著述的梳理、归纳和探究,认为沈括的民族音乐创作美学思想主要表演在三个方面:其一,他秉承了儒家的乐教思想,首先看到了音乐创作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提出“礼乐在天下,为用最大”,并根据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亲自进行音乐创作实践。其二,沈括认为词曲音乐创作的真正源泉在民间,因此他重视民间音乐,尊重民间艺人,经常深入民间,走访考察,敏锐的观察、记载、研究当时的俗乐。其三,在多种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沈括得出了“声词相从,声意相谐”的音乐创作之法,至今仍是作曲家遵循的基本准则之一。
一、音乐创作之用——
“礼乐天下,为用最大”
“沈括的音乐美学思想基础是儒家乐教思想”,故其秉承《乐记》中的“审乐以知政”的思想,十分重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在其早期给欧阳修的书信《上欧阳参政书》中,就提出:“礼乐在天下,为用最大”。沈括认为举天下之政应从大者着手,而政之大者,即为礼乐,因此建议欧阳修把礼乐当作施政的头等大事,虽然是给欧阳修的建议,却也寄寓着沈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礼乐观点。
在给蔡襄的书信《与蔡内翰论乐》中,沈括借用圣人的语言又云:“礼乐云者,其关天下盛衰如此”,音乐的风格和审美倾向,往往能反映一个时代政治的清浊。“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歌的思想感情是安逸平和的,就用安逸平和的音调来歌唱,诗歌的思想感情是幽怨的,就用幽怨的音调来歌唱。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安逸而快乐,动乱时代的音乐充满着怨恨和愤怒,故只要听听音乐,便能“听”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状况,这就是考察音乐可以知道政治情况的道理。因此,在《上欧阳参政书》中,沈括又道:“昔周之盛也,《清庙》、《大明》之音作于上,《武象》、《南口》之乐兴于庭,《鱼丽》《鹿鸣》《关雎》《猩首》之声塞于天地之间,嘉祥美物备至,而天下风教习俗皆宽舒广裕,蔚然号为至平极治之时”,足见其非常向往周代大治境界的礼乐文明。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人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社会环境对人具有教育意义”,沈括的记载着重反映了当时的音乐状况,同时也是对当时政治、社会状况的写照,故“在复古风气弥漫于音乐领域的宋朝,沈括的音乐思想是重今的”,杨荫浏先生称之为“现实主义音乐观”。沈括在后来的一生中,最高官至三司使,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尽管他以礼乐达到治政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但在具体的工作中,沈括非常重视音乐的现实作用。在延州上任时,常见士兵得胜回来,高唱凯歌,但词粗俗,于是作几十首歌曲,让士兵演唱,如:“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扎吃儿”、“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等歌词,抒发了战士们慷慨激昂的雄心壮志和反对妥协的豪迈情怀,反映了人们要求统一,反对战争的心情,带有深厚的人民性和普遍性。沈括所揭示的题材、主题和思想感情,也正体现了沈括对音乐创作的社会功能的重视。
二、音乐创作之源——
“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
民间音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因此保护和利用好我国的民间艺术,对于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凝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
然而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一大特点,是统治阶级的音乐与民间音乐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统治者们试图推行《雅乐》来控制广大的人民群众,经常非议、排斥民间音乐。而在沈括的论述中,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弊端。丰富的科学知识及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让沈括在论及音乐事项时十分重视民间艺人的音乐创作和布衣平民的音乐活动。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资本的兴起,北宋城市蓬勃发展,市民阶层壮大,反映市民阶层的音乐艺术形式昌盛,涌现出了众多的演艺场所和民间艺人。民间音乐的发展强烈地冲击着贵族音乐和宫廷音乐。当时很多文人雅±和封建统治者沉醉于古乐,以古非今,轻视民间音乐为“淫哇之声”、“不依古法”。然而也有许多的音乐家和文人,他们思想进步,非常重视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并根据现实生活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其中沈括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沈括认为“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他承认音乐随时代前进、民族融合发展的事实。与那些一味抬高雅乐、排斥民间音乐和沉醉于古乐的态度相反,沈括把“清乐”、“燕乐”列入音乐史,给予应有的地位,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endprint
沈括非常重视劳动人民在艺术和科学上的发明创造,这与他重视调查研究,较多的接近群众是分不开的。他深入民间,吸取养料,敏锐地观察、记载、研究当时的音乐状况,真实记述民间艺人及民间音乐的状况,他甚至把对教坊老乐工请教切磋乐律变化的情况都如实的记载下来。在《补笔谈》卷一“乐律”第535条就有这样记录:“席朝燕部乐,经五代离乱,声律差舛。传闻国初比唐乐高五律。近世乐声渐下,尚高两律。予尝以问教坊老乐工,云‘乐声岁久,势当渐下”。而一般的封建文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在谈到音乐创作的时候,沈括认为“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他觉得在他的时代中声词相从的只有里巷歌谣。沈括赞扬了民间音乐,反映了词曲音乐的真正源泉在于民间
“人民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唯一泉源”。“沈括充分地认识到音乐创作者要让自己的创作‘乐有志,声有容,开神兼备,只能深入群众和实践,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故尖锐的指出,音乐是“百姓”的事情,并辩证的强调从民间音乐实践中汲取养分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意义。在《上欧阳参政书》中,沈括写道:“然观古者至治之时,法度文章大备极盛,后世无不取法。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遗而至于大备极盛,后世无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明确的指出了创造与发展科学艺术的不是什么“圣人”,而是“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所谓先王的宫廷雅乐,究其最初的源头来自于民间。这些论述在当时实属难得可贵。当今的民族音乐工作者主张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强调田野与案头相结合的工作原则,而沈括恰恰以其自身的实践,很好的诠释了这一原则,为后世的音乐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在当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潮中,经常提起的就是“传人”这个词,
“传人”即所谓的“民间艺人”,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宝贵财富。民间艺人所掌握的某类传统音乐表演技艺,都是在数百年的传承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民族音乐文化珍宝,其价值无可估量。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乐工和民间艺人身份很低,尽管身怀绝技,但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歧视,乐工被称为“贱工”。然而沈括却逆潮而行,在他的著述中常以赞扬和钦佩的口吻叙述他们高超的技艺。例如在《补笔谈》“乐律”539条中有这样的记录:“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稽琴格”。稽琴是两根弦的拉弦乐器,用一根弦奏完曲子,需要乐工熟练的转换高低把位,体现了伶人徐衍精湛的演奏技艺,从此以后,“一弦稽琴格”,被认为是稽琴的演奏方法之一,成为乐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音乐创作之法——
“声词相从、声意相谐”
芙音乐创作是作曲家通过各种实践对客体(宇宙、社会)得到感知、感受,采用形象思维并用音乐的载体表现、传达至欣赏客体,是为音乐创作。感情的表达、词曲的结合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起着贯穿始终的重要作用。在沈括的时代,有一些“音乐人”只做一些表面的功夫,而不抒发内心的感受,使声词不相从,故在歌曲创作上,沈括主张“声词相从、声意相谐”,通过歌词与曲调的完美结合,真实的表达思想内容,至今这仍是作曲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之一。
在古代,词与乐的结合是中国音乐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形态之一。诗词既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入乐传唱,受到音乐的制约。“音乐性”和“文学性”是诗词不可或缺的两个属性,词与乐一度关系密切,水乳交融。沈括对词与乐关系的表达主要体现在《梦溪笔谈》“协律”一条中。
在论述的过程中,沈括首先阐明词与乐发展的两个阶段:“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第一个阶段是先诗后乐,乐从诗,诗歌为主。他认为古代的诗歌都是按照其音调的抑、扬、顿、挫吟诵的,然后依照吟诵韵律谱成曲子,叫做“协律”。如《诗经》中的标题《关雎》、《鹿鸣》等都是诗名,而不是乐名,音乐处于伴奏地位。第二个阶段诗从乐,音乐为主。唐末、五代、北宋初词人的作品,则以音乐标题为词的标题,如《菩萨蛮》、《蝶恋花》等,音乐从伴奏地位发展为主导地位。
在此基础上,沈括概述了“词”的产生过程,“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日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刘尧民先生在专著《词与音乐》中认为:“他是最早从音乐中寻找词产生原因的人,这段论述是关于词起源的最早学说”。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产物,从诞生之初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陆游在《长短句序》云:“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词的入乐传唱,使声词协谐,可以歌唱,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曲子词的繁荣以及词的产生,呈现出北宋时期“宫廷禁苑、士人家宴处处歌声,青楼画阁,茶坊酒肆家家管弦”的局面。
沈括十分注重将曲子的情调与词的内容统一起来,在说明了词与曲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沈括进一步提出了“声词相从”的创作原则,指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三种情况:“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第一种情况是赞扬了民间音乐,他觉得在他的时代中,曲调和内容能密切结合的,只有在民歌、民谣和《阳关》、《捣练》等曲子中间才能找到。第二种情况是说明唐人填词对,多半是以曲牌名的含义为依据,因而悲哀、欢乐的情者和曲调还配合得当。第三种情况沈括批评了当时某些乐人,认为他们不懂音乐,常常不注意曲调,用悲哀的乐周去唱快乐的歌词,或用快乐的声调去唱哀怨的歌词。尽管歌词写得真切动人,但由于声调和思想内容不相符合,就无法达到感染群众的目的。由此看出,他是对当时那些利用现成曲牌,不管音乐的感情内容,而形式主义的硬填进内容与音乐毫不相关的歌词的文人而言的。
正是因为词逐渐的从音乐中脱离出来,到了南宋,词最终成为了不可歌的书面之作,只能是士大夫文人用来抒怀的诗篇了。而此时兴起的诸宫调、唱赚、陶真、涯词、鼓子词等说唱艺术形式,更能适应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从而取代了曲子词这一歌唱艺术形式的主流地位。可以说,词与乐的分离是曲子词衰落的根本原因。而沈括所反对的封建文人重词轻乐的风气,正是以后词衰落的原因之一。
结语
宋朝音乐文化上承先秦、隋唐之歌舞伎音乐,下启元明,奠定了明清音乐艺术发展的坚实基础。生于北宋中期的沈括以其亲身实践,把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引入封建统治者层层束缚的音乐领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他重科学、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更为后世的音乐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在他一生的业绩中,音乐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他对音乐不凡的修养和造诣,深刻而独特的见解,使他在音乐创作方面的研究不限于了解表面现象,而能够深入地看到音乐创作的功用与本源问题,进而总结出“声词相从,声意相谐”的音乐创作之法,这不仅丰富和拓展了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更为当今的音乐创作者指明了方向。参考文献[1][元]脱脱等《宋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吴自牧《梦梁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3][北宋]沈括《长兴集》,引文据四部丛刊本,兼以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校改。[4][北宋]沈括、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文艺理论组《“梦溪 笔谈”音乐部分注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版(本 文所引《梦溪笔谈》论乐原文均出自本书)。[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年版。[6]王文章《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版。[7]金湘《音乐创作学导论》,《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4 期。(责任编辑 金兆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