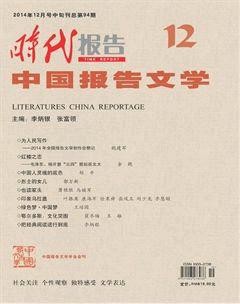乌拉盖河的记忆
任秉舜
五月的一天,老连长张志和从乌拉盖打电话告诉我:六月中旬,乌拉盖管理区文体局将组织“乌拉盖河徒步溯源之旅”,问我参加吗?我心里一下子激动起来,没有犹豫,脱口就说:参加!
我手头有一本乌拉盖管理区旅游局出版的《最美的天然草原——乌拉盖》的画册,其中有一幅乌拉盖河在丘陵中蜿蜒曲折滋润着广袤草原的航照,宏大的画面让人震撼。还有一幅旅游点的分布图,乌拉盖河和她主要支流——色也吉勒河如同两条金线串起河边的湖泊,泉眼在汇合处打了个结的项链,乌拉盖苇塘如同是那光彩夺目的项坠,等待着人们去观赏,去抚摸。徒步乌拉盖河让我魂牵梦绕了多年,终于有了机会,我约了要好的朋友,要作乌拉盖河全程徒步之旅。准备已经做好,与组织者取得联系后,澎湃的心情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组织者要求每位参与者必须持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近期的体检证明,可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现办恐怕来不及了。我反复声明,如果出现意外,后果我自负,但还是被谢绝了。
尽管无缘全程徒步乌拉盖河,但没有挡住我去乌拉盖的行程。若在乌拉盖河边撩撩水,涮涮脚,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和乌拉盖河有三十多年无缘了。
刚到内蒙兵团时,新兵班长刘志会给我们介绍内蒙兵团和乌拉盖的情况,着重说了乌拉盖河:乌拉盖河是全国第二大内流河,是全国唯一从东北向西南流淌的河流。上学的时候,老师讲地里知识时说:中国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所有的江河不论怎样曲折,最后的归宿都是向东流入大海。并引用古人的诗句加以佐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乌拉盖河从东往西流有悖自然规律,用学到的地理知识和刘班长抬起杠来。刘班长找来一张地图指给我看,乌拉盖河的源头是东边大兴安岭的余脉宝格达山,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低矮的丘陵,造成了东高西低的地形,水往低处流,所以乌拉盖河也就顺着地形向西流淌。
我在兵团时,去过乌拉盖河上游的宝格达山,到过乌拉盖河中游的九曲十八弯,在乌拉盖河的终止地乌拉盖苇塘打过芦苇,逐渐对乌拉盖河从东往西流的缘故清晰起来。但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乌拉盖河弯弯曲曲行进了360多公里,途中又接纳了数条支流,日夜不息地注入苇塘,这苇塘到底能蓄多少水?是不是苇塘某处有暗河又通往他处?这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谜。
色也吉勒河在我的老连队五十一团十连东南方向龟山的龟尾部拐了个弯汇入乌拉盖河。后来,我调到张志和任连长的五十二团四连,四连距乌拉盖河徒步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但我接触乌拉盖河总是某一河段,对乌拉盖河的记忆用断断续续这个词再恰当不过了,所以有“瞎子摸象”的感觉,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对乌拉盖和乌拉盖河情有独钟,不论是在兵团时期写的东西,还是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每次写在内蒙兵团苦与乐,汗与血的经历时,便会提到乌拉盖和乌拉盖河。有编辑问我:为什么总是写乌拉盖和乌拉盖河?我说:别的我写不来,兵团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那里寄存着我的青春,我还要一直写下去。
这次到乌拉盖应韩连山大哥之邀,去他家的牧场作客,韩大哥的连襟李向德的皮卡载着我们一行四人,从师部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下了柏油路,汽车行进在只有两条车辙的土路上。草原刚返过浆,坑洼不平,汽车忽上忽下,但觉得比在柏油路上多了些惬意。三十多年没走过这样的路了,顿时产生了亲切感。当年我们不论去什么地方走的都是这样的土路。
顺便说一下,现在乌拉盖人称我们当时的师部——巴音胡硕镇为管理区,我们知青还是习惯称之为师部。当年的烙印,在我们脑海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凭我的直觉,汽车行驶的方向是乌拉盖河,而且越来越近。我问向德:韩大哥的牧场离乌拉盖河有多远?向德说:也就是二里多路。又要见到久违的乌拉盖河了,我跟朋友们说起当年的事来。
哪里有蒙古包,哪里必定有河流或水泡子,有河流和水泡子的地方,牧草必定茂盛。那时候不像现在把草原划成若干个库伦分配给牧民定居放牧,那时是逐水草而居。登上龟山山顶,往北看,是时宽时窄的色也吉勒河,往南望去是弯弯曲曲的乌拉盖河,两条河的河边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在蓝天白云、青草碧水的衬托下特别醒目,河岸边的牛、马、羊群散落在草滩上,显着平和与宁静。
我们最愿意去的地方是两条河的汇合处,那里有几座蒙古包,包里的牧民跟我们都很熟悉,因离我们连近,像买些烟酒或寻医问药等项经常与我们来往。我们也经常去他们那里喝奶茶,吃奶豆腐。有意思的还是在河边“端鱼”,“端鱼”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把破脸盆底凿几个眼儿,上面绷上块纱布,纱布上抠个窟窿,盆里面放上几块肉骨头,找个水浅的河弯,把脸盆沉入水中,稍许盆里面钻进半盆大大小小的的细鳞鱼,把盆端上来后,把小鱼挑出放回河中,大鱼打掉鱼鳞,去掉内脏,捡几块干牛粪燃着,用铁丝将鱼串上,架在火上烤,一会儿鱼香四溢,蘸上细盐,那叫一个香。吃渴了,趴在岸边,嘴贴着河面来个“牛饮”。
调到四连离乌拉盖河更近了。夏天,乌拉盖河在这里宽有数丈,河水满槽,听说最深的地方有二三米。一次团支部在河边组织青年活动,一个新来的王姓知青,不听劝阻,执意下水,结果被吞噬了生命。
连里为生产、生活、牲畜饮水方便,从农乃庙水闸上游处,挖了一条渠,安上渠闸,把乌拉盖河的水引入连里。每天早晨,管水员骑马到农乃庙,先放下乌拉盖河里的水闸,等河水涨起来后,就提起通往连里的水渠闸,往大渠里放水,待渠储满水后,又放下渠闸,供连里用水。傍晚,管水员再把渠闸打开,让水撤回乌拉盖河里,这样,大渠里的水总是新鲜的。
一天,从团部拉粮回来晚了,马车经过大渠的小桥时,趁着月光,我们发现不远处银光闪烁,好奇心油然而生,我让车老板把车赶过去,近前一看,竟是一搾多长的细鳞鱼。渠水撤出后,鱼儿滞留在凹地,密密麻麻地挣扎着。我们跳入大渠,足足装了半麻袋。回到连里,我让炊事班的弟兄们赶紧扒膛去鳞,第二天中午炖了一大锅红烧鱼。尝到了甜头,每天傍晚,待渠水撤出后,便约上几个人,拎着水桶,顺着大渠转悠,有时满载而归,也有双手空空,悻悻而回的时候。
农乃庙是三连的驻地,距我连有十几里地的路程,乌拉盖河在这里拐了个胳膊肘弯,河湾的内侧是一片泽地,那里的鱼更多。一次骑马去三连,见农工们的房顶、门前几乎家家都晾着鱼干儿,鱼腥味扑面而来。三连的司务长与我相识,忙不迭地张罗午饭,炖猪肉、炒鸡蛋,还有一盆铁锹把粗细的红烧泥鳅。吃饭时我开玩笑地说:你们炊事班做饭的手艺真高,炖肉、炒鸡蛋竟能做出鱼味的来。司务长一笑:我们这里鱼多,连里和农工们饲养的猪、鸡都是用鲜鱼、鱼干儿喂养,所以,猪肉、鸡蛋都有股子鱼腥味儿。他指了一下不远的河滩:春夏之交,泥鳅咬籽的时侯,一个人一天能整几水桶泥鳅。他说给我烧的泥鳅还不算是最大的。他又说:冬天多冷,白毛风多狂,猪不进圈,迎着风吹肚皮。夏天猪怕热,整天泡在河里,这就是“鱼生火,肉生痰”的道理。
后来听说,当年日本人占领了农乃庙,把庙里的僧人赶走,日本人在这里建了军马场,养驯乌珠穆沁马,供关内外的日本骑兵乘骑。乌珠穆沁马种脚力好,抗寒,耐疲劳,通人性,再加上这里的水好,草场好,养驯出来的马更是上品。苏联红军出兵满蒙,农乃庙地处草原深处消息僻塞,住在这里的日本兵没有接到上峰的投降命令,负隅顽抗,苏联人将农乃庙和里面的日本人一并摧毁。
乌拉盖河最好的去处当属她的终止地——乌拉盖苇塘,苇塘有多大面积我不得而知,我知道五十四团有两个连队驻扎在这里,他们主要任务是冬天打芦苇。每年冬天打下的芦苇堆积如山,一年四季成队的卡车将打成包的芦苇运往大石寨火车站,然后再发往牡丹江等地的造纸厂。仿佛苇塘的芦苇无穷无尽,永远打不完,拉不败。
每年冬天,我们连也要到苇塘打芦苇,一是用来打苇帘交到团里。二是分配给农工每家一车苇子,用来取暖做饭。为满足上述需求。全连人差不多用半个月的时间去苇塘。苇塘离连里有二三十里路,马车得走上一个多钟头。有人别出心裁,用木板钉成木排,下面安上两根拖拉机履带的链轨销子,再用铁条做成钎子,安上木柄,就是极好的冰车了。
我有几次体验,拖着冰车,拿着钎子,趟过雪原,直奔河边。坐在冰车上,撑起钎子,冰车在冰面上疾驰如飞,感觉太棒了。我们到苇塘多时后,才听到车老板吆喝牲口的声音。
苇塘的苇子齐刷刷的有两人多高,小竹子般粗细密不透风。不识地形的人不能贸然进入,即便离岸边不远,也很难返程。打苇子时,先由一个人用一米多宽的推刀,擦着冰面推出一条道来。然后,几把推刀四面开花。推刀与冰面的摩擦声,推刀割断芦根的爆裂声,咔——嚓,咔——嚓十分悦耳。推刀手每推几步,倒下的苇子就能捆上个牛腰粗的苇个子。一个推刀手后面跟着几个人捆苇子,应接不暇。推刀推过的地方,像镜子面那么光滑。人们叫着号地把苇个子装上马车,七八辆马车装的有一人多高,宽出马车车厢两倍多,如同用苇子堆起的座座小山。
夏天是苇塘最漂亮的季节,各种鸟儿在苇塘上盘旋,发出各自不同的鸣叫,不绝于耳,委婉动听。听说在苇塘栖身的鸟类不下几十种。最有意思的是掏鸟蛋,一次,去芦苇二连,几个老乡带我去掏鸟蛋,不到一个钟头,收获了一水桶。小的指甲盖大小,大的如同铅球。他们根据鸟蛋的大小,不同的颜色,告诉我哪个是野鸭蛋,哪个是地鵏蛋,哪个是大雁蛋。掏鸟蛋时不知被什么鸟给袭击了,在我脑袋上狠狠啄了一口,浸出血来,尽管受了伤但没有影响情绪,煮蛋、炒蛋,吃得满嘴流油。
向德握住方向盘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我接着想说乌拉盖水库的事,向德指了指前面的几排瓦房说:那就是韩老大家的牧场。
我们到韩家大哥的牧场时临近中午,韩家人操持着午饭,厨房里飘出煮手把肉的膻香味。与韩大哥和他家人寒暄后,见人家都在忙活,插不上手,便和同行的朋友们去寻乌拉盖河。
这天天气真好,湛蓝的天上飘着几片白云,阵阵清风掠过,嫩草的清香直扑鼻腔。深吸了几口气,恨不得把五脏六腑的浊气全部置换出来。南面远处的山峦,由嫩绿梯次为浅蓝、深蓝一直铺向天迹,如水墨画般的宁静、飘逸。东南面有两座一大一小的山丘相互依偎着,如同一只巨大的乌龟静静地卧在一马平川的草原上。那是我的老连队五十一团十连的所在地。
尽管已进阴历五月,草原上还有些寒意。听说今年春天来得晚,前些日子雪才融尽。但草原上的各种草借着春光,春水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牧场的牛羊低着头,迈着小步,享受着春天的恩赐。我跟朋友们说:乌拉盖的天气特点就是冬寒长、夏热短、春暖快、秋凉早。别看现在还有寒意,用不了几天,脱下冬装,便进入盛夏。
有朋友问我,现在的天气还这么冷,冬天得多冷啊?我说:乌拉盖最难熬的就是冬天,从十月份开始下雪,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五月。冬天虽然残酷,但也给人希冀。严冬对草原也是保护,就跟人一样,累了、困了需要休养,睡眠。当时我写过几首律诗,刊登在《兵团战友》报上,其中有一首《乌拉盖之冬》,我随口念给大家听:
雪落原野路无痕,
风吼淹没马嘶声。
乌河已作蛇行死,
龟山去绿白头生。
牧人停歌酒暖身,
牛羊反刍卧畜棚。
虽说尽是苍茫地,
来日青草花更红。
我们没走出多远,一条小河横在我们面前,我闹不清这是不是乌拉盖河。这时,向德怕我们陷入泽地,开着皮卡追了过来。我问向德:这是乌拉盖河?向德一笑:这是刚融化的雪水形成的溪流,注入乌拉盖河。他指了指前面一道弯弯曲曲的银带:那才是乌拉盖河。
我绕过溪流,想亲近一下乌拉盖河,可没走几步,脚一下子陷入泽地,用力拔脚,可越陷越深,无奈把脚从鞋里退出来,弯腰用劲把皮鞋从泥潭里抠了出来,我那狼狈像惹得大家一阵大笑。向德说:这个时候,河边到处泥泞,夏秋季节来河边最好。我这个“老乌拉盖”由于心切,竟忘记了最起马的常识。向德又说:自中游修了乌拉盖水库,下游的水比以前少多了,鱼也不多了,苇塘也萎缩了不少,鸟种也稀少了,向德长长地叹了口气。
牧场那边的人向我们招手,看来,酒席已备好,我极不情愿地一步三回头,近在咫尺的乌拉盖河,却没来得及用河水洗把脸,涮涮脚,真是遗憾。
朋友手指着龟山那边问我,那边是不是在下雨?不知啥时候,东北面一片乌云,天连着地,地接着天,如同黑色的瀑布悬挂着,把整个龟山遮挡的严严实实。我说那边是在下雨。朋友说:这真是“西边日出东边雨”,真是作诗的好场景啊。这时我又想起我当年写的一首律诗来,题目是《乌拉盖之春》和《乌拉盖之冬》一起刊登在《兵团战友》报上。当时的情景跟眼前的特别相似,我随口吟了出来:
嫩草青青味芬芳,
花蕾婷婷欲待放。
百灵鸣叫晨曦里,
骏马奔驰晚霞旁。
近听牧人有歌声,
远看毡包伴牛羊。
龟山脚下垂雨瀑,
乌水河畔艳阳天。
写到这里想起一句话来:有时遗憾并不见得是遗憾,遗憾也会产生动力。如果说再有徒步乌拉盖河的活动,提前做好准备,以了却徒步乌拉盖河全程的夙愿,免得真的留下遗憾。
责任编辑/何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