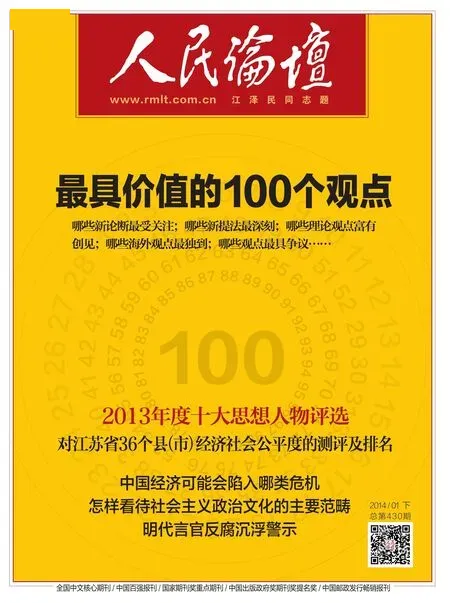改革新逻辑开启改革新进程
李占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继往开来,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提出了事关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国家抉择。全会以改革新逻辑提出“六个紧密围绕”,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定位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六大方面,真正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进程。
全会展现的改革新逻辑
习近平同志在全会召开之前就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论述。这一论述让举国上下意识到,今天的改革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改革前后党的历史与国家历史。全会正是根据这一逻辑积极主动地肩负起未来使命的。实际上,改革开放前后历次党的三中全会都从不同方面承担了国家改革的重要使命,进而做出了对党和国家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抉择。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七次三中全会,每一次都深刻体现了党的执政治国理念的成熟、发展与深化以及国家各方面改革发展的新认识。
不得不说,这些新认识往往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实际问题的严重困扰时产生的。例如十一届三中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十年“文革”动荡造成的国家发展落后、社会秩序混乱的严峻政治、经济形势,唯有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才是让国家焕然一新的新逻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说:“改革需要胆量,没有胆量就没有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前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们必须将它做好。”习近平同志也说:“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以解决党和国家现实面临的问题为落脚点。”①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五年,党和国家都是以改革来解决发展历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难题的。思想认识问题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定解决;市场经济问题被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解决;发展观问题被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解决等等。可以说,改革的春风化雨不断深化、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三十五年风雨兼程中时刻指引党和国家朝着新的历史高度迈进,推进中国改革不断开启新的历史进程。
全会开启的经济新进程
首先,全会要求中国经济要协同求变。这意味着中国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转变过去多年所提出的增速“保八”的僵化维稳思维,而是将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相协同、调整,建立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案系统。所谓求变,就是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动态思维,保证经济和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并积极勇敢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局。此外,中国经济协同求变也是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协同与求变,它要求全方位转变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不仅要做到上下、内外协同,还要做到中央与地方、各产业、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中国经济协同求变的根本价值在于,曾经非“左”即“右”的既定单一经济评价标准无须再提及,而是综合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手段推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经济制度,偏“左”与偏“右”两者也都需要协同。如果做不到协同求变,中国经济将会面临更大风险。
其次,全会要求对分配结构进行有序调整。分配问题是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解决好这个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科学检验改革开放成果的根本。当然,现实社会中这一问题的解决比经济学领域常用的“分蛋糕”比喻要复杂得多,而全会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这块“难啃的骨头”上。②例如全会试图针对国民赋税进行均衡化调整。中国在分配领域曾经长期高度依赖针对流转环节的税收。换言之,就是偏重于对劳动者征税,反而对资本及资本所有者的征税偏轻。如果言及赋税公平,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背离了赋税正义与公平原则,也逐渐背离了经济效能与效率原则。有鉴于此,全会突出了深化国家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期望从正义、公平原则出发,改变税收结构不合理甚至逐渐扭曲的状态,从而避免近几年在中东、北非国家因赋税结构扭曲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和政治教训。此外,全会所提出的国家财税制度改革还涉及到定向转移支付问题。定向转移支付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再分配的均衡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资本分布在地域和产业层面上的均衡化,从而引导国民经济的结构化改革。在必要时,定向转移支付也会与金融创新、改革相互结合,让国民经济加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阴霾。无论如何,通过对分配领域进行结构化、有序性调整,进而从根本上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可以使全会后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继续保持正常发展的态势。现在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或政治精英估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如果真的能够落到实处、经济结构调整步入正轨,那么只需要大约五年时间,中国经济可以预见到崭新的、平衡的、有序的状态。
最后,全会要求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努力实现自主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努力调整内部结构的同时,还需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努力调整日益严重扭曲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毕竟它已经是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介入这种国际性调整。中国要实现自主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国家主权以经济为手段适度延伸至全球范围。也就是说,中国将从单纯的商品生产与输出进阶为包括生产、流通、销售等领域在内的全球商品管理。当前,扮演这一国际角色的只有美国一家。但国际金融危机业已表明,美国作为全球商品管理者并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反,它在不断利用这一角色地位为自己牟取暴利。与此同时,以德法两国为发动机的欧盟正在努力挑战美国全球商品管理者的地位。所以,中国没有理由坐视不理,而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介入经济全球化的管理工作,或者至少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管理成员之一。
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自主性,必须立足于不断迅速成长的金融力量,而中国金融力量的根本在于人民币的实力和国际认可,同时也在于中国国家财政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强大。基于这一点,建立稳定、健康、高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是全会胜利召开后中央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目前,中国仍然处于难得的发展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历史机遇期内,因此,中国需要正视这个机遇期内所存在的三种历史可能性,以严肃的危机意识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第一个可能性是,开启经济全球化的自主进程,推动国家健康、高速发展。第二个可能性是,陷入漫长的调整过程甚至是停滞过程,犹如当年的日本。第三个可能性是,调整失败,彻底陷入贫困、腐败、萧条的历史周期,犹如当年的南美洲诸国。然而,全会及其《决定》无疑给中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第一种历史可能性,更有理由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完成历史性飞跃。
全会开启的政治新进程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察觉到,改革的总体框架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③1986年,他以当时日益突显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家长制问题为着眼点,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着重发展社会主义和党内民主政治。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末,在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顶住了压力,取得了一定成效。而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稳妥、积极为主基调,以政治建设为重点,放到依法治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上来。进入21世纪,十六大明确了国家性质和宏观发展道路上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顶层设计的理念。从国家性质而言,就是要始终将政治体制改革框定在社会主义原则之内,绝不将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一套模式照搬进来。从宏观发展道路而言,就是要始终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积极稳妥推动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之源。正是因为多年来我党坚持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才使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随着行政运行和政府权力行使的日益透明,一个法治理性与民主色彩日益浓厚的中国正在给世界制造一个又一个惊喜。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改革政治权力的配置模式。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党的领导机制范畴,还关系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中国的政治权力配置长期以来呈现出一元化格局,具有明显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特点。具体表现在人治超越法治、党委领导一切、书记一人说了算等很多方面。例如,尽管确立了党委协调各方、总揽全局的领导模式,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关系进一步理顺,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党委高度集权的行政领导格局;尽管有步骤地削减了党委副职人数和职数,提高了交叉任职在党委班子中的比重,缩小了只能由党委班子拍板决定的事项范围,但实际上党委书记的一言堂现象还是没有能够从机制上得到有效遏制;尽管党在民主监督、管理、决策、选举等多方面相继施行了新的举措,还通过“适度放权”实现了“还权于民”,但实际上人民群众的行权、维权成本仍然居高不下,过去的政治权力配置体系仍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图谱。
之所以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不符的局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以权力配置为重点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化。有鉴于此,全会提出:第一,施行党政职权适度分离。在科学合理处理好党政关系的同时,党委要避免过多介入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日常事务。各级党委要积极面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路子、新方式。例如,地方政府党委书记在一般情况下应规避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能随意插手或控制人大事务;有的地方政协主席由一名党委副书记兼任,使党委过多干涉了政协内部事务。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那么所谓党委协调各方、总揽全局,就会成为事实上党委集权的借口。第二,要改变党内权力运行缺乏监督的状态。当前,各级党委实际上集中了各级党员代表大会或其常设机构的决策权,而它在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又对本身被赋予监督权力的纪委施行领导权力,客观上使党委成为集决策、执行和监督为一体的绝对权威机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活力的施展。第三,要充分发挥我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法宝。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与其他党委成员在坚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同质、同量、同等行使票决权,绝不能只流于民主集中的形式,只集中、不民主或者只民主、不集中都是不可取的。总之,全会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目标明确、方式果断,切实以顶层设计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全会开启的社会新进程
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社会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社会主义社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要进一步探索的改革新领域。党的十七大就已经意识到,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逐渐与经济建设相剥离,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于是提出“社会建设以推进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增了一项范畴,即业已独立于经济建设的社会建设。全会继承和发扬了十七大的社会建设创新理念,下决心全面推进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推进就业政策,将改革目标定位于充分实现就业、提倡就业公平、改进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以兼顾公平、效率为原则,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为基调,让人民普遍分享改革开放红利;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价值目标,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社会创新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党领导下的公众积极参与、社会共同协调、政府负责到底的社会科学化管理新格局。全会之所以提出上述社会体制改革目标和途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社会体制改革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全会在该领域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良好开端、开启全新进程。
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一大重点和难点。三十五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④如今,中国在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下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极富活力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实现了政府主导、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文化生产和经营主体依法管理运营的多位一体。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体描绘了中国文化事业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全会之所以提出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让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和整个世界民族之林。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另一方面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真正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真正提高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自信心,真正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此外,全会还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作为社会改革的另一项重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还不断加强和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时至今日,社会管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成为“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及其负面影响的正确途径。全会提出,要让九亿农民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必须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工农互惠、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型城乡结构关系。为实现这一点,全会还明确提出了四个要求,即:推动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和市场要素的均衡化配置;充分赋予和保障广大农民的财权;构建农业经营的新型体系。这些具体措施明确了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强城乡活力、促进共同繁荣影响深远。
【注释】
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第45~47页。
②《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33页。
③周小文:《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解析》,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166~167页。
④高尚全:《改革只有进行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4~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