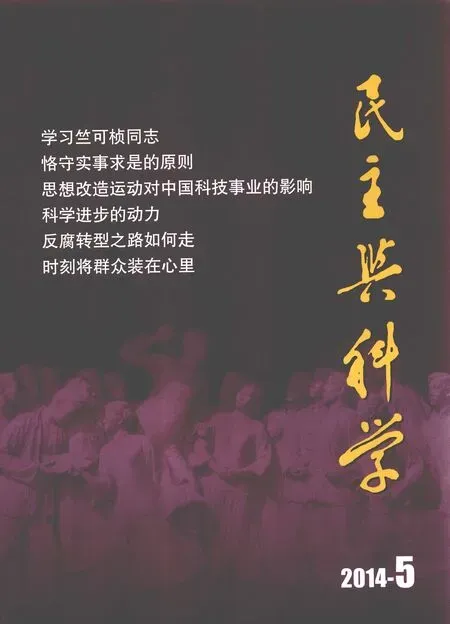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竺可桢的“文革”岁月
李玉海
(作者曾任竺可桢秘书、原中国科学院技术条件局局长)
那场动荡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在其后的1967至1969年间,伴随着在全国范围滚滚而来的批斗当权派、结合革命领导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一次次政治风暴,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人事外调的大潮。在这种潮流下,著名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将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接待外调事务上,俨然成了一个外调专业户。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文革”开始时期,浙大师生可谓遍及全国各地。竺老任职中国科学院当时已快20年,接触的多是所级领导和高级研究人员,所以在外调潮中,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蜂拥而来,应接不暇,接待量之大,超乎想象。对来访人员,有时是直接面谈;有时是先留下调查提纲,回去查对日记做准备后再谈;有时要将来访者的记录带回家认真核对修改;也有的来函提出调查提纲,竺老书面回复。
据统计,1967年接待各种外调、来访共92次,最多的一天接待三次。1968年是接待外调的高潮期,接待各种来访、人事外调及书面回复总数多达230次。最多的一天多达六次;一上午最多约谈四次,说得口干舌燥。1969年接待量有所下降,也约达160次。在整个“文革”期间,接待与书面复函总数在500次以上,合算下来,纯粹用掉的时间当在一年以上。
竺老的这段往事,是在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和特殊贡献,花费了无数心血。其中的点点滴滴,无不折射出竺老的求是精神与道德情操。
实事求是是竺老为人处世与做学问始终恪守的原则,同样也是“文革”中接待外调工作所坚持的准则。他把接待外调看成是政治任务,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既对外调人员负责,又对被调查人员负责。每作回答,言必有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68年6月,复旦大学来人调查学部委员苏步青教授,竺老用了许多时间从日记中查清事实,共谈了三个上午,有问必答,不厌其烦。1968年12月2日,武汉水利学院来人了解该院通讯部副主任刘忠潮。刘于1948年在浙大壁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骂青年军为职业学生,与当时反动学生发生争吵。来人要调查在争吵中刘出卖了多少人。当询问看法时,竺老敢于直言,认为这不是出卖。他说:“我的看法认为写大字报不是地下工作。地下党是秘密工作,大字报是大字报,是大鸣大放的一部分。大字报统留有笔名就是负责的意思。”为了还原被调查人员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反复查对当年日记。他说:“像这类事花费我时间不少,但目前清理阶级队伍是政治上头等重要任务,我不能不把我日记中记录详细写出,可以作为刘忠潮当时表现的实录。”
竺老对外调人员的记录稿,必经亲自阅览和修改,确定无误后才签字。如在1968年7月18日日记上,关于浙大学潮的谈话稿,他的记述说:“所记前后不相连贯,如若当档案看待,读了以后不完全能了解,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改了三页,前后共计11页。下午睡一小时,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晚膳,膳后直到8点为浙大来改写记录稿子。XXX等并没有把所记录的加以整理,所以前后错乱,读者尚不了解那时浙大情况,读了可能莫明其妙。我要她们重抄,才能签字。”
在接待中,竺老从不迎合外调人员,尊重事实,坚持己见。1967年6月21日,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来人了解副所长施雅风,说他反党,是反革命。其根据是1937年施曾参加国民党所办的武汉战事训练班,而造反派抄家时还留有参加该班时的文件。竺老认为根据不足,明确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说要看战地军事训练班训练的什么,“如是为了对付日本敌人,则亦不能厚非”。1968年6月24日,杭州大学来人了解教育家郑晓沧教授,质问郑等赴英美考察做了什么“罪恶勾当”?竺老当即指出这个问题提的不当,并引用毛主席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话“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来应对外调人员。对外调人员说,没有确凿证据与事实,不能说去外国就是做罪恶勾当。
竺老认为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问题,历史是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同时常常引用毛主席的话作为根据和武器,使他的观点更具说服力。1968年6月28日,北京电业管理局来人了解浙大毕业生吴祖光时,问到1937年浙大迁建德时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如训练壮丁等等。竺老在日记中写到:“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文中说道:‘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陷落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毛选》页986)所以从现在看过去必须以辩证的眼光去看,把历史当作是发展的。国民党特务想统治学校从1939年建立训导长制度以后加倍严厉,而从1942年1月浙大、联大举行倒孔运动游行以后,才进学校抓人。在吴祖光在校时代国共关系尚属和缓的。”
竺老的日记是当年的实录,对澄清事实很有说服力。竺老依据日记记载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对正确反映被调查人员的历史经历及对改正某些诬陷不实之词,起了重要作用,对被调查人员起到了保护作用。如1970年9月25日,原子能研究所来人了解学部委员赵忠尧在1947年是否在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问题,竺老从日记中提供的材料解除了他们的疑惑。竺老记述说:“他们疑心赵忠尧参加美国那时试验原子能用作原子弹的问题,这谣言是捕风捉影之谈。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捕风捉影之谈也要追踪一个究竟。星期三他们二人曾来吴老(吴有训,编注)处谈了一个多小时,吴老于1947年10月才到麻省理工到了赵忠尧做实验的地方。但他们要知道的是1946年10月到1947年3月赵的足迹,我适在1947年年初到剑桥遇见赵忠尧,我留剑桥直至五月,所以可为赵在剑桥的见证。他们认为满意而去。”
竺老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人所要了解的多是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尽管他以日记为据,秉持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但出现记忆模糊或出差错的情况也在所难免,当他一旦发现所提供的材料存在问题,就立即纠正。有一次对所调查对象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那是1968年12月9日上海高教处来人了解钟道赞到遵义调查浙大学生倒孔运动的情形。接待后发现将此钟道赞与时任遵义警卫司令部的钟参谋给混为一谈了,次日立即进行了更正。他在日记中写到:“把昨天所发现关于1942年钟道赞来遵义调查倒孔运动时,他的作为写了一个概略,以更正我昨天告上海高教处XXX中所述一节的错误。因为他已把我所说的写成一个节略,我阅后并签了字。这样就把伪教部钟督学和遵义警卫司令部的钟参谋混为一谈冤枉了人,急须加以更正。”竺老这种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精神,堪为楷模。
在接待工作中,竺老也表现出了他一贯的为人正派与善良,处处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有一个名叫吴藻溪的人,一连给竺老写了6封信,反映他被划为右派,至今未得平反,要求竺老将他的信转给科学院革委会,以求其问题得以解决。竺老并不认识此人,看了其来信后也觉得信中所说未必可靠,但想到此人万一真有冤枉,如果置之不理,使受有冤屈的人得不到昭雪,不是被自己给耽误了吗,所以把其中的3封信转给了科学院革委会。
竺老也设身处地为外调人员着想,认为他们远道而来,很辛苦,所以不厌其烦,有求必应,尽己所能。1969年5月22日接待河南南阳工业局来人调查该局副局长潘家苏,已是第4次了。他在日记中说:“1967年两次,今年一月间一次,这次又来,可说费力甚大。所以这次一定要答好,不要再漏掉什么,否则他们老远还会再来。”还有一次杭州大学来人了解张君川和张其昀。他记到:“因为我口讲是拉杂很随便的,不能作为一个正式文件,所以看后改了数处,但没有签字,他们作为参考而已。因他们从杭州远道而来,所以我总是尽我心把我所知道告诉了他们,有多大用处是很难说了。”所以,绝大多数外调人员都对竺老的认真负责与事实求是的态度留有深刻印象,都有所收获,满意而去。
“文革”期间的外调人员,鱼龙混杂。有些是带着框框为打倒某人而来,竺老依据事实,坚持己见;而大部分来者是为弄清事实,为保护好的干部而来,竺老为他们提供了真实情况,都使好干部得到了保护。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在那个是非颠倒、罪及全家的年代,因受竺老提供的有力证据而免于被冤枉的干部,也使他们的家人免于被株连。竺老的辛苦、忙碌、付出,惠及不少家庭,实在是温暖人心、公德无量的善举,功不可没。
今天看来,竺老撰写的外调材料无疑是一批珍贵的史料。但遗憾的是,留存至今的已微乎其微。
竺老付出的时间之多,接待数量之大,前后跨越时间之久,书写材料之多,前无古人,后恐也难有来者,可誉为“文革”接待外调第一人也。
纵观竺老一生,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大事、小事,他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都用心、尽力地做好。就以“文革”中接待外调这件事,不少人都经历过,而唯在竺老手上,做得如此有声有色,令人心悦诚服、称赞不已。
竺老的每段人生,都留下了不同的精彩。
正是许多看似平凡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他伟大人生的滔滔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