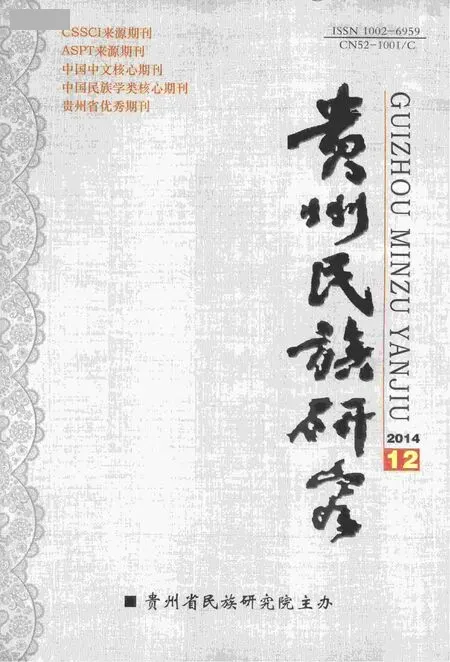哈萨克族摇床及其人类学解读
唐莉霞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49)
一、哈萨克族摇床简介
新疆哈萨克族将摇床称为“别斯克”,是他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一直使用的育儿护理用品。 “一种绵延发展了几千年的物品,透过思想的、宗教的、经济的、民俗的和民族的因素,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基础就是功能,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魅力”。[1]哈萨克族的摇床就是这样一件既具育儿功能,又体现游牧文化魅力的物品。每一个哈萨克族的孩子都是在摇床里和着长辈的情谊长大的,摇床是哈萨克族婴儿的第二个怀抱。
哈萨克族传统的婴儿摇床长约100厘米,宽约50厘米,高约60厘米,由质料坚硬的桦树、红松等木材以榫卯结构而成,通体不用一根钉子却非常牢固。摇床头尾两端的下方由弯曲为弧形的木条着地,以使床体左右摇摆;摇床上方有一横木将首尾衔接,便于提放和放置纱幔遮挡蚊虫。大多数摇床的床帮和床腿都雕刻或用土漆着色绘制哈萨克族传统的角纹或植物纹样,既美观又富有游牧文化的特色。一些精致的摇床还镶嵌有金属制成的乳丁,显得熠熠生辉。为了祈求婴儿健康茁壮成长,特别是如果婴儿“不那么好带”时(容易生病、夜啼等),家长还会在摇床上装饰“乌库”即猫头鹰羽毛、狼髀石等在哈萨克族看来可以驱邪除灾的吉祥物,有的家长会给婴儿的摇床上挂上一个小小的图马尔(这也是一种哈萨克族的吉祥物,几乎家家都会悬挂,具有消灾禳祸的意义),这个图马尔是家人为了孩子健康,将古兰经经书的手抄页缝制于其中,再请阿訇念过经的。哈萨克族相信摇床悬挂了这些吉祥物能使婴儿免受邪气侵害而健康成长。
摇床的中间掏出一个约10厘米大小的洞,便于婴儿大小便。当孩子固定在摇床上时,母亲一般会将“图别克”即一根一端打磨挖孔、一端切掉的中空的羊小腿骨管或木管,整个形状比较像一个烟斗,套在小男孩儿的生殖器上;而女孩则用一块木制的或骨质的削成勺状器物扣在孩子的外生殖器上。这样孩子的尿就会顺着它流到摇床中间预先放置的容器(“加克”)中。摇床上铺有羊毛毡毯作为褥子,视季节而厚薄不一;小床单和小枕头。毡毯上也留有与摇床相对应的圆洞,洞口四周放有四块巴掌见方被称为“奥达”的棉布并在弄污时及时更换。摇床的排便构造科学合理,保证了孩子能在一个清洁干爽的环境中成长,有效防止了便溺或尿布更换不及时导致婴儿可能出现的生殖器感染等问题。
摇床两边各有两条用纯色或彩色羊毛捻成的绳子,用于对放入摇篮的孩子进行捆绑。摇床很大程度上使得父母得到了解放,尤其是几乎要承担起所有家务劳动的女性,有了摇床,她们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照顾婴儿。转场的时候哈萨克族把摇床固定在马或骆驼的背上,安全又平稳。而哈萨克族长期以来积累的严格而合理的捆绑婴儿的方式,在保证了孩子舒适度的同时既能避免孩子挣脱出摇篮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又能起到塑身的效果帮助孩子有个笔直的身形。此外,摇床由于体积小,特有的榫卯结构又具有拆卸自如、收纳容易的便利,所以在空间有限的毡房里摇床几乎不占什么地方。
二、哈萨族族的摇床礼及相关禁忌
哈萨克族在婴儿出生后7天(现在有的哈萨克族举行摇床礼的时间为婴儿出生后40天,也即产妇坐月子结束后)举行将婴儿放入摇床的睡摇床礼,即“别斯克吐依”。届时,主人邀请亲朋好友、邻里乡亲,而参加者主要以女性、孩子居多。摇床由德高望重、最好为子女有作为、儿孙满堂的老年妇女铺好,摇床礼也由她主持。由她点燃松树叶子或火柴,在摇床上绕上几圈(多为3圈或7圈,因为3、7是哈萨克族的吉利的数字),边绕边祈祷:“真主啊,请让灾祸远离此处,让孩子健康成长,让快乐幸福跟随他(她)一辈子。”同时,前来参加的妇女则要给婴儿送诸如衣服等贺礼。还要在新布置的摇床中间的洞里,撒上一些糖果、包尔沙克(哈萨克族的一种传统油炸面食)、奶疙瘩、干果等,前来参加的孩子要上前“一抢而光”,以“恰秀”(哈萨克的一种祈福形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祝福。接着,这位老年妇女会为婴儿洗澡,擦净身体后用早已准备好的羊油在孩子身上抹一遍,轻轻拉扯孩子的四肢后,再将婴儿放在摇床上包好。这时前来祝贺的人们一面尽情享受早已准备好的哈萨克族传统美食,一面弹起冬不拉,载歌载舞。孩子的母亲则守在摇床旁视孩子的性别为孩子唱起饱含祝福之意的摇篮曲。传统上,若是男孩,母亲一般会期望他长成一个出色的牧人,成为部落的英雄,若是女孩,母亲则希望她能心灵手巧。而现在母亲的期望则更多地淡化了性别的因素,希望无论男女,孩子都能健康长大,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哈萨克人。
可以看出,哈萨克族的摇床礼既有哈萨克族崇奉伊斯兰教的因素,又有他们曾经信仰萨满教和拜火教的影子。而更多的是摇床礼成了一种象征,成了一个仪式过程,成了初生的哈萨克族婴儿必经的一个阈限,通过摇床礼迎接孩子正式成为这个家庭、这个部落,乃至哈萨克族的一员。同时,参加这个摇床礼的其他哈萨克族小孩,在一次次耳濡目染中从小就懂得尊老爱幼,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也得传承。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摇床礼相伴而生的对孩子的祝福也有了新的内容。平日在毡房里,或是定居房内,哈萨克族也总是喜欢把摇床放在靠近火塘的地方,因为他们相信火是光明而神圣的力量,可以防止邪气侵蚀婴儿。哈萨克族人还忌讳当面夸奖孩子,尤其还处于“摇床期”的孩子,认为这会给孩子带来坏运气。另外,哈萨克人不摇动空摇床,他们认为只有失去孩子而变疯的女人才会这样做,如果摇动空摇床则不仅会失去孩子还会使自己变成疯子。从这些关于摇床的禁忌来看,更多地表达了哈萨克族对新生命的悦纳,对孩子简单而直接的爱。
三、哈萨克族摇床的人类学解读
哈萨克族的摇床是哈萨克族人的手工造物,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之前关注“how people make things”到如今对“how things make peole”的重视,从之前的“只见物不见人”到如今的“既见物又见人”,即从技术和艺术形式层面转而对物进行深入的解释与阐释,了解造物者们的“文化理念,发现背后的概念系统和意义体系,认识与之相关的其他许多因素”[2],理论范式的转变使得人类学对物的研究更加丰满。以物的研究角度而言,不仅是哈萨克族人制作并使用了摇床,在某种程度上,摇床也成了哈萨克族的生计方式、儿童养育文化、家庭文化、族群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及工艺之美的表征。“照例说,是特定的社群或文化族群、民族或部落制造并使用着物体,并因此反映了群体的某些行为方式,这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3](P219)因此哈萨克族摇床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其作为手工之物的形制、功能、工艺、装饰等“外显”的元素,其后内隐的与摇床相联系的哈萨克族的文化、民俗、民族性等更有深意。
哈萨克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在他们的谚语中就有“教子一次,胜过施粮一升”这样的古训。作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被誉为“世界上搬家次数最多的民族”,流动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家庭教育在哈萨克族子女的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他们“教育孩子要从摇床开始”的传统。哈萨克族爱护儿童,从不轻易打骂儿童,更多的是通过言传身教对孩子进行道德规训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哈萨克族的孩子从出生到会走路,除了必要的活动外,一般都在摇床上度过。母亲和家人通过摇床照看孩子,孩子通过摇床观察世界。母亲在哈萨克族儿童的启蒙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在摇床边教孩子说话、给孩子讲哈萨克族的故事、给他们唱哈萨克族的摇篮曲、儿歌,教给孩子们哈萨克族的格言、谚语、箴言等。孩子们在母亲的歌声、故事声中沉沉睡去。当孩子从摇床中出来时,有时母亲也会给孩子哼唱起哈萨克族传统舞蹈“黑走马”的曲调,扶着摇床的孩子总是情不自禁地和着歌声扭起来,哈萨克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就在这一方小小的摇床中传承下去。而伴随着母亲在摇床中长大的哈萨克族对母亲也是敬重有加,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哈萨克族人在做“乃玛孜”(伊斯兰教的礼拜)时,对父亲的呼唤可以不加理睬而专心做仪式,但对母亲的呼唤则不可置之不理,否则就是失礼。哈萨克族的家庭和民族的教育也是在这一方摇篮里开始的。通常每个哈萨克族都能说出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他们认为“不知七代祖先的名字的人是孤儿或是没有知识的人”,所以当孩子还在摇床里咿呀学语时,长辈就经常教给孩子七代祖先的名字。哈萨克族历史上的英雄、名人也是长辈经常给孩子讲述的对象。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孩子从小就培养了对哈萨克族家庭和民族的认同感。
哈萨克族的摇床一般是代代相传,新疆阿勒泰市民俗博物馆展出的一个摇床,据说已经有四代人使用过,将近80年的历史了,尽管摇床上的花纹已经磨平、曾经的雕漆已经脱落,但是依然可以使用。在阿勒泰市萨尔胡松村的报道人家里访谈时,正好看到报道人一岁两个月的小孙子睡在摇床上,他的母亲正给他哼唱着摇篮曲。这个摇床是他爷爷当年做给他爸爸的,爸爸的弟弟和妹妹也是在这个摇床上长大的,他的哥哥和堂姐也是枕着这个小摇床长大的。爷爷说,这个摇床就是家中的传家宝,如果可以的话还要继续传下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哈萨克族家庭都有这样一个承载着家庭记忆的传家宝,而通过摇床这个传家宝,“家庭成员能够建构一种类似的档案,使各个家庭成员赢得一种历史感,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这是超出、延伸到他们自己生命和成就之外的。”[3](P149)在与哈萨克族接触的过程中,当问起他们的摇床时,每个与它相关的人总是如数家珍,有关家庭的片段通过摇床被串了起来,在那一刻,摇床不仅是家庭的一部分,更变成了一种有关家庭文化的“计时的工具”——摇床意味着一再掀起了生活的新篇章,意味着哈萨克族最为重视的血缘、谱系关系的延续,意味着家庭和社区中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以及围绕着这些新生命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勾连,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物品会用来提醒主人它第一天来到他们家时和自那时起所度过的时光。它不仅构造他们的现在,还有对他们自己过去的感知。”[3](P122)无疑,哈萨克族的摇床就是一个家庭的历史记忆和亲属关系自我延伸的载体。
如果说,摇床是逐水草而居毡房的哈萨克族的一项基于生计方式的选择的话,如今许多住进了定居平房甚至楼房的哈萨克族仍然绝大多数选择用摇床来照看、抚养婴儿,尽管他们的经济和居住条件允许他们使用各种更精美、功能更多样的婴儿床。笔者在阿勒泰市区古丽家拜访时,她家靠窗的沙发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旋木雕花摇床,和煦的阳光洒在摇床上的纱幔上,她半岁的女儿正甜甜地睡着。而房间的一角放着一个汉族朋友送的没有开封的现代婴儿床。古丽说;“汉族朋友给我送这个婴儿床,我很感谢她,但还是觉得我们的摇床好,晚上把摇床往床上一放,睁开眼睛一扭头就能看见女儿,若是她哭了,顺手一摇,都不用下床,而且自己睡沉了也不用担心会压着孩子,多方便啊。而且摇床是我们哈萨克族的文化啊,我们每个哈萨克族人都是伴着摇床长大的。我儿女睡的这个摇床是我公公专门托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哈萨克族木匠给订做的呢!你看我们好多传统的东西都没有了,比如小时候我奶奶毡房里桦树皮碗、我妈妈结婚的花木箱,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了,但摇床还在用,肯定会传下去的。”古丽的话代表了我接触的大部分哈萨克族人对摇床的看法,用哈萨克族人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对摇床有一种情结,一种源出于摇床是哈萨克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的一部分的情结。对他们而言,摇床意味着游牧文化一种根性的东西,哈萨克族的孩子就应该在摇床里长大,就应该经过摇床礼,这些东西是时间带不走、岁月磨不平的族群的记忆。
如前所述,摇床作为哈萨克族婴儿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件物品,一般是婴儿的父亲、爷爷或者是当地手艺最好的木工所做。在现代生活方式和机械化无处不在的今天,哈萨克族的许多传统手工艺已经部分或完全使用了机器,比如绣花有绣花机、擀毡有擀毡机,牛奶发酵也不再是皮囊发酵而使用了温控发酵机。但摇床却一如既往地主要是手工生产的,虽然机器加工组装的摇床可能更精美、刨得更平整、抛光更细致,但许多哈萨克族还是宁愿选择自己做摇床或是请木匠手工制作摇床,这可能就是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的手工艺品偏好时所提出的“手工制品要花更久的时间来创造——即他者更多的自我投入了其中”。[3](P131)而且“所创造的东西,不管是一件物品或是一种抽象思想,其创造者都在这件物品上保留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一直能保留到只要还剩下一个标志或某种与其创造者的联系。这个身份通过保留创造者与其精神独创作品之间的联系的版权、专利和科学依据而被编码固定了。”[3](P133)哈萨克族人在制作手工摇床时可能并没有想着保留身份、什么版权、专利的,然而在哈萨克族这样一个重视血缘谱系的民族里,孩子是他们血脉的延续,他们喜欢孩子,家庭将有一个小生命诞生,全家都满怀期待,甚至孩子降生是整个社区的喜事。爷爷或者爸爸早就亲自准备好小摇床,不仅是送给孩子的礼物,更倾注了满满的爱意。不会木工的长辈早就拜托了临近手艺最好的木匠来为孩子制作了一个摇床。当面对这样一件用于喜庆和具有生命诞生和延续意义的活计,木匠也是一丝不苟,他希望自己做的这个摇床不但能代表自己的水平,更能带给使用它的孩子以好运、健康与长寿。作为手工制品的摇床,实现了“物”、“我”、“心”的意蕴相连,正所谓“佳作至纯,能显示出延续的生命的喜悦”[4],这就是日本民艺专家柳宗悦推崇的“工艺本身应带有‘爱’的性质”吧!在哈萨克族婴儿的摇床礼上和今后的岁月里,摇床的制作者也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此外,摇床主要以木为原料,木乃性温、性平,和自然天地造化,木之温润加上摇床中饱含的手工的温暖,手艺的力量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便成就了勤劳、善良、质朴、团结的哈萨克民族。
四、结语
如今新疆的哈萨克族大多已走出毡房,跨下马背,走进了定居安置点,其传统的游牧生计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许多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传统手工物品也与他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哈萨克族人家用的还是这具有千年历史,代代相传的摇床,摇床成了哈萨克族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致用则久、致用则美、致用则爱,哈萨克族摇床让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这个既科学实用又美观大方的饱含了哈萨克族人的智慧与情感的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对现代生活的强大适应力,更让人再次体验到了根植于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摇床所传递的手工的力量和勃发的生命力。
[1]杭间.手艺的思想[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203.
[2]王建民.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转换[J].艺术人类学论坛,2007,(1):44.
[3]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日)柳宗悦[M].徐艺乙,译.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