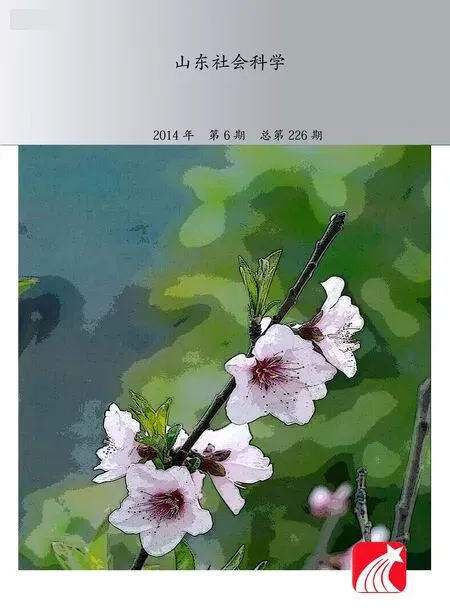交往行动理论视角下现代道德合法化危机的根源
陈太明 傅永军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1784年,萨德(Marquis de Sade))于巴士底狱写下《贞洁的厄运》一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哲学著述要成为杰作就必须顺从天意的安排达到为人类安排的目的而运用的手段,而后依据这一目的而设计出若干行动计划。使这可怜的两足动物清楚自己在充满荆棘的路上该如何行走,才可预防命运——有着无数不同名称而尚未做到加以认识、予以界定的命运——种种变化莫测的离奇拨弄。”[注][法]萨德:《贞洁的厄运》,张章译,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作为启蒙时代邪恶象征的萨德,用自己乖谬、荒诞而又悲剧的一生从另一个方面诠释着启蒙的另一副(丑恶)面孔。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提起萨德所宣扬的邪恶道德风尚与被社会公开接受的道德规范之间存在的张力与冲突,直面曾经发生在启蒙的欧洲的人道主义灾难(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现代化”的集体大屠杀)时[注]关于反犹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按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看法,二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启蒙所造就的异化、统治等工具化倾向导致了个体的消亡,这也就为大屠杀提供了理据上的支持。关于这一点韩水法教授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反犹主义的出现乃是根源于基督教一神论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导致统治者必须从敌对者的存在中获得自身合法性基础,在这种不断的树立与压制敌人的过程中,使得自身统治得以巩固(对于此问题的具体讨论详见韩水法:《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话语与范式》,载[德]阿梅龙等主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23页)。对于这二者谁更有说服力,我们在此不予置评,但就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高墙壁垒与现代化的屠杀工具而言,启蒙造就的自由之任意性诠释与工具理性的单向度理解模式无疑充当了帮凶。,我们是否认同这样一种判断:“理性的最后一点光芒已经从现实中彻底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坍塌的文明废墟和不禁的绝望。”[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面对此种境况,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我们不禁要问:人——这个用理性为自己谋划的具有语言和行动能力的存在物,要为现代道德提供一种合理性论证,真的必须回到那遥远的前启蒙时代吗?答案可能一时令人迷惑,但重新检视启蒙无疑是重新反思的起点。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把启蒙称之为“文化活动”的精神革命,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经过启蒙运动的精神洗礼,现代人完成世俗化之脱魅过程并真正获得了其为人的尊严。当然,启蒙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因素。从今天的角度看,启蒙乃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它就像希腊神话里的雅努斯(Janus),具有两副面孔。支持者可以从启蒙中发现解放的动能与力量,反对者亦能从中发现野蛮的现代变种及宰制的现代形式。这种吊诡特别体现在现代道德上,现代道德继承了启蒙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崇尚理性、自由与平等,却又因此招致自身从未有过的证成危机与现实危机[注]“证成危机”指的是启蒙之后的众多道德理论在论证人类道德时所陷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诸如元伦理学的道德情感主义把道德看作感情的表达、社群主义者将其看作特定社会中美德的培育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继承了启蒙的断裂精神,但却得出了不可通约的结论从而放弃了启蒙的规范性诉求。“现实危机”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种种道德缺位的情况,现代社会在物质进步与有效管理上无疑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我们却随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无情。这些表现同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将动物的自私基因发展到了极致,而悬置道德规范的规约作用。。“我们诚实且真诚,我们归还自己的债务并信守承诺;我们具有同情心且关心他人,同时公平且公正。我们敏感、友善、仁慈、宽恕、慷慨、感恩、忠贞、自我牺牲;我们具有政治的自觉与主动,并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不论性别、种族与性取向。”[注]Logi Gunnarsson, Making Moral Sense: Beyond Habermas and Gauth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
然而,令人困厄的是,这些人类引以为傲的现代道德品性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合法化危机,以致其本身无法得到理性的辩护从而失去合法性根基。表面看来,这些危机的存在乃是源于现代社会各种价值取向与意义追求的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危机的存在植根于启蒙精神本身的含混与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自由的误读;其二,理性自身的矛盾。这两个方面分别导向现代道德合法化危机的两个侧面,即证成危机与现实危机。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最激进的旗手之一,康德用“哥白尼革命”式的理性革命为启蒙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脚。因而,回顾康德对启蒙本质的论述有助于重新发现现代道德困境的诸多线索。换句话说,现代道德所面临的深层矛盾实质上已经有意无意地隐含在康德的思想中了。
一、“主观自由”的误读:现代道德的证成危机
众所周知,康德对启蒙抱有极大的热情与自信,在他看来,启蒙乃是人之理性的解放与自如运用。1784年,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开宗明义地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注][德]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距康德提出并给定这一问题的答案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的时代是否已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知,抑或换一种表述,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已然在康德为启蒙规划的康庄大道上自由自主地行进?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此,对于什么是启蒙的回答依然扑朔迷离且仍在继续,正如福柯于二百年后(1984年)发表的同名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假如今天我们要追问什么是现代哲学,那么答案是——“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一直在试图回答两个世纪前非常贸然地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启蒙?”(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 in Paul Rabinow(ed.),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one, trans., Robert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303-320, p. 306.)可见,虽然今天哲学的主题变幻更迭,各家之言各有理据,但就本质而言,我们仍然未能厘清何为启蒙这一问题,也未能就启蒙带给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进行有效反思。那么,何为“受监护状态”?康德对此论道:“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注][德]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由此可知,所谓的“受监护状态”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外在权威的盲目服从。依照福柯对这一术语的分析,康德“所谓的‘受监护状态’,指的是我们的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得我们在需要运用自身理性的领域中,却接受了他者权威的指导”[注]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 in Paul Rabinow(ed.),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one, trans., Robert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303-320, p. 306.。从康德的论述以及后来福柯对康德论述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启蒙的首要目的乃是将人从他者的限制与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自我抉择、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已经解除了对人的魅惑,但现实中却仍有很多未启蒙者沉醉在他者给予的压制中,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康德认为乃是因为人的懒惰和怯懦。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于依赖自我之外的他者来获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愿意接受启蒙所暗含的自我论证负担。因为“受监护状态是如此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智慧,有一位牧师代表我拥有良知,有一位医生代替我评判起居饮食,如此等等,那么,我就甚至不需要自己操劳”[注][德]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如此情势下,人似乎沉浸于那种假象的、无理性自主的安逸状态,他们已经完全被规制于监护者所给予的各种章程和公式甚至是不允许有任何质疑的命令下。由此可见,在康德的思想中,在未启蒙的蒙昧状态或受监护状态下人并非没有理性,而是尚未学会如何运用自己本身固有的理性能力去论证、行事与生活。既然理性乃人之固有,接下来要做的只是需找一种方法来激发它使之显现,进而通达启蒙的光明之路。
依康德所见,受监护或蒙昧状态相较于启蒙状态乃是一种不成熟,只有经过启蒙的人类精神才标志着人走向了成熟状态,因而,哲学家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教授人摆脱奴役进入自我决定状态的方法。根据康德的观点,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由,“这种启蒙所需要的无非是自由;确切地说,是在一切只要能够叫做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务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注][德]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从康德这一掷地有声的豪迈宣言中可以窥见,康德实际上对自由作了限制,或者说这里的自由并不是那种我们惯常理解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要能够不受自身意志之外的东西(外在他者)的限制、公开地运用理性之自由——即“理性的公开使用”。
就康德的语境来说,理性的公开使用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宗教状况,其时,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不但独断地掌握了解释世界的方式,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对之自由诠释的空间。根据康德的看法,生活于这样思维脉络中的人乃是非启蒙状态的最好诠证。哲学家作为理性启蒙的精神导师所要做的,就是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力量为思想开辟空间,并将这种方式向普通群众传播,从而克服因其懒惰而陷入的不自由状态。正如康德在讨论神职人员对信条的解释与反思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仍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和公开地向世界阐述他们在这里或者那里偏离已被采纳的信条的判断和洞识,以供检验;而其他每个人不受职责限制的人就更是这样了。这种自由精神也向外传播,甚至是在它必须与一个误解自身的政府的外在障碍进行斗争的地方”[注][德]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康德对理性公开使用的论断,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来讲,可以说它的精神乃在于“解构”神学传统的独断统治。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种解构思维中。启蒙精神拒斥的是外在他者的限制,尤其是蒙昧宗教的精神压制,现代道德危机的诸多表象即导源于此,从“受监护状态”中挣脱出来的现代启蒙道德战胜了属神的道德,却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了内部争斗。启蒙精神对自由的阐扬为属人的道德追加了一种理性论证负担,我们不再能够依照上帝来为道德奠定根基,而必须自我负责、自我论证,或者按照韦伯(Max Weber)的说法,“今天的命运,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注][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哈贝马斯接过康德的问题意识,发起自己的追问:“抛弃了上帝的人的主观自由和实践理性能否为规范和价值的约束力提供有力的证明?”[注][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面对此问题,现代道德哲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由此诞生了情感主义、现代功利主义、元伦理学以及现代美德伦理学等诸多现代道德论证策略。这些道德理论从不同方面为启蒙之后的现代道德提供了论证方案,却也导致了一种多元论证甚至论证冲突的离散局面。道德情感主义宣称道德乃是个人情感的表达,现代功利主义进一步强调道德乃是功利的计算,而现代美德伦理学则宣称道德乃是品性的涵养,如此等等。但有一点却是它们的共有特征,即都认为道德不是普遍的,更不能是真理,因此没有知识内涵。
毫无疑问,经过现代哲学对启蒙的重新关注与诠释,启蒙在隐含着抵制他者力量的同时亦走上了自我消解的道路。依哈贝马斯所见,“现代的首要特征在于主体的自由”[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可是,“主体自由”这一被康德视为人之自主与解放的最为根本的保障,并使“理性的公开运用”得以可能的要素,却遭遇误读并发展成无限制的个体主义,恰如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个体主义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具有无可怀疑的优先性,这是现代道德秩序概念的核心特质。……现代人的错误,便是认为这种对个体的理解是理所当然的。”[注]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对康德自由概念的理解由此也就变成了一种个体性的、自我主义的自由,此种自由观泛滥于现代道德的论证中,便造成了现代道德合法化危机之证成危机维度的出现。而就当今道德多元主义的现实境况而言,过度强调个人的自主与自由无疑是现代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道德情感主义等坚持道德不具普遍性的道德理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倘若自由被理解为绝对的个体自主,那么任何的道德理论都可以从完全的个体主义自由角度来寻求其证成的可能性。
当然,现代性道德危机的出现并不仅仅被限定在对自由的误读这一个层面上。可以说,假使理性公开运用的的启蒙观念是理性本身的唯一效用,那么现代道德危机至少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并不会导致危机的出现。但是康德对理性的另一个维度的分析却进一步加重了现代道德的合法化危机,它使得合法化危机在证成危机的基础上导向了另一个维度——现实危机。
二、工具理性的僭越:现代道德的现实危机
康德在将启蒙的核心保障因素定义为自由,并进一步将其设定为自由地对理性加以公开运用时,同时提到了其对立面——“理性的私人运用”。康德指出,人们在“……某个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者职位上对其理性可以做出的那种运用”[注][德]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即为理性的私人运用。“康德认为,当人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a cog in a machine)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人的……康德这样说,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盲从,而是要求他们在运用自己的理性时,要适应这些受限定的情况。同时,理性必须从属于所考虑的特定目的。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运用。”[注]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 in Paul Rabinow(ed.),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one, trans., Robert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303-320, p. 307.
作私人运用的理性并没有自由可言,如果仅仅将我们的理性局限于此,就仍然是未经启蒙的,对“理性的私人运用做这样的解释,其意涵在于对合法权威意志的无条件服从”[注]Ciaran Cronin, “Kant’s Politics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3, Vol. 41, No. 1, pp. 51-80, p. 59.。只有对理性的公开运用才是启蒙的真正诉求。为了人类的公共事务及人类福祉使用理性,或者说,使用理性论辩正义与善等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的价值理念,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这是康德对理性公开运用的根本规定。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将理性的私人运用理解为达成自我设定之特殊目的的力量,即具有无条件性质的权威使受其指导的未启蒙者受限于如下宣称,即他们必然被关联于实现目的的工具中。而将其公开运用理解为批判力量,即启蒙者通过自由运用理性能力摆脱意志的受监护状态而将批判动能运用到人类共同体相互间关系之协调中。这就是说,康德虽然揭示出了理性在不同层面的运用,但对他而言,真正昭示启蒙精神的乃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而在特定岗位上用职责以及外在权威的命令来使用的理性实际上像宗教这种外部限制一样,限制了人类理性的发展,它是非自由的从而也是非启蒙的。
分析康德论证启蒙的基本理路可以发现,康德首先以否定的方式界定了启蒙,赋予启蒙以一种对过去状态的超越性质,藉此获得不同于旧时状态的新的精神气质;其次,康德将这种新气质的获得归功于自由,只有人获得自由运用理性的空间才可以获得启蒙的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康德赋予启蒙以批判的力量,批判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反抗,反抗蒙昧、反抗权威、反抗一切理性之外的他者控制。所以,在康德这里,启蒙既表现为一种摆脱外在限制的力量,也表现为自我反思的力量。启蒙标志着人进入了一种新的环境,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这种与过去的断裂使人得以只依靠自己就可以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规划。因而,在康德启蒙意识中不仅有启蒙的断裂意识,而且有启蒙的规范性诉求。
不幸的是,现代哲学似乎误解了康德,进而误解了启蒙。自从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呼吁超人道德以来,回荡在西方上空的理性力量似乎是那洗澡水中的婴儿,随着洗澡水一起被泼了出去。尼采之后对启蒙理性发出的最为深刻的反对之音来自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启蒙辩证法》。本书的开篇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立。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启蒙意在祛除蒙昧、解除神话对世界的遮蔽、最终用理性知识替代那些虚幻的信念。“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思想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动力量。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对立面,是因为启蒙用更好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来反对世代延续的传统的权威约束。之所以是神话的反动力量,是因为启蒙使个体获得了洞察力,并转换为行为动机,从而打破了集体力量的束缚。”[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启蒙无疑要终结神话魅惑而走向超自然力量的终结,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最终却悲观地断言:“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将启蒙理性等同于神话,虽然曲解了康德的意思,但是就其所批判的维度来讲,却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理性功用的视角。
启蒙最初是以反神话、反宗教的姿态获得其合法地位的,这是一个已然获得共识的结论,但是经过现代哲学家的剖析,特别是韦伯将社会合理化过程定义为技术与计算、组织与行政管理的理性化之后,启蒙理性的批判力量渐次消失,人们逐渐将启蒙理性理解为实现人们特定目标的目的理性,特别强调理性的功能主义使用,这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启蒙理性越来越显示为工具理性之意涵所在。“对源始的疏远如果意味着解放的话,那就意味着启蒙成功了。但神话力量证明自身是一种延缓因素,它阻碍了人们所追求的解放,也不断拖延源始对个体的约束,在个体看来,这种约束就是监禁。”[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人从反神话过程中获得的自由重新丧失,启蒙与知识和权力重新纠结在一起,并获得了如神话般的控制力。
台湾著名学者黄瑞琪曾如此评论:“启蒙思想家对人类理性抱着很高的期望,他们推崇的理性是现代性的重要内涵。这种西方理性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方面最为显著,意图有系统地、有方法地去理解、预测及控制自然。”[注]黄瑞祺:《现代与后现代》,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46页。这也是韦伯的社会合理化主题的基本思路,但是如果以韦伯式的合理化来理解世俗化的世界,那么,“彻底合理化的现代世界只是表面上实现了解神秘化;恶魔般的物化和沉闷的孤立等诅咒还是萦绕不去”[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工具理性在摆脱宗教控制上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用,在此过程中其工具目的效用之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欲望日渐强烈,这样一来,“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哈贝马斯由此断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现代性批判的要旨是:“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如果反思性和批判性要求不再是理性本身内在的品性,那么“这种理性就是纯粹的自然统治的理性,它就此而言还是压制的原则,是本质上独立的东西”[注][德]T. W.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因而,就哈贝马斯而言,现代哲学对理性的理解并不是理性本来的面目,从康德启蒙理性的分析而言,也确实印证了这个结论,理性在启蒙之初充当的是批判者而不是监护者角色,后来的发展只是对启蒙理性的“扭曲”或者片面理解。
当现代哲学家以工具理性的单向思维模式来理解现代道德的生成与运行模式时,这种非启蒙模式便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普通大众在处理道德问题时所采取的基本行动方式上。因此,现代社会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情况。如果当信守承诺、互相尊重、见义勇为等等这些道德规范都在工具理性下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话,可想而知,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将会走向何方,人与人之间的行动的协调又会在策略性的工具目的关系中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道德的现实危机实际上来源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的工具理性态度,这种工具理性态度在康德的理性的私人运用中被揭示,但现代思想家们对它作了不恰当的阐发。
所以,康德对启蒙精神的分析实际上先知般暗喻了现代道德可能发生的两种危机:一是对自由的阐发所引生的对自由的误读,从而导致现代道德的证成危机;二是对理性的误读而引生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工具主义倾向,从而导致现代道德的现实危机。当然,两者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界限,因为现代社会的两种危机本身就是相伴而生的,证成危机会导致现实危机,现实危机也会加剧证成危机并催生出新的道德论证策略。而且就其启蒙根源来说,理性的运用方式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打破这种关系的是现代哲学家以及作为现实道德生活中的行动者。公允地说,康德本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责任应由现代思想家来承担。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康德所解读的启蒙精神的误读,导致理性主义走入现代性危机。在以价值多元自我标榜的现代社会里,在多元主义被接受为一种理性事实的今天,现代道德理论所遭遇到的双重危机本质上指向对道德普遍性与知识性之理性诉求的背弃。
三、现代道德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普遍性与知识性的缺失
按照泰勒对启蒙之后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合法基础的理解,“一旦社会不再有一个神圣结构,一旦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或上帝的意志,这些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在某个意义上就可以嬗变由人”[注][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页。。承继启蒙的精神矛盾,秉承神圣结构崩塌后的自我立法精神,现代道德哲学的合法化危机便逐次展现出来,各种论证策略间不可通约的结论造成了现代道德的证成危机,而依据这些理论指导的现实道德生活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实危机。隐藏在这些纷争背后的乃是对康德理性公开运用与私人运用之区分的非理性化诠释,由此分离出两个基本倾向:或者是导向感性,或者是导向工具理性。前者“试图把道德语言的认知内涵整个地揭示为一种幻想……道德判断和道德立场的表达背后,隐藏着的只是主观情感、主观立场和主观抉择”[注][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而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对新科学力量(the power of new science)的信仰,希望把这种力量应用于思考社会和道德问题”[注]Hillary Putnam,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9.,其实质乃是自由的任意化以及工具理性的彻底化,它们企图以科学观察者而非道德参与者的视角将道德规范作客观化解释,从而仅仅关注现代道德之启蒙路向上的断裂意识,却并未意识到断裂意识之外以普遍化为宗旨的规范性诉求。
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知并给出理性出路的论证策略,实际上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继者哈贝马斯来完成。“对哈贝马斯来说,将启蒙作为一种支配力量来加以激进地批判,其最主要的后果是导致理性概念的混乱,从而破坏了西方理性文化自身的理性遗产。”[注]Martin Morris, Rethinking the Communicative Turn: Adorno, Habermas and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ve Freedom, New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1, p.55.重新审视康德的启蒙论述及对现代道德状况的影响,乃是接续理性主义传统、拯救现代道德危机的唯一可行之路,而这一方式的正确路径则在于认识到现代道德的普遍性与知识性缺失这一实质。现代启蒙语境下诞生的诸多道德论证策略虽然还在某种程度上坚持道德规范的可论证与可辩护性质,但已经以不同程度的相对主义背弃了启蒙之理性精神对道德之普遍性与知识性的原初诉求,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甚至于否定理性可以籍由自身的论证力量来为道德规范进行论证以获得普遍性认同。
启蒙在经验世界的日常道德实践中确实间接导致了邪恶面孔的出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盲目否定启蒙的理性诉求,而是需要重新发现启蒙的论证潜能。这里首先要做的是重构一种适合于摆脱现代道德危机的理性能力,这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构建现代道德秩序的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如果现代复杂社会的行动者依然在康德的理性公开运用与私人运用意义上来构建现代道德秩序,那么他们依然无法摆脱现代道德的危机趋向。因为虽然康德对理性的运用方式作出了基本界定,但是就康德的理性公开运用而言,其依然是在主体性哲学视域下以个体独白方式设定理性潜能而存在沦为工具理性的隐忧。这一点,可以从哈贝马斯的以下论断中得到印证,他说:“康德放弃了传统的典范地位,并赋予现代事物以平等的地位;将思想转化为一种诊断工具,使思想卷入自我决定(self-reassurance)的混乱过程中。”[注]Habermas, “Taking Aim at the Heart of the Present: On Foucault’s Lecture on Kant’s What is Englightenment?”, in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ed. and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9, pp.173-185, p.176.
现代道德的自我决定观念本身是启蒙留给现代精神的宝贵遗产,它不再将那些未经理性反思的宗教、传统、习俗、生活样式基础上的典范作为其盲目效仿的对象。但其同时也造就了多元主义的理性事实,而且理性在多元视角下被不适当地落实于同样具有表面上的多样性的道德领域,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道德的合法化危机。由此,现代道德对启蒙工程的现代拒斥转向了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普遍性诉求的批判甚至完全否定。但实际上,康德并未否定理性在现代道德中的地位,而是要在理性自我决定基础上确立新的基础,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及其后来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实际上要回答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实践理性是否像理论理性指向事实世界的真理一样,可以具有真理性。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康德自由地公开运用理性这种启蒙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理解康德对启蒙作为理性的公开运用的解释,需厘清隐含在这一方法中的两个本质方面:其一,我们必须将康德的论证看作对理性、批判以及公共文化的更广泛的争论的某种调停;其二,我们需要在自批判哲学的脉络下解释他的论证,将其看作对我们合理论证的有效性条件的反思性检验。[注]See Katerina Deligiorgi, Kant and the Culture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4.正是基于以上两层含义的思考,为了反对启蒙辩证法反启蒙的消极立场,重新寻找现代道德普遍性与知识性的根基,哈贝马斯指出:“对现代性的不满并不是植根于工具理性的合理化,而是其未能在适度的方式下发展与制度化现代性理解世界的不同理性维度。”[注]Thomas McCarthy, “Reflection on Rationalization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Richard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5, pp.176-191, p.176.如果道德只是功利计算,那么计算的标准就存在问题,我们用来指导自己的某些计算方式或许根本无法被采纳,而功利主义的“福利最大化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精确计算的原则。“在各种可能的、相互冲突的计算方式指导下,我们根本无法明确说用目前的计算方案规制我们的生活或应用它是理性的。”[注]Logi Gunnarsson, Making Moral Sense: Beyond Habermas and Gauthier,London: Cambridge, 2003, p. 4.所以,康德对理性在启蒙中作用的阐释,深层次上隐含了对现代道德论证结构的形式条件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核心是澄清普遍化的论证结构之于道德规范的证成规则,功利主义则放弃了这一层次而转向对经验现象背后的匿名规则的客观把握,从而未意识到康德所谓启蒙针对的是自我启蒙者的意识结构。这种启蒙意识的区别于经验观察者视角之处正在于对危机意识的理解的参与者视角,因为一种危机之称为危机并不在于其可以观察到的外在现象,而在于处于危机中的行动者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并试图克服危机进入正常状态的自我意识,“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就心照不宣地赋予其一种规范意义,即危机的解除代表处于危机中的主体之解放”[注]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trans., Thomas McCarth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80, p. 1.。启蒙的现代危机的自由与工具理性误读滋生出的功利主义倾向恰恰因应了韦伯等人的批评,从而成为一种宰制力量主导下的危机现象,却并不能进一步生成危机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论证条件的反思。
综上所述,要想解决现代道德的混乱状况,克服其陷入合法化危机的境地,必须重塑道德的理性、自由与平等的崇高特性,恢复被康德奉为与宇宙星辰一样具有普遍性与知识性的道德法则的神圣地位必须重新发挥哲学的批判潜能,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湮灭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所定向的道德知识的真理性,从而既维护其普遍性又坚持其知识性。而这里的自由概念并不是盲目人性的个体主义自由,而是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道德规范规制下的自由;这里的理性也不是主体理性,更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哈贝马斯所发掘出来的、得自于语言学转向下对主体间性结构有所揭示的交往理性。通过自由沟通而达至共识的交往理性至少可以为现代道德危机提供两方面的保障:一方面,交往理性是一种自由的反思理性,它从参与者视角以对危机的自我意识来反思危机并超越它;另一方面,交往理性也是一种论证理性,它克服了康德先验理性的强制性特征而赋予每一个参与论证的行动者以论证权利,来共同寻求具有充分理由的理性共识。通过交往理性的这两方面的作用,现代道德的合法化危机不仅能得到正确认知,而且可以获得走出危机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