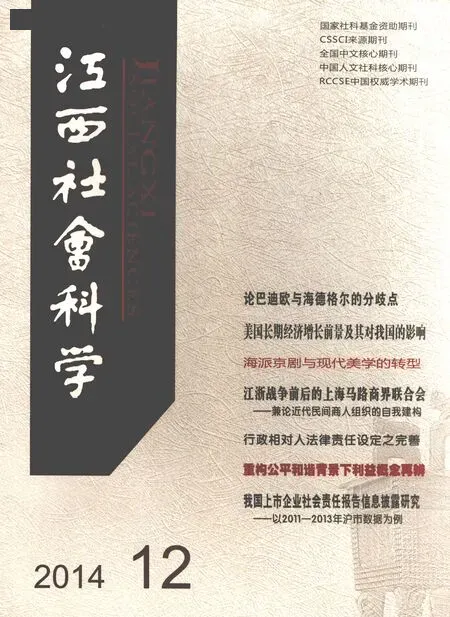从起点到观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界碑的一种思考
■李小玲
一、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争议
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学界聚讼纷纭,以前学者多认定为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时期,后来则有学者提出晚清说,还有的从历史分期或文类兴起的角度予以概说。作为一个学科缘起的标识,它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区分度问题,王富仁认为:“起点对一种文化和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关系着对一种文化和文学的独立性的认识。”[1](P75)背后“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2](P91)本文试图从现代文学的起点出发,通过解析每一种文学史叙述方式背后潜在的观点,对现代文学界碑作出新的阐释。检讨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出并确定民间文学的价值是文学观念裂变与转型的标志。
总括起来,关于现代文学起点,学界大致有如下五种意见。
(一)五四说
这种观点以20 世纪50 年代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史稿》的这一定位影响深远,正如王瑶所说:“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部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著作。这些著作尽管各有特点,但它们所阐述的都是由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十年间的文学历史;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起讫时间是明确的,并未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怀疑。”[3](P175-176)《史稿》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文学史书写的依据和立足点来解释现代文学的“性质”,指出:“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4](P5)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被王瑶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叙事话语中,文学的性质为政治意识形态所笼罩,文学的政治属性被当作切割文学“过去”与“现在”的分水岭。
(二)1917 年:新文化运动说
20世纪80年代后期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颇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文学史教材。它明确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是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其理论前提是“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而现代文学的概念揭示了文学的“现代”性质,即“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显然,钱理群等人是以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来进行分期的,他们认为,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正是这场运动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和契机。”[5](P1-4)由此促成了文学的现代转型。90年代后期,王富仁等学者提出“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开端,五四新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6](P82)作者从语言类型的转变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角度加以阐释,与钱理群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
(三)晚清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这种观点最初来自于国外的汉学家,后来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回应。李欧梵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 至1911 年的16 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所谓现代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文学报刊的发展,二是“新小说”理论的提出,三是新小说的实践。[7]王德威强化了“晚清说”:“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他明确指出,他所强调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并不是指涉启蒙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等人所力求的改革,而是指狭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谴责小说等等,并将其视为被压抑的现代性。[7](P123)
“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文学”等概念,将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上溯到19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之交,都可以看出“晚清说”观点的影响。
(四)民国文学说
民国文学说是以历史断代来划分文学起点的。陈国恩指出:“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他认为,“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能消弭关于现代文学起点上的诸多分歧,而且,“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8](P82)
(五)通俗文学说:以《海上花列传》为起点
范伯群以“现代性”为准的,认为:“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是以1917 年肇始的文学革命为界碑,可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要比这个年代整整提早了四分之一世纪。”[9](P15-16)而“《海上花列传》从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等方面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作为中国文学‘转轨’的鲜明标志,应该当之无愧”。并且韩邦庆使自己的小说走上现代化之路是不自觉的,“但惟其是自发的,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推进与文学发展的自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学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的阳光雨露催生的必然结果。”范伯群进而指出,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与启蒙主义有内在联系,而“中国早期的通俗社会小说——谴责小说,已经具备了启蒙的因素”[9](P17)。
栾梅健认为《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开山之作”。可见,“通俗说”,细化为《海上花列传》说依然是以“现代性”作为文学史分期的重要乃至唯一依据。[10]
二、从起点到观点:文学批评的多元化
上述诸种观点为现代文学史的阐释提供了多元的叙述框架和可能性,由此,既显现了这一学术话题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也折射出文学界碑乃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上述观点稍加梳理,便可发现,对于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学者们或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依据(“五四说”),或是以历史断代来划分(“民国文学说”),或是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至于其余几种说法,细究起来,都是以“现代性”为依据。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革命的意识形态来构建新文学史观,乃是出于新政权执政党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当时,教育部将中国新文学史定为高等学院中文系必修课程,并对教学内容提出明确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11](P126)
《史稿》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将新文学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方向均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方向来决定的。《史稿》可谓是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命题作文,其注重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研讨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式”,“许多晚一辈现代文学研究家,是以《史稿》为入门的向导的。”[11](P133)其本身亦被视为意识形态下“体制化”文学史写作的案例。这也是后来常被学界诟病的地方,对文学起点的新探寻也往往是以跳出政治话语干扰为前提,试图卸下政治的禁锢,获得对文学史的新的解说。
“五四新文学运动说”将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重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早期“五四说”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新文化运动并不等同于五四运动,作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的胡适就曾强调过两者的差异,并为一场文化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而深感遗憾。“民国文学说”虽舍去了诸多枝蔓,但偏于笼统,以历史分期作为文学史的分期,难以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内涵,至于“现代性”概念的解说也是在反对“五四文学说”的背景下脱颖而出的。王德威的“晚清说”,与其说是对晚清文学的肯定和张扬,毋宁说是对“五四文学说”的拆解。王德威认为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而以其实很儒家式的严肃态度,接受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且树之为唯一典范,并从而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主义形式屏除于正统艺术的大门外”。于是,他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重新解释“跳开五四知识分子所设立的限制”。[7](P121)据李欧梵的观点,“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12](P2)汪晖也认为,“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涵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而且“从十九世纪前期直至二十世纪,现代性概念一直是一个分裂的概念”[7](P2-5)。西方学者Taylor 也提到“所谓现代性,表面看来是从欧洲发展而来的,事实上它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而西方的这一套现代性又是充满矛盾的,其中包括了理性、科学,但是也包括了其他因素,如个人因素、主体性因素、语言和现实的因素。”[12](P3)正是因为“现代性”的歧义纷繁,导致“‘到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modernity)在哪里?’这个问题,已被一再提出”[7](P121)。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本身就是变动不居的,而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且对号入座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必然会因各自选取的坐标系的不同而发生观点上的位移,所以,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看似纷繁复杂,实际上,无非是不同学者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理解各有偏差而已。
问题由此产生了,“现代性”概念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以西方的文化文学现象为基准的。如郜元宝所言,王德威在强调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时,“也设立了一个西方标准的现代性模式,从而严重误解了五四以后文学中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性因素。”[13](P17)以此看来,现代性模式取之于西方而不是立足于本土,这就存在着一个西方理论与中国土壤是否恰适的问题。是否真的存在如汪晖所提到的“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现代性”?[7](P13)Taylor 在《个体的来源》一书中就质疑过现代性的普适性价值,“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否能在第三世界国家行得通的问题”,他甚至断言“现代性”“这种文化模式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当它接触到其他文化之时,很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12](P3)。
如何借鉴和引入西方术语和理论,或许,鲁迅的“拿来主义”在当下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拿来”意味着不拒斥,意味着表现更为主动,即不流于对西方理论的隔绝,尊重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间的交流与碰撞,但绝不是以西风压倒东风,中国的文学史实不能仅是充当西方理论的试验场,更不能将西方模式作为中国理论和现实的模板而“削足适履”。回答和应对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还必须回到中国文学本体,建构自己的理论。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说:不能套用西方理论和艺术标准来剪裁中国的审美,衡量中国的艺术标准。[14]
三、新的界碑:民间文学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在笔者看来,新文学的界碑不能以政治为标杆,因为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它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但同时,也不能以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为坐标,依葫芦画瓢,牵强附会。因为,人的思想一旦被限定在某种思想体系中,“把本土的历史看作世界性的”,那这种“世界性”将“使我们忘记了自身所属的话语空间的类型。[2](P91)因此,跳出政治及西方的诸种理论预设,由外围转入本体,基于中国文学的现实也就是事实本身作出判断和结论,或许是更为可行的办法。
检视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文学观念的裂变是以对民间文学的发现和重视为前提的,此后,文学观念的核心和范式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作为汉语概念,民间文学的引入是与胡适领导的白话文学运动紧密相连的。1916 年3 月,梅光迪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入手,此无待言。”[15](P208)梅光迪首次从西方输入民间文学概念,并用“俚俗文学”一词予以解释和界定,且在括号中以“Folklore”诠释之。“Folklore”意指“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包含有文学的“民间性”和“民众性”特点,和白话文学运动“走向民间”的指向一致,因此,胡适也常将民间文学、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交叉使用,用以区别于上层文学、文人文学和文言文学等传统文学。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往往是一个杂糅的概念,其精神实质与民间文学是吻合的。很显然,白话文学运动代表的只是文学观念的转向,它既不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参照物,也不等同于五四运动,“五四”是个政治的力量,而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则“完全不注重政治”[16](P807)。
白话文学运动将文学的视点转向了民间和民众,由此催生了具有本土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也拉开了以民众的语言来表达民众情感的现代文学的序幕,或可以说正是民间文学的“民间性”和“民众性”为文学注入了新的内涵,现代文学才得以应运而生。
(一)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确认促成了文学的现代转型
白话文学运动常被视为语言形式运动,但语言的变革不可能是独步而行的,新的语言形式承载着新的精神内核。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人倡导白话文,但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从未想到要涉及文学的范围去,而白话小说的作者,亦从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中国的正统文学”[17](P6)。“他们办教育,往往是一种‘开通民智’的心理,他们办‘白话报’,自己却看文言报。他们说话用白话,写诗写文章得用文言,他们永远把社会分成两层阶级。”[18](P436)胡适则是“第一个肯定白话文的尊严与其文学价值的”[17](P6)。他明确指出:“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19](P329)而且,“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20](P15)胡适最为夸赞的是那些情感质朴、富有生命活力的民间文学,其白话文学理念已包蕴了民间文学的精神内核。胡适对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确认促成了语言的变革和文学的转型,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由边缘一跃而进入正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史的走向,可以说,正是民间文学价值的确认催促了现代文学的产生。
(二)自觉的文学意识
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唯有自觉,方能有所推进。胡适曾多次提及文学自觉意识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学从古到今,都有许多白话的成分,“但是就从来也没有人自觉的,意识的来做白话诗。”[18](P435)在总结五十年文学时,他又提到:“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史仍旧与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有同样的一个大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便是一种有意的主张。”近五年的文学革命,“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便是五年来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19](P262)他认为文学革命之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21](P152)
(三)“人的文学”作为“民的文学”
1918年,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就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22](P272)胡适也强调: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18](P277)胡适倡导的“人的文学”(litteraehumane)与“人文运动”(Humanism)相关联,即“不满意于中古宗教的束缚人心,而想跳出这束缚,逃向一个较宽大、较自由的世界里去”。他以为,“人的文学”是相对于庙堂文学而言的,“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21](P160)可见,这里的“人”并不指向王公贵族等上层人物,乃是作为普通的人的存在,或类同于“民”。胡适提倡“人的文学”且作为“民的文学”的符号揭开了文学史新的一页。
(四)对启蒙的超越
新文学运动常常被誉为面向下层的启蒙运动,但就笔者看来,新文学运动的诞生就根本来说,它不是面对下层的启蒙运动,而恰恰是对启蒙的一种超越,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面向上层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启迪,即改变和纠正上层人物还有知识分子对民众和民众知识轻视的一种偏见,这和前面所提到的“人的文学”作为“民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
王德威将胡适作为五四知识分子代表,并给五四知识分子贴上启蒙、理性、革命等标签,[7](P123)但这一定位并不切合胡适实际。相较于启蒙运动,胡适坚持“比较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23](P172)。笔者以为,这一坚持并非无心之举,乃是反证了他对启蒙运动本身一直保有的一种警惕。“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4]启蒙运动的权威意识乃是将自己高悬于民众之上,如果没有对启蒙的超越,根本就不可能有“民的文学”的发现,有对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确认,有对民间文学的一种自觉意识。
不是作为启蒙的产物,而是启蒙的超越使中国文学的属性和价值有了新的评估体系,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新的界碑成为可能。
[1]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2](日)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J].董之林,译.文艺理论研究,1994,(1).
[3]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6,(5).
[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M].北京:开明书店,1951.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刘石.关于胡适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J].文学评论,2003,(4).
[7]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C].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8]陈国恩.关于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9]范伯群.分论易 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0]栾梅健.《海上花列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N].文汇报,2006-05-09.
[1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2]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3]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J].上海:复旦学报,2001,(3).
[14]文化部召开文艺界座谈会.他们都说了啥?[N].中经文化产业,2014-10-25
[15]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
[16]胡适.胡适全集(第2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17](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8]胡适.胡适全集(第1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19]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7.
[20]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7.
[21]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2]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3]胡适.胡适口述自传[Z].唐德刚,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