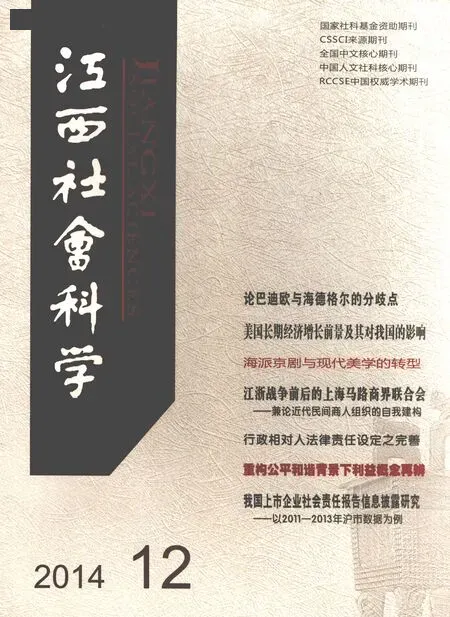海派京剧与现代美学的转型
■陈 伟 王 展
文化艺术领域中使用频繁而广泛的“海派”一词,起源于对上海的京剧和书画艺术的称呼,具体的“海派京剧”概念却始终未曾获得业界明确、一致的认同。本文所使用的海派京剧概念,不是泛指地域范围上在上海地区演出的京剧,也不是泛指艺术表现上与传统京剧基本规范不相符合的“外江派”;而是特指自1867 年京剧南下进入上海,以传统、定型的京派(也称“京朝派”)京剧范式为基干,深受上海本地开埠后发达的工商社会影响和文化转型熏陶,传递新的社会观念,表达新的审美体验,引领新的审美趋向,并结合商业经营和运作特点,在剧目题材、道具布景、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强烈革新意识的京剧流派。本文拟就海派京剧的渊源、特点及其美学特征等方面加以探讨,力图推进海派京剧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一、“海上竞逐”的商业大潮与海派京剧的诞生
京剧兴起于清乾嘉时期的帝都北京。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伶人高朗亭率扬州“三庆”徽班入京为高宗贺八十大寿,祝寿戏演毕,三庆班留驻北京继续公演,得到各方普遍欢迎。受其影响,别的徽班也陆续抵京演出,其中较著名的有四喜、春台、和春等,与三庆合称“四大徽班”。四大徽班的表演各具特色,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之说,即三庆班以连演整本大戏见长,四喜班以演昆曲戏取胜,和春班擅演武戏,春台班以童伶著称。[1](P3)一般认为,四大徽班进京标志着京剧发展历史的滥觞。随后的清乾嘉年间,汉调演员开始入京搭徽班演出,两派艺人同台切磋促使徽、汉两调在艺术上进一步融合,出现了“徽汉合流”的艺术变化。这个变化带来的显著特征是:演出剧目和表演手法得到丰富和拓展;改变了诸腔并呈的局面,以皮簧声腔曲调为主;舞台唱念语言以中州韵为规范,沿用部分湖广音。“京剧是在徽班内部逐渐孕育、演化而形成的,是徽调、汉调、昆曲、梆子互相交流、结合、融化,从而产生的新剧种。”[2](P76)加之在实地演出时不断依照北京的地区特点和观众需求进行修正,大约到了清道光二十年(1840),京剧这一独特而极富魅力的艺术种类便在北京基本形成。它作为中华古老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继承与发扬了中国戏曲的优良传统,通过不断积极吸收、融合、提升各地方剧种的声腔、板式、剧目、表演手法等特色,在数十年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身一整套的基本规范和表现形式。
京剧在北京形成后,由于受到上至皇室贵胄下到平民百姓的喜爱和追捧,其影响范围逐步扩展到全国,总体来说,它的流布路径大致呈由北到南、由大中城市而村镇乡里的态势。据姚民哀《南北梨园略史》记载,清同治六年(1867)京剧正式由天津进军上海。英籍华人罗逸卿于1866 年斥资在公共租界营建了一座仿京式茶园“满庭芳”,1867 年春开张时“派人赴津邀角,置办锦绣行头”,“此京班到申之破天荒”。由于京剧使“沪人初见,趋之若狂”,故同年即有富商刘维忠兴建“丹桂茶园”与之竞争。丹桂茶园赴京邀请三庆等班名角,又去广州置办华美行头,开业一年便“获利颇厚”,不仅在与满庭芳的角力中取得胜利,而且不久即增设分园“南丹桂”,迅速扩大了自身的经营规模和商业影响。[3](P3)自此,京剧在上海站稳脚跟并日益兴盛,“随着京、津两地京班艺人的大批南下,上海开始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京剧艺术中心”[4](P256)。上述京剧南下的史实虽然简扼,其中却包含有丰富信息量,对于理解海派京剧发轫有重要意义。第一,沪上商人将京剧直接“搬”到上海不啻为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商业尝试。整个活动中,他们在上海开埠后形成的工商社会环境里久经历练而获得的敏锐的商业嗅觉、前瞻的商业判断和熟练的商业经营手法无疑得到了充分展露。第二,大量金融资本的聚拢、占有、运作是京剧南下的重要经济保障。全新演出场地的建设、邀约演员的开支、华美行头的购置等一系列环节,均离不开雄厚资本的直接支持。第三,京剧自进入上海之始便一直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除了要与当时本地已有的昆曲、秦腔、粤剧、杂剧、滩簧等兄弟戏种争胜,它自身不同营业场所之间的互相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工商市场的逐利性和残酷性。要而言之,从京剧初离皇城迈入沪上的第一步起,上海这个工商发达的沿海早期都市里蕴含的“海上竞逐”的商业气息对它方方面面的影响就已经初现端倪。
京剧进入上海时距其开埠(1843)已有二十多年。1840 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紧闭的国门,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欧风美雨浸润的城市。西方近代的经济方式、文化思想、生活做派等诸多方面的外来因素在这里和东方文明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上海发达的工商社会基础、先进的文化思想观念和独特的审美欣赏趣味。上海又属五方杂居之地,民众普遍不喜墨守成规,善于用好奇的目光省视新鲜事物;对现实生活充满了热情,乐于关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尤为重要的是,受工商社会环境和西方现代观念熏染,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民主思想萌芽破土而出。初到上海的京剧还暂时保持着传统“京派”的定型模式,演出场地设施考究,票价昂贵,出入满庭芳和丹桂茶园的观众多为官僚巨贾、洋行买办、各界名流,因此在原有消遣娱乐的功能外,京剧又很快成为上海工商社会上层人士重要的交际媒介。一时间,京剧俨然成了流行时尚、身价地位的代名词,“就连英商太古洋行招待客户、广东商人招待卸任广东巡抚都在茶楼包场做堂会”[5](P27-28)。不过这种高端路线独占经营的模式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商业逐利大潮的涌动,众多大小茶园纷纷仿效开设,互相竞争压低票价,努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观赏,京剧真正走进了上海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决定生产,京剧在上海地域经济、文化影响下诸方面的革新变化日渐凸现,“海派”京剧应运而生。在剧目题材上,海派京剧重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求新求变,涌现了大量的创编时事戏、改编西方戏、新编历史戏,在拓展传统剧目的同时针砭时弊,传播进步的思想观念。在道具布景上,海派京剧讲究机关布景、真刀真枪、华美服饰,体现了有别于京派京剧专注虚拟化的戏剧美学特点。在表现手法上,海派京剧不拘一格、大胆创新,融入多种表演形式,以求舞台表演的热闹火爆,革新了京派京剧注重程式化的传统模式。自此,海派京剧以其新颖独特的风格逐渐开启了一道广受观众欢迎的文艺样式之门。
海派京剧之“海”,既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又不能简单理解为在上海地区演出的京剧。从时间上看,京剧初入上海的演出,聘请的是京津两地的京剧艺人,沿袭的是京派京剧的传统剧目和表现形式,这种情况此后从未断绝,“甚至到了1942年袁世海来沪演出时,舞台正中还高悬有‘标准平剧’(即标准京剧)匾额,以与其他剧场演出的‘改良新剧’相区别”[6](P30)。从范围上看,海派京剧以上海为中心呈辐射状,其影响覆盖了杭州、武汉、南京、苏州、南通等南方城市,远超一城一地的局限。从代表人物来看,虽然“伶界大王”谭鑫培六下上海,京剧大师梅兰芳时常莅沪公演,乃至一度定居上海,但显然他们均不属海派京剧代表。海派京剧之“海”,也不能理解为对京派京剧基本规范不加限制的任意突破、胡编乱造。它虽有艺术上的创新,但始终坚持以传统、定型的京剧范式为基干,并未“脱胎换骨”。无论是海派京剧早期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冯子和,还是后来的一代海派宗师周信芳、盖叫天,均认为海派京剧未曾脱离京派京剧实质,而是在其艺术规范上有所发展。周信芳本人就曾于1908年13岁时入北京“喜连成”科班带艺坐科,接受过京派京剧的严格训练和熏陶浸染,为日后的表演打下扎实基础,对此他深有体会:“戏曲有一套传统的舞蹈和表演程式。这是每一个戏曲演员都必须要学习的基本功夫。”[7](P156)海派京剧之“海”,关键在于在上海这片中国最早萌发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商经济和思想观念沃土上,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转型时代大潮中,通过演员和观众共同努力,传统京剧艺术的演出形式、消费群体、审美需求等方面发生了重大革新变化,从而体现出“海纳百川”的艺术姿态和“海上竞逐”的商业意识。这是理解海派京剧内涵本质的一把钥匙。
二、海派京剧对京剧美学风格的突破
海派京剧应运而生后,在发展道路上逐渐表现出与京派京剧不同的特点和轨迹。京派京剧囿于北京深刻的贵族阶层烙印和浓厚的封建意识影响,更多采取在京剧艺术范式定型后小范围的精益求精、不断打磨。海派京剧滋生繁荣的社会大环境则决定了它拥有突破传统“常规”的革新精神与实践品格,形成了自身鲜明、新颖的艺术特点。
第一,海派京剧拓展传统表演内容,涌现出大批深受欢迎的新剧目。海派京剧的新剧目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创编时事戏,如19 世纪末期的《张汶祥刺马》《大清得胜图》《火烧第十楼》(原名《火烧第一楼》)《铁公鸡》《左公平西》,20 世纪前期的《宋教仁》《鄂州血》《潘烈士投海》《复辟梦》(又名《恢复共和》)《枪毙阎瑞生》等。这类创编剧目演绎的故事内容大多皆有实事,不管是重大历史政治事件还是社会轶事新闻,往往于发生不久即被编排上演,充分迎合了上海民众关注现实生活、乐于追新逐异的审美需求。梅兰芳1913 年第一次抵沪演出,受海派时事戏启发后也说:“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这一种新思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年。”[8](P211)随后他尝试在北京排演了时事戏《孽海波澜》《邓霞姑》《一缕麻》,可惜虽一时叫座但昙花一现未成潮流,终究归于平寂。京海两地观众的欣赏趣味由此可见一斑。第二种类型是改编西方戏,如《新茶花》《瓜种兰因》《电术奇谈》《拿破仑趣史》《经国美谈》《黑奴吁天录》等。如果说时事戏因梅兰芳的演出在京派京剧中尚难言绝无,那么改编西方戏实为海派京剧所仅有,京派京剧未尝一见。京派名家尚小云的《摩登伽女》虽亦属搬演外国故事,但一来题材为宗教传说,二来地域为东方天竺,难归其类。[9](P1279)海派西方戏剧目均改编自西方文学著作或近世野史趣闻,是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汇的特殊场所孕育、绽放出的京剧艺术奇葩,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观念藉此得到广泛传播。西方戏演出中异于本土的故事情节、人物造型、生活方式等,也从某种角度上拓展了上海民众的眼界。第三种类型是新编历史戏,如《汉刘邦统一灭秦楚》《王莽篡汉》《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徽钦二宗》《党人碑》等。此类新编剧目沿用历史题材、人物,但多在其中依傍正史或历史演义添枝加叶、自由发挥。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剧目的上演大有针对时政借古讽今的深沉意味。例如1915 年10 月13 日周信芳编演的历史剧《王莽篡汉》首演,“戏中借王莽之尸,把袁世凯骂得痛快淋漓……这个戏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袁世凯篡位称帝的狼子野心,并且在报纸登的戏码广告上,鲜明地写着《篡位大汉奸》”[10](P49)。
第二,海派京剧开启时代之风,彰显了具有现代民主科学观念的新思想。与京派京剧身处京师要地,深受浓重封建气息影响,恪守封建伦理纲常的境况不同,海派京剧活跃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通商口岸,率先呼吸到西方现代社会吹来的新鲜空气,大量具有现代民主科学观念的新思想萌动生发,通过海派京剧这一文艺载体呈现于广大民众面前。其中,宣扬爱国主义、反对民族压迫的有《瓜种兰因》《明末遗恨》《哭祖庙》等剧;鞭挞专制独裁、赞颂民主自由的有《博浪椎》《维新梦》《秋瑾》等剧;揭露社会黑暗、针砭时弊陋习的有《黑籍冤魂》《烟鬼叹》《赌徒造化》等剧;鼓吹男女平等、倡导婚姻自主的有《黄慧如》《老五殉情记》(又名《蒋老五哭灵》)《文明人》等剧。例如《瓜种兰因》(又名《波兰亡国惨》)由海派京剧代表人物之一的汪笑侬编剧,1904 年8 月5 日首演于上海春仙茶园。此剧“述波兰亡国之痛史”,实为借描摹国外之政事抒发国人之胸臆,“以提倡爱国,鼓励士气为前提”。[11]时值清末,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清政府却腐败无能,不断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剧编演的目的正在于警醒民众,如果不热爱国家、不协力抵御外侮,和波兰一样国破家亡的惨剧即在目前。“爱国”的含义在这里已不再是传统封建观念上与“忠君”的等同,赋有现代意义的独立主权国家概念成为唤醒国民、凝聚人心的基本内核。又如《黄慧如》(又名《黄慧如与陆根荣》)一剧则选取了一则1927 年上海本地发生的时事为内容,通过对少女黄慧如与男仆陆根荣不幸爱情遭遇的描写,强烈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恶果,倡扬了女性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吁求。此剧1928 年12 月7 日首演于上海舞台,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轰动一时,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第三,海派京剧演出锐意求变,运用大量讲究商业卖点的新科技与新手法。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乃各国之租界”,“租界多商”。[12](P453)不可否认,“商性”的确是直接调度海派京剧通盘演出的一根指挥棒。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观众,海派京剧从业者调动了几乎所有能够运用的方法、“噱头”来取悦观众,力求演出场面的热闹非凡,以期获得丰厚的商业回报。在演出硬件设施上,早在19 世纪70 年代的上海戏园就使用煤气照明,继而更新为电灯,不仅增强了舞台观赏效果,而且首开演“夜戏”之风,极大丰富了上海市民的业余生活。1908 年10 月新舞台建成则标志着中国第一座完全新式的剧场在上海诞生。“新舞台与茶园完全不同,它采用镜框式的月牙形舞台,一面朝向观众,并且从国外引进了布景、灯光设备与新技术,舞台上方有天桥,舞台有转台,舞台面积大,可在台上骑真马、开汽车,观众席采用横排座椅,有三层楼,可容两千多观众。”[13](P38-39)继新舞台后诸多类似场馆蜂拥而起,为海派京剧标志性特征的连台本戏和机关布景的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在演出表现手法上,海派京剧大量使用精美巧妙的布景,并将魔术、杂技、西方歌舞等元素融入舞台实践,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1928 年天蟾舞台“刻复延至编剧置景专家,排演独一无二之神怪剧《封神榜》,牺牲巨万金钱,购置全新行头,特别机关布景,陆离光怪变化无穷”。“类如金碧辉煌之宫殿,八九尺高之长人(方弼方相真人所扮)……老君所骑之青牛,元始天尊之座骑,口内均吐莲花,花上更立多人;申公豹杀头还原,摘星楼火烧琵琶精,明明是一美女,忽然变作琵琶;五龙桥子牙跳水,骑龙上天等等,可谓极神奇之变化之能事。”[14]海派京剧著名武生盖叫天在排演《西游记》时,曾经携真骆驼上台。“孙悟空穿锦衣,带花帽,骑在浑身挂彩的骆驼背上,这新鲜一招,很受观众的欢迎。”[15](P146)以上这些海派京剧特有的风格,在京派京剧中无疑是难觅踪迹的。
三、海派京剧体现出的美学现代性
从文艺美学视角考察,海派京剧的发展历程及其形成的独特风格,较为清晰地体现了中国从古代社会以和谐为美学重心的古典美学形态,向现代社会以对立崇高为美学重心的现代美学形态的转型。这一切,还要先从中国现代美学形态和美学现代性的缘起与本质谈起。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漫长,它以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为生产力基础,重农抑商、禁锢思想,向现代社会前进的脚步极其缓慢。西方国家则早在17 世纪便由英国带头踏上产业革命之路,以新型的工商经济取代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力藉此迅猛发展,到20世纪已基本完成了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资本不断扩张、寻求世界市场的浪潮中,严守了数百年的中华帝国大门在19 世纪中期被西方列强挑起的战争攻陷,中国随即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资本入侵中国后,联手买办资本共同推进着工商业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在其夹缝中渐渐生成,这在上海、广州、天津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中国沿海通商口岸表现得尤为显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殖民资本经济局部萎缩,中国市场留出的空隙给民族资本经济发展释放了部分生长空间。伴随着民族资本的兴起,一种民族的现代思想文化破茧而出。它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肇始,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以启蒙为实质,崇尚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确立了全新的现代美学形态。“这种新兴的美学形态及其延展的审美文化,在立意上高扬科学民主,在政治上推进富国强民,在手法上注重求真写实,在形式上追求通俗明了,在审美上强调平等互动。其深刻之处在于,把美学精神上的破旧立新与社会实践中的破旧立新联系了起来。”[16]身处社会现代性实践中的中国人民在与帝国主义列强不懈斗争的同时,也致力于寻求把中国从封建的农业社会改造成现代的工业社会的多重途径。审美文化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中国美学现代性的本质属性。
美学现代性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看,实质是工商经济的产物。依历史角度观照,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早在宋代就已萌芽,随后经过了明清两代的继续发展,但始终处在封建经济的严厉压制下,发展进程极其艰难缓慢。19 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资本经济暂时还没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在内地的大片土地上封建经济仍然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但是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由于西方殖民资本的直接强制干涉和“国中之国”租界的存在,使区域社会的经济环境和文化思想得到了迅猛发展。如果说“五四”时期标志着中国美学现代性的正式发端,是从和谐型古典美学形态向对立崇高型现代美学形态的质的飞跃,那么这种质变前的量变累积在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上海就已经集中凸显。就美学思想而言,以资本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美学观念,主要存在于中国沿海的早期都市里,主要反映在早期都市的文艺领域里。海派京剧恰恰与之吻合,成为体现美学现代性的最佳文艺载体之一。一些“五四”精神所包含的进步元素已经开始在海派京剧中酝酿生长,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扬与支持。该时期的海派京剧主要代表汪笑侬、潘月樵、夏氏兄弟等人均有强烈的民主革命精神,在舞台上编演了《党人碑》《潘烈士投海》《宦海潮》《拿破仑》等大量关涉社会政治、切中时弊的时装新戏。潘月樵经常在表演中插入针对时政的评论,素有“议论老生”之誉。除了在演出内容上鼓吹革命思想,海派京剧艺人甚至还直接参与了革命活动。1911年上海光复战役中,潘月樵、夏氏兄弟亲率新舞台成员攻打江南制造局,救出了遭擒的上海同盟会领导人之一陈其美。潘月樵因功被授予少将军衔,后被沪军都督府任命为调查部长。1912 年2 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南京召见潘月樵,授予勋章,并亲笔题赠“现身说法,高台教化”横幅。4 月5 日,孙中山至上海新舞台观剧,为潘月樵题词“急公好义”,为夏月珊题词“热心劝导”。7 月13 日,为表彰上海新舞台诸艺人编演新剧提倡革命,激发国民,孙中山又亲笔书写“警世钟”幕帐相赠。[17](P1-4)海派京剧及其艺人以实践行动生动诠释了现代美学形态的主旨含义,彰显了美学现代性的前进路向,为“五四”精神的确立奠定了厚实基础。
20 世纪20、30 年代是海派京剧发展的鼎盛时期,连台本戏大行其道,机关布景花样迭出,真刀真枪武打火爆,观众大呼过瘾。在美学现代性引领下,作为人的个体自觉意识逐渐觉醒,一种新的审美需求和趋向集中反映在海派京剧中。上海工商社会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较快,海派京剧市民观众的娱乐消费目的多为放松身心释放压力、寻求耳目之娱的自由快适,所以他们特别注目于京剧表演的情节性、节奏感。连台本戏的表演形式,机关奇巧、近身短打、五音联弹的表演手法都符合他们的审美愿望,故而大受欢迎。受关注现实生活影响,海派京剧还表现出“求真写实”的审美趋向。道具布景要真实可感,于是出现了舞台上的真水、真火、真刀枪和真物;故事内容要真实可信,所以《枪毙阎瑞生》《黄慧如和陆根荣》等新闻时事被反复搬演。当1929 年上演第二本《黄慧如》时,“扮演陆根荣的演员还邀请真陆根荣上台,以获得一种真实感,并以此吸引观众”[18](P67)。然而自20 世纪30 年代后期开始,海派京剧发展便逐渐陷入困顿,裹足不前。究其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海派京剧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政治氛围肃杀,社会经济萧条,多数名角避难远走或隐逸辍演,部分观众流失,都给海派京剧的健康发展以致命性打击。另一方面,在新兴娱乐样式(如电影、歌舞、话剧等)和新型娱乐场所(如夜总会、游乐场、俱乐部等)的强势冲击下,海派京剧自身的经营理念和手法走向了过度商业化,甚至低俗化。为了赢取市场份额和利润,部分海派京剧演出甘于自降艺术品位去满足观众庸俗欲求,《大劈棺》《纺棉花》等充斥色情、恐怖成分的剧目泛滥成灾,“恶性海派”制造了演出市场畸形繁荣的虚假表象。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京剧精英们准确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律动,坚持排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宗》《文素臣》等极具爱国热情的作品激励民众。除了在舞台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他们同时还积极投身于救亡活动,组织进步社团进行募捐义演,为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派京剧是传统京剧南下后,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商经济社会环境里孕育生长出的独特艺术样式。它与代表传统的京派京剧并非采取简单对立、对抗的姿态,而是在其基础上的衍生、发展与变革,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京派京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者共同推动中国京剧迈向戏曲艺术高峰。海派京剧的演变轨迹反映出了中国美学形态从古典和谐型向现代对立崇高型的转型,体现了美学现代性进程中从侧重“人的解放”维度向侧重“民族独立”维度的逻辑转折。科学分析这一动向,将使我们站在美学高度上深化对海派京剧的理解,真正掌握它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
[1]黄钧,徐希博.京剧文化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2]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3]姚民哀.南北梨园略史[A].周剑云编.菊部丛刊·歌台新史[M].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4]胡晓军,苏毅谨.戏出海上——海派戏剧的前世今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5]周信芳,卫明,吕仲.周信芳舞台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
[6]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7]曾白融.京剧剧目辞典[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8]沈鸿鑫,何国栋.周信芳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菊屏.汪笑侬述闻(一)[N].申报,1925-03-08.
[10]鲁迅.“京派”与“海派”[A].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京剧在上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2]刘豁公.天蟾舞台《封神榜》之特色[N].申报,1928-08-30.
[13]龚义江.盖叫天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4]陈伟,桂强.现代性视野中的“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之审视[J].文艺研究,2011,(3).
[15]陈洁.民国戏曲史年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16]钱久元.海派京剧的奥秘:钱久元博士论文及剧作选[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