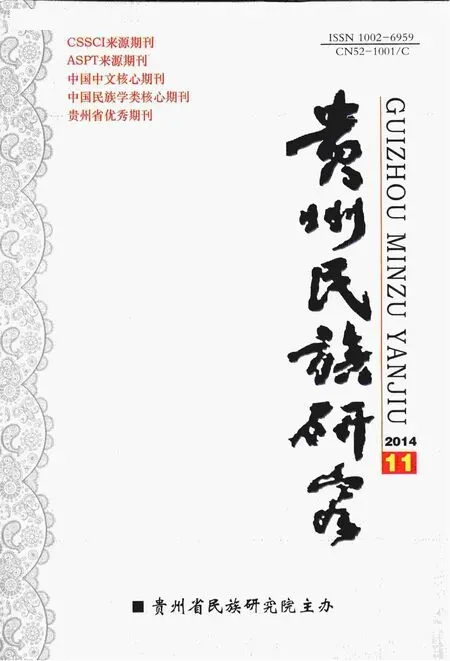关于音乐宗教性、社会性与民族性的思考——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研究
李雨佳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一、从祭坛到舞台的宗教性场所变化
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是少数民族宗教活动的传播手段之一,用以达到宣传宗教观念、升华宗教情感的目的,然而由于普遍的迁徙与定居历史,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相较西方宗教音乐而言,其发生发展过程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缘由,例如蓝山瑶族的度戒仪式音乐即是在赵宋王朝的杀戮历史时期兴起的,并伴随着蓝山瑶族人的逃亡路线呈现相应的社会分布,但当压迫和反压迫斗争停止后,以救苦济世、消灾度厄为宗旨的瑶族度戒仪式音乐便逐渐衰落下来,度戒仪式也演变为多神信仰,因而国内一些文献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纯粹性不足,民族性强过宗教性”,[1]并指出少数民族宗教仪式环境与过程的纯粹性越弱,宗教音乐的场所过渡越顺利,世俗化进程也就越容易,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看待这一问题。
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宗教性是否排斥民族性,以及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场所变化与世俗化进程的关系。从我国少数民族宗教的发端来看,并不是所有宗教形态都是源自神灵崇拜活动,例如佤族的道教信仰,其传播缘起是佤族先民将其作为教化族人德行的一种“授仪礼”,佤族的道教音乐通常用来营造“授义礼”的庄严氛围,因此民族性内涵与行为可以是宗教音乐的起源,且特定时期的民族性活动反而能促使宗教音乐大放异彩,例如“蓝山瑶族度戒仪式音乐的经韵从头到尾都是运用瑶语来吟诵”,[2]仪式音乐中所歌颂的火砖法、棘床法术都并非宗教法术,而是瑶族原始武术的变体,因此瑶族度戒仪式音乐所传递的“神兵保护”信念实际上是民族自尊心的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斗争时期通过宗教仪式起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从而推动瑶族度戒仪式音乐迅速传播,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传播的过程自然伴随着宗教性场所的变化,但只要地域性扩张并没有脱离宗教信仰这一关键性角色,其宗教音乐的属性就没有发生更改,至于其信仰对象是否改变又是另外一回事,而现当代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俨然已经超越了民族性地理环境的限制,创造了从祭坛到舞台的历史性革新。
因此我们要探讨的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以宗教场所变化为基本表现的世俗化进程是否意味着少数民族宗教与少数民族社会的分离。以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宗教场所变化为例,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一般由祭祀巫师主持,阿昌族的马兰调、唢呐铜鼓与葫芦笙等祭祀歌舞在祭坛上的表现形态始终伴随着严格的宗教程序,包括开场的经韵、仪式道具(神轴、法器)的应用、场地环境的配合(许愿、安坛、立堂)等等,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已演变为“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舞台表演形态,代表作品如《云南映象》、《印象丽江》等等,虽然是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舞台反映,但它们的呈现却完全剥离了祭坛仪式的宗教场所,场所的改变能说明少数民族宗教与少数民族社会的分离吗?例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受到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深刻影响,美国本土的基督教福音音乐风格各异,开创了宗教通俗音乐与爵士音乐的先河,除了教堂里必备的祈祷乐、忏悔乐曲目外,各个流行音乐舞台都能发现对福音音乐的借鉴与创造,那么基督教文化与美国种族社会脱离了吗?显然没有。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场所改变与宗教价值取向的改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此美国神学家们提出了“相对化信仰”的概念,指出人们的宗教记忆如何在文化上得以延续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才是宗教音乐发展的方向,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祭坛形式与舞台形式是宗教信仰的相对化表现,用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瑟夫·鲍姆贝克的话说,“宗教信仰本身必须是神圣与世俗的混合体,否则它便无法流传”。[3]
二、从神职人员到表演人员的社会性载体确立
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从“神圣”走向“世俗”是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移为基础,即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是社会公共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绝大部分民族音乐学家都致力于探索少数民族音乐如何顺应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近些年来国内对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功能开发大多都是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将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市场化与世俗化混淆,两者在过程上有相似之处,但追求的实质性社会效益却不尽相同,前者达到的是刺激、表达、分享音乐并获得商业价值的目的,后者则指向宗教发展与社会同步的一体化进程,要求宗教音乐对社会文化产生持续与稳定的良性影响,然而由于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性,其宗教音乐世俗化进程受到的市场助力往往弊大于利。
首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世俗化的社会性载体确立表现为从神职人员到表演人员的市场化过渡,“在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从事音乐仪式行为的主体是本民族的宗教神职人员”,[4]例如哈尼族的莫丕、彝族的毕摩等等,当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承载主体变为舞台表演人员后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这些表演人员并不信仰任何宗教。例如当今活跃的道教“洞经古乐”的民间表演团队,演出人员全是统一培训的艺术学校毕业生,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修养,但对白族、彝族传统洞经音乐缺乏真实的信仰经验,演出过程完全摒弃了相关的宗教禁忌,例如斋戒沐浴、演奏者必须为男性等等,为了吸引大众眼球甚至出现女子穿短裙加入表演行列的走秀环节,可见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载体改变伴随着市场经济对宗教价值取向的弱化与消退。既然社会载体的确立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世俗化的必备前提,那么如何促使社会载体发挥保全宗教音乐价值的主体职能便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音乐形式的社会保存与发展都面临着时代内容的增减问题,其社会承载者有着筛选、更替、创造音乐形式的主体权利,那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承载主体根据社会环境而做出市场化决策的标准与底线在哪里呢?拿西方宗教音乐来说,西方宗教音乐的早期音乐体裁是“格里高利圣咏”的纯音乐形式,现在已发展出“独唱、齐唱、应答唱、交替唱等多声部复调音乐体系”,[5]但深入研究则会发现,形成西方宗教音乐新体裁的舞台容器是附加的宗教戏剧,即一种通过将宗教音乐融入宗教戏剧氛围中的艺术表演形式,它赋予了戏剧演员展示宗教音乐的合理身份。纵观近代西方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无论是田园恋歌、巴歌体、叙事歌还是回旋歌,都是在另一种艺术容器之中注入宗教音乐作品,旨在完整地呈现宗教价值取向,同时促使表演人员的身份变得合理化,对此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欠缺的即是促使社会性载体身份合理化的途径,为什么同样是对音乐形式的改变,中西方宗教音乐价值的保留程度完全不一样,原因便在于“人们对社会性载体的感受左右着社会大众看待宗教信仰的内隐性心理”。[6]因此,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并不是对社会市场性的迎合或适应,而是对社会艺术系统的衔接,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性功能的发挥应与社会市场性需要相互区别。
三、从通神到娱人的民族性功能拓展
“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宗教性承载亦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承载”,[7]同样都是佛教,藏族地区与阿昌族地区的佛教信仰活动各不相同,“民族性”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例如藏族有闻名全国的“沐佛节”、“马奶节”,近些年来藏族佛教音乐的社会传播几乎都是依靠藏民族节庆活动与旅游产业的相互配合,而阿昌族的风俗文化相对保守封闭,以家庭式的佛教活动为主,催生了阿昌族特有的唱经小调,其佛教音乐的社会传播多依靠阿昌族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可见,少数民族区域性所发展起的音乐种类奠定了宗教音乐传播的类型,而超越地域环境则需要依靠少数民族自身独有的民族性来赋予宗教音乐额外的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具体表现为从通神到娱人的民族性功能拓展。
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原初性目的是“通神”,即“将音乐作为献给神灵享用的祭品”,[8]世俗化进程带来的最大改变即是宗教音乐开始被社会大众享有,以“通神”为目的的禁忌空间被打破了,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发展越成熟,通神的功能越退而次之,娱人的功能则越明显。例如白族的“绕三灵”、瑶族的“盘王节”都由最初的通神活动转化为了娱人活动,其中不间断的宗教乐舞表演更是蜕变成了服务于民众娱乐的“世俗之歌”。对此,国内相关文献出现过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从通神到娱人的民族性功能拓展是一种“去宗教化”的表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这种“娱人”行为仍然依附于宗教并通过宗教活动来开展,那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便处于合理的社会适应机制之中。对此,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但想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谈谈这一问题。
英国神学家格雷罗姆·沃德曾说:“宗教音乐的世俗化是宗教信仰变得人性化的标签”,[9]宗教性自然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具备神圣感的内因,但民族性提供给宗教音乐是“人性化”的成分,因为民族性包涵着人们的起居饮食、婚丧嫁娶等民俗生活经验与情感,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社会学家尼德兰曾发问:“宗教信仰能轻易地感化信徒,它能轻易地感化非信徒吗”,[10]宗教音乐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需要的是非信徒的认可,当西方基督教福音音乐与哥特音乐结合,“彻底破坏了哥特音乐的野蛮、黑暗以及恐怖氛围”,[11]让无数非基督教徒为之动容,它依靠的是宗教学说吗?不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民族性功能拓展本身就是为了成全宗教音乐的世俗性,通过超自然成分的减退来促使越来越多的“凡人”参与进来,“一味强调宗教音乐的‘神圣性’会让少数民族原生态宗教信仰在现代化进程中凋敝”,[12]而“民族性”反映的是“人”的本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社会适应的过程必须通过人且只能通过人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围绕宗教性场所的变化、社会性载体的确立以及民族性功能的拓展来体现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承本质。
结束语
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是以宗教为核心题材来传播信仰、强化民族体验的音乐手段,既包涵着宗教产生与发展的精神属性,又融入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两者互为依托共同服务于社会生活,因此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具有宗教性、社会性、民族性的三重内涵,本文从三者的整体框架入手系统地看待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是为了防止研究的片面性。第一是“宗教性”研究的片面,单纯从宗教性的角度来审视宗教音乐场所的改变,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世俗化进程对少数民族宗教价值的弱化,但从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民族性缘起去理解宗教音乐场所变化,便能将其与宗教价值取向的改变区别开来。第二是“社会性”研究的片面,如果仅仅站在社会系统层面考虑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进程,必然会走入社会市场决策的误区,出于避免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市场化与世俗化混淆的目的,笔者对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社会载体身份进行了区分,借助西方宗教音乐对宗教价值的保全来反思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载体身份的合理性。第三是“民族性”研究的片面,人们一般都能察觉到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宗教性承载亦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承载,但多以探究宗教音乐的民族文化特征为主,并没意识到“民族性”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世俗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音乐的民族性与音乐的人性化等同这一基本事实”。[13]本文认为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世俗化是对“凡人”的邀请,代表“人”的“民族性”如果不能与代表“神”的“宗教性”齐头并进,那么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信仰传承则是无米之炊。
[1]张 鹏.近现代宗教音乐发展综述[J],民族音乐,2013,(2).
[2]杨方刚.贵州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综述[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2).
[3]陈婷婷.中国近现代音乐从业者的社会角色研究[D].上海音乐学院,2011.
[4]片意欣.中西方宗教音乐在音乐史上的异同与作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5]陈丽清.阿昌族生活习性、祭祀以及音乐探源[J].中国音乐学,2009,(12).
[6]李媛莉.宗教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1,(3).
[7]周凯模.云南民族音乐论[M],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8]李项阳.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黎锦晖的探索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启示[J].音乐艺术,2013,(6).
[9]龚易男.蓝山瑶族度戒仪式音乐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10]俞人豪.原生态的音乐与音乐的原生态[J].人民音乐,2012,(9).
[11]赵晓娜.论宗教音乐的发展历程与价值[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12]颜 聪.少数民族音乐产业化对现代音乐发展影响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4,(1).
[13]Jonathan H.Shannon.Sultans of Spin:Syrian Sacred Music on the World Stage[J].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