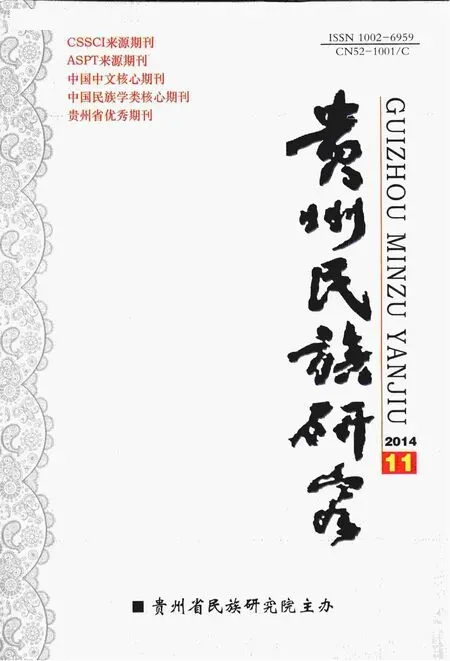西南少数民族自然崇拜折射出的环保习惯法则
柴荣怡 罗一航
(1.安顺学院,贵州·安顺 561000;2.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贵州·贵阳 550004)
自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存在着对自然的崇拜,而这种自然崇拜至今还存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之中。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个主要聚居区,并且少数民族数量众多,其所保留的自然崇拜文化也较为原始和完整。西南地区主要分布有苗、布依、侗、土家、水、瑶、仡佬、白、彝、纳西、哈尼、景颇、傣、藏、羌、壮等少数民族;其所生活的地域较广、地型复杂,民族社会层次和类型繁多;所留存的自然崇拜既有各具特色,又有许多相同之处。自然崇拜就是少数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产生出的崇拜,其实为对物质生产产生影响的自然“物”的崇拜,是对天地山林、风雨水火、动植物等崇拜等的一种“超自然力”的崇拜。究其所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这种“超自然力”的崇拜实际是形成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人应如何遵循自然的规律与法则,由一种对自然“物”崇拜习惯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生活的习惯法则。
一、天、地崇拜体现出族群对自然环境的维护规则
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中,“天”被赋予了人格化的色彩,其可主宰世间万事万物,不同民族所崇拜的“天神”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对他们的称谓有所不同。彝族史诗《梅葛》称天神为“格兹苦”,《勒乌特依》称之为“恩体古兹”;白族那马人称天神为“黑来俄”;[1](P54)在贵州黔东南苗族的苗话中,雷和天是同义词,天神既是“天公”又是“雷公”;侗族则相信“天上以雷婆为大”,视为天神。[2](P126)
对于天神的形象,因民族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象征物,有的体现为牌位,有的体现为人面像、竹筒、树干、白石头等。川、滇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男子在头上扎“天菩萨”作为天神的象征,纳西族用一棵黄栗树作为天神象征,羌族每家屋顶上和每个寨子的神林里,都供着有一块白石作为天神的象征。祭天仪式是天神崇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了隆重的祭天仪式。据李京的《云南治略》记载,元代的纳西族就形成了每年的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为严洁,目的是祈祷丰收、减免灾害。
对于大地的信仰,主要是由于人们生存的需要而对土地的依赖,万物的繁衍,物相的交替都是土地的贡献,因而崇拜土地的自然性质就被逐渐地人格化及神化。根据《释名·释地》中描述“地,底也,言其底下载万物也”,“土,吐也,吐生万物也”。
人们崇拜土地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祈求生产;农作物的生长、结果,收成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土地神的意愿。例如,川西南的藏族和黔东南的苗族都视土地神为丰产之神,庄稼、水果、树木等的生长皆由土地神主宰。为了祈求土地神的保护和恩赐,许多少数民族在耕种作物时会在田地里举行祭祀仪式。昆明西山区的彝族在农历二月播种谷物时要到水田里祭祀;黔东南苗族在正月初二到田地里祭祀;仡佬族正月初三必须到田头、地头去祭祀。[3](P106-107)
族民们希望对天、地神灵的祭祀与敬畏得到神灵的庇佑,通过神圣庄严的祭祀仪式净化族民的心灵,唤起他们对宗族及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热爱,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持族群秩序的效果。[4](P59)对遵循和维护天、地自然环境的族民给了族群内部的奖励及肯定,但对于触犯和破坏了天、地自然环境的族民便要给予一定的责罚。
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会通过族群组织的活动形式,对其依赖生存的天、地自然环境进行保护。通过祭祀等活动来强化民族的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增强民族内部对“天地恩赐”的认同感,成为整个民族约定俗成的规约,同时也成为整个族群应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达到维护自然生产秩序的目的。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主要以农业为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的环保意识在本族中通过文化意识和行为规则贯穿于整个生产生活中,族群组织采用禁止性规则和惩罚规则进行权威规范,形成一套有效地族群控制运作机制。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曾在他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论述道,任何社会规则,犯之者由习惯加以刑罚。这一论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肯定了原始部族的法律是由部族内部裁定的风俗习惯演变而来。可见,族群组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控制机制都来自于族民们千百年演进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习惯法则。
二、对山、水神灵的敬畏形成质朴的民族习惯法
西南少数民族在其原始宗教信仰中,都存在着对山的祭俸。这是因为山与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西南地形复杂、多山环绕,对于世代居住在此的民族来说,山就是他们的地;甚至觉得山与天地浑然一体,与天地同构。因此,对山的崇拜成为了对山神的崇拜,也成为天地间最重要的神灵信仰之一。
山是最早的山神形象,先民祭俸山的最早方式就是直接向山祭祀跪拜。四川石棉藏族也保留了古老的祭山仪式,在他们心目中山就是神,神就是山。森林树木就是山神的毛发,岩石是山神的骨骼,土地是山神的肤体,野生动物是山神喂养的畜群,猛兽是山神的坐骑。如果人们烧山开荒、取石种地、狩猎放牧、伐木采集都是对山神的直接侵害和冒犯,都可能引起山神发怒。而一旦山神发怒就会导致地震、塌方、泥石流等灾害,直接威胁到族民的生命、生产。因此,每年秋收或年初时节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山仪式,杀牲献祭祈求山神的宽恕与保佑。居住在泸沽湖附近的摩梭族人认为山神是除天神之外最为敬畏的另一神灵。摩梭人世居高山,历来十分爱护山林,禁止乱砍滥伐;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神山,神山之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倘若有人随意上山,动了神山的一草一木,自己及家人就会遭受灾难。
在贵州的侗族地区,所有的河流都是崇拜对象,水井河流不能被污染,否则就会损伤“地脉龙神”给全寨人带来灾难。每年春节,侗寨的妇女都要准备酒菜到水井边进行祭祀活动。她们围绕着水井“哆耶”,颂赞水井给人们带来幸福,祝水井终年长流,四季清澈。[5](P136)
纯净的水是东巴教仪式中的必备之物,因此,在纳西族人的世代教育中就要求孩子不能做任何污染水源的事。东巴经《迎净水》中就留有关于保护水源的习惯和禁忌的记载,常见的禁律有:不得在水源地杀牲宰兽、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丢弃污物于水中、不得在水流中洗涤污物等以免污染水源。纳西族人还通过村民大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老民会”,制定全村的村规民约,如果有人违反了习俗不仅会受到族人共同的制裁还会遭到神灵对此的惩罚与报复。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自然力就被抽象为“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渐演变为人与自然神之间的关系。族民们对山、水的自然崇拜昭示着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暇思;对自然山、水之神的敬畏,将族民们的尊重一切生命、尊重世事万物的自然道德观念逐渐演变成了禁忌约束条例,这些禁忌约束在人民心中也逐渐权威化了,从而形成质朴的民族习惯法则。这些被固定下来的民族习惯法,被族群社会所普遍地认可和遵循,在生产生活中显示出普遍的效用和极强的规范功能。
三、对动、植物的禁忌成为世代传承的生态伦理法则
野兽是西南民族衣食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他们狩猎的对象。人与兽的这种关系,在《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许多与动物有关的神灵;在神话传说中人物也都为“兽身人面”或“人面兽身”,例如神农、伏羲、女娲和西王母等造型上都为半人半兽。
哈尼族对狗、虎和蛇,壮族对青蛙、乌鸦、蛇和鸡的都有图腾崇拜的习俗。而白族、彝族、傈僳族等民族则认为自己是老虎的后裔。在布依族中每年的农历六月选定吉日便要举行祭虫神的仪式,除祭献供品之外,还要由巫师念《虫神经》。
独龙族、怒族等民族在狩猎时,都存在着一定的禁忌,忌打怀孕、产崽、孵卵的各种动物。在贵州荔波的努侯瑶中,对鸟的崇拜最为强烈;上山打猎时,喜鹊、燕子、乌鸦是绝对不能猎杀的,特别是乌鸦,谁用猎枪捕杀了乌鸦,谁的枪就要变坏,并且这支枪将禁止用来狩猎。
西南地区的先民们居住的地理位置为低纬度温湿地带,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他们更多地依赖植物性食物,往往以采集为主。在西南先民的植物崇拜中,主要为对树木和森林的崇拜。
苗族认为除天地之外,世间的万物都源于枫树,在《苗族古歌·枫木歌》中就讲述了枫木孕育了苗族的始祖姜央。黔东南的苗族就将枫树视为神树,族人在选择寨址时,都先要在此栽种枫树;村寨边的枫树,就是寨神,严禁砍伐,即便干枯也不能捡取做柴火或他用;但在建筑房屋时,确定要使用枫木做为中柱。[2](P183)彝族、白族、哈尼族、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神林”文化,在他们居住的村寨,大多都有自己的“神山”,山上的林地都会被视为“神树”。这些“神树”是不容冒犯的,因而村寨的族民们都有相应的许多的规范和禁忌,不准任何人违犯,以免给全寨人带来灾难。
西南各民族对动、植物的崇拜,以及有关的禁忌和祭祀活动,不自觉地起到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这些先民们制定的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民俗和维护村寨族群秩序稳定的规约禁忌,有效地约束了人们的不良行为,并且显现出该民族世代传承的生态伦理法则。少数民族的诸多动、植物崇拜信仰,为我们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生活的时代,寻找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路径和有益的启迪。
四、西南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体现的价值与功能
(一)社会功能与价值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朗提出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功能是指局部活动对整体活动所作的贡献。这种局部活动是整体活动的一部分。一个具体社会习俗的功能,是指它在整个社会体系运转时对整个社会生活所作的贡献。[6](P203)
长期以来,西南域民族的自然崇拜体现出人们与自然相处的聪明智慧。从自然崇拜的特征上来看,一方面是内心自发的和朴素的,大多融入人们的生活生产之中;另一方面是普遍的和实用的,充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
在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秉承着“万物有灵”的观念,通过禁忌、习俗、神话故事等世代相传,起到约束人们破坏自然环境的不良行为,维护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这种传统文化促进了民族人口生产与环境和谐的关系,这也折射出了一种生态智慧:即人、天地山水、动植物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这种认知实为对生命的敬畏,同时也将伦理道德法则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
各民族传统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认知,形成了一系列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对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加强社会控制、维护地方秩序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对西南少数民族维护民族地区生态平衡做出有效的贡献。
(二)规范功能与价值
西南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之时,探索认识出了自然规律,既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各自民族独特的生态环境意识。
这些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渗透于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育丧葬和岁时年节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这些认知又蕴涵着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原始信仰和风俗习惯等。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原始信仰和风俗习惯渐渐形成各民族区域内的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民族区域内的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是民族内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调整、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本民族全体成员共同确认并自觉遵守的规则,适用于本民族区域内的行为规范。
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是经过少数民族长期沉淀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环境习惯法则既是法律规范,又是道德规范。因此,民族环境习惯法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调节民族区域内的社会矛盾起到了社会规范的作用,对其成员的生产生存行为起到调节、控制的功能,同时也对其成员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起到指引、强制、评价、预测和教育不可低估的作用。
《牛津法律大辞典》概括习惯法价值的一个方面为:氏族的习惯法是法律的主要部分。法国布律尔教授认为,“人们习惯于把法令置于法的正式渊源的首位”。根据台湾著名学者杨仁寿先生的理论,习惯法与成文法、法理共同组成法律的三大渊源。在国家制定法的互动过程中,习惯法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民族的环境习惯法则由于其本身的属性在民族区域内形成特殊的调节、保护机制;满足了民族的生活需要,使人们能将传统的环境保护民俗习惯作为调整自身行为的规范准则,在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生产中起到了具有法律调整功能的裁判、教育、调整作用。
总而言之,西南少数民族经过千百年演进而成的自然崇拜习俗,在生态环境方面,形成了少数民族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优秀传统形式。作为现代的人们应当用科学、理智的态度去审视这些维护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民族习惯法。这些基于民族习俗而形成的少数民族环境资源习惯法,不仅起到了外在调节人们行为的“他律”的效果;更是从内源上,使人们内心真正认可并严格遵循达到“自律”的主动调节目的。因此,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在生态环境平衡上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深刻地折射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优秀的环保习惯法则。
[1]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何光渝,何 昕.年初智慧的年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3]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4]陈金全.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冯祖贻等.侗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