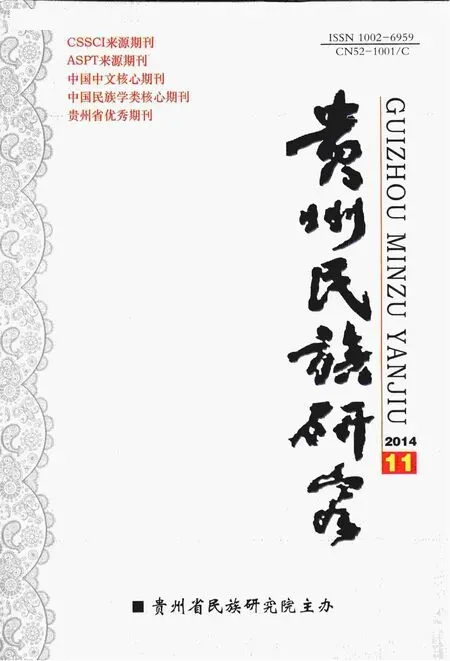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性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安宝洋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性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以文本学的视角审视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性的直接阐述所占篇幅不大,但其内涵却相当丰富、论述也颇为翔实。其中的主要思想有尊重和承认每个民族客观独立的民族性,对民族性必须坚持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批判,民族解放要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性”的概念辨识
作为实践着的革命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性问题的研究理路并未困囿于对“民族性”进行精准定义,而是大量渗透在其对“民族性”、“民族性质”和“民族性格”等民族问题的精辟论断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论述民族和民族问题时,已在不少著述中直接使用了“民族性”这一表述方式。诸如,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这篇恩格斯最早谈及民族性问题的文章中,他提到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和英格兰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民族性,而且正是法国因素和德国因素的相互混合构造出了英格兰人的民族性。同年9月,布鲁诺·鲍威尔在《文学报》中对民族问题提出绝对唯心主义论调——“假使存在一个在精神上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那么只能是那个能够批判自身并能够认识普遍颓废原因的民族”。[1]为批驳这一佯谬,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反驳道:“满心蹉跎地将本民族放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并且还幻想着其他民族能伏倒在自己面前,这纯粹是一种漫画般的、基督教的唯心主义,这只能证明它仍然深陷在德意志民族性的泥坑里。”
除直接使用“民族性”这一表述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语境中还使用了“民族性质”、“民族特性”和“民族性格”等近似表述来指涉“民族性”。在1848年8月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一文中,恩格斯首先不无讽刺意味地提道:“法兰克福议会的辩论从来也没有失去德国人温和的民族性质,就是在最激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同一著述中,恩格斯在对波兰人和法兰西人进行对比时,又对“民族性”进行了另一近似表述:南方的法兰西人为什么犹如一个绵软无力的累赘,被北方的法兰西人随意摆弄,以至于它的“民族特性”就这样彻底地完结了。1886年2月,恩格斯在致纽文胡斯的信中使用了“民族性格”一词来说明国家政治制度是民族性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荷兰直到18世纪的时候,仍然是西欧国家中唯一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所以它具备许多优越的政治条件,比如政府中已经消除了普鲁士和法国的那种“官僚机构气味”,“这对于民族性格的完善和发展,有很大好处。”[2]
由是观之,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对“民族性”进行精准的概念阐释,随着语境的转换其表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通过对具体民族的“民族性”表述,我们不难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性”的一般概念抽象,即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起来的,为本民族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等多方面特性。
二、尊重和承认民族性的客观独立存在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理路,马克思恩格斯尊重和承认各民族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并以此作为研究民族问题的逻辑基点,从未刻意否认民族性的客观存在及其历史合理性。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出:正是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解放与社会发展上也相应存在着多种方式。以自发的唯物主义为信仰的法国人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由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因为信仰泛神论和唯灵论,德国人必须先经历一场哲学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所以完全听从于经验。于是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社会革命。”[1]对于简单粗暴地否定民族性的思想和做法,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并给予了严厉批判。他们认为肆意否定民族性是有害无益的,这只会影响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解放事业。1872年5月,针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某些成员的沙文主义观点,恩格斯指出:“爱尔兰人在每个方面都形成了独立的民族,他们讲英语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丧失在国际内部具有独立民族组织这一大家同样享有的权利。”而不列颠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却妄图强迫他们抛弃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只遵从委员会的领导。对此,他强调:“如果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压迫民族的会员忘却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撇开民族分歧’,这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是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进行统治辩护。”这种在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宣扬民族共同解放的“国际主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借以维持统治的手段而已。
(二)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民族性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根源进行了深入阐发,这主要体现在其对犹太人问题的辨识中。作为犹太人民族精神传承和发展的纽带,犹太教是犹太人独特民族本性的重要载体。1843年,布鲁诺·鲍威尔在讨论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时提出,要是犹太人仍然信奉犹太教,那么犹太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狭隘宗教本质”[3]就必然压倒他成为人的一般本质,而且会很明显地把他和非犹太人区分开来。因此,依照鲍威尔的观点,犹太人始终无法融入基督教主流社会,主要就是源于他们的“宗教褊狭性”。正是由此出发,鲍威尔提出犹太人要获得自我解放,就必须摒弃自己的宗教褊狭性,也就是要彻底放弃犹太教这一民族特质。为批驳鲍威尔这一错误论断,马克思写作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作为回击,他一语破地指明鲍威尔在这里混淆了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错误地将政治解放与民族性混为一谈,而实际上无需否定和放弃民族独立性。犹太教的继续存在是有其世俗基础的,因此并不违背历史。因此,马克思强调民族性的客观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任何试图以否认和消解民族性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解放,并最终达到所谓“人类解放”的做法都将是无法实现的。
三、坚持对民族性进行历史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尊重和承认民族性的客观独立性,但并未因此就视其为绝对不变的永恒存在。他们强调民族性是受社会生产实践、国家政治统治和民族交往融合等诸多因素影响,并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而不断发生流变。
(一)各个民族地区的不同社会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状况是形成民族特性、造就民族精神的首要原因。民族性和民族是密不可分的,不存在没有民族性的民族,更不存在没有民族依托的抽象民族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审视民族问题,民族性是附着于民族这一物质载体之上的,它们一样都是历史的,都有生成演变的客观理路及过程。民族的产生亦是如此,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进行分工的必然结果,而正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分离直接促成了“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和“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4]。作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跃迁和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更是对各民族的民族性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工业使不同国家的各阶级之间产生了大抵相同的社会关系,从而大大地消弱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另外,工业革命还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阶级没有祖国,它与整个旧世界相脱离并与之战斗。而且,这个阶级在每个民族中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各种民族特性在它那里都已完全失去了意义。从本质上看,民族性始终是一定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任何民族性都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
(二)政治统治作为国家统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手段,对民族性的生成演进和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谈道,“从15世纪的胡斯战争开始,说捷克语的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波西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则并入匈牙利。自此,斯洛伐克人就已经丧失了一切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同样,整个德国东半部领土,由于一千年来的持续抗争,已经从斯拉夫入侵者手里夺了回来。几百年来,“这些地区大部分人都已经日耳曼化,斯拉夫人的语言和民族性已经完全消失。”随着政治统治的变更,德国斯拉夫人试图恢复独立的民族存在已是不可能了。
(三)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各种民族文化不断激荡碰撞,民族性亦会在交汇融合中发生流变。日耳曼人的民族性发生改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指出:“日耳曼人从凯撒开始,在文明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商业传播到了日耳曼人那里,为他们带来了罗马的各式产品,也一并带来了罗马人的一些需求;商业唤醒了本地的工业,这必然效仿起罗马人的样式。”在罗马人新式文明的潜移默化之中,原本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日耳曼人所具有的游牧民族本性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同样的例子还有在爱尔兰港埠中生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到12世纪的时候,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习俗上,都已经深受爱尔兰文化的影响了。正如马克思所讲:“野蛮的征服者最终会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永恒的历史规律。”[1]
四、民族解放要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民族性是一种客观独立存在,他们坚决反对否定和压制民族性的做法,但同时他们也强调,民族性问题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何种社会,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解放最终都取决于社会发展总问题的解决。所以,如果民族性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发展存在冲突,那么民族问题就必须要无条件地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狂飙突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工业化将各国日益连结成为一个紧密整体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机器大工业的锻造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地步,许多“类民族”特性在两者身上逐步显现出来。与资产阶级相比,深受工业革命锤炼的英国工人阶级,“说的是另一种习惯用语,有另一种宗教和政治,另一套的习俗和道德准则。”[1]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彼此间存在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就好像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对资产阶级而言,他们亦存在作为“民族”的共同特性。不管各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激烈竞争,正如他们需要共同针对国内的工人阶级一样,他们始终会存在着某些共同的阶级利益。而这种共同性,“就是所有资产者的民族性”。所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类民族”像两个不同民族一样具有各不相同的“民族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不同阶级之间的“类民族性”问题已经比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问题更具革命价值和历史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工人阶级的领空不属于法国人、德国人,也不属于英国人,而是工厂的天空。他们所显现出来的民族性区别于英国人、德国人、也区别于法国人,是自我贩售、雇佣劳动,是自由的奴隶制。”[1]
争取“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胜利”,是我们必须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能违背这个最高目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两难抉择中坚持的一个基本准则。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错误言论,“全体泛斯拉夫主义者都坚信,他们虚构的民族本性是高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虽然他们也承认必须要进行革命,但是这是以满足他们的一个条件为前提的,即一定要让一切斯拉夫人毫不例外地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而不顾最迫切的物质需要。”[1]但是革命不允许有人向它提出任何条件,革命与作为泛斯拉夫主义者压迫工具的“民族性”是不可兼容的,任何试图调和二者,甚至将民族性置于无产阶级革命之上的做法终将失败。1882年2月,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又进一步阐释了民族性如何从属于阶级性的问题。他指出,要是资产阶级在革命已经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还试图通过挑动德国人民与法国人民在战争中相互残杀,进而达到把革命无限推迟下去的目的,那么我们要说:“绝不允许你们阻拦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去路上。”[5]
五、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性思想的时代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中,民族性思想是其研究现实民族问题的重要逻辑起点。虽然其民族性思想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其论述的具体民族性问题也离我们较为久远,但是其理论研究的“合理内核”对于我们妥善处理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性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和承认每个民族所具有的客观独立的民族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还是人口数量和规模上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另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质,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民族性”,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些民族差异性,特别是在制定与民族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时,要切实考虑到各民族的民族特点,不搞一刀切,不断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性的思想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性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尊重和承认民族性的客观独立存在,并不等同于我们就要用僵硬、死板的态度来对待民族性问题。我们应该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路出发,改变以往机械僵硬的错误理论倾向,理性面对和深入理解各民族独特的民族特质和文化遗产。虽然现阶段各民族间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民族差异,但是民族性是会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流变的。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和具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不应当过于强调民族认同而将民族差异特殊化,而是应该努力促进各民族的相互融合,最终使各民族在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形成越来越多的民族共同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性思想强调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为早已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正沿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中国,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全局。当前,我国民族问题极具复杂性,但从本质来说,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偏远地区迫切要求发展而自身发展能力有限。因此,现阶段我国民族事务工作的主题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只能切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步伐,努力缩小并逐步消除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现实差距,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1]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张添翼.论作为同化的启蒙——从政治哲学角度重释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J].学习与实践,2013,(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张 胥.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世界历史”透视及当代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