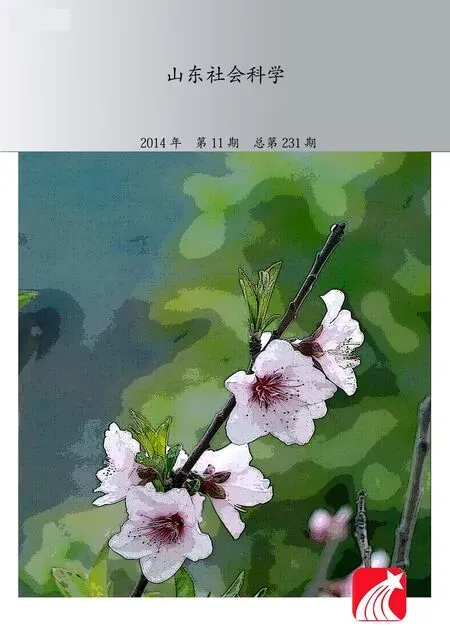论生命人格与文艺创作
杨守森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在心理学界,“人格”一语,常见以下两种更具主导性与普遍性的看法:一是指一个人的“先天倾向,冲动,趋向,欲求,和本能,以及由经验而获得的倾向和趋向的总和”*陈仲庚、张雨新编著:《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据此而有内倾型人格与外倾型人格,完美型人格、成就型人格、理智型人格、活跃型人格之类划分。二是延续了拉丁文的面具(persona)本义,指一个人在公共场合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的外在自我,据此而又有政治人格、道德人格、法律人格、审美人格之分。政治人格指的是一个人与政治观念、政治立场相关的个性表现;道德人格指的是一个人在品行与操守方面的行为模式;审美人格指的是一个人超越现实、向往美的个性情怀;法律人格指的是一个人在一定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本文所要论及的生命人格,与侧重于社会文化层面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法律人格、审美人格以及更具现代心理学意义的含混“总和”之人格不同,指的是一个人更见本真性与内在性的自我,即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身体机制、遗传素质、生命本能而形成的人格特征。这样的生命人格,与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之间,无疑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透过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分析探讨作家、艺术家的风格与成就,亦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何以“文若其人”以及又常常“文不若其人”之类相关问题。
一、文学艺术家的生命人格
世上的人,有的优柔寡断,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沉默寡言,有的风风火火;有的洒脱不羁,有的谨小慎微;有的易于激动,有的老成持重等等,表现出来的生命人格是不一样的。这些生命人格,有的更适于文学艺术活动,有的则更适于其他方面。比如我们很难想象“见花流泪,见月伤心”的林黛玉那样一种生命人格者,会成为一名习惯于动刀动剪的外科医生;也很难想象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抡动板斧的李逵那样一种生命人格者,会成为吟风弄月的诗人。
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大不相同,文艺创作,更需要飞扬的才思、敏锐的感觉、燃烧的激情、活跃的想象,而这些素质,虽亦可经由学习训练、环境影响而增强,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更赖于一个人不期然而然的生命人格。由中外文学艺术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可见,这类生命人格,最常见的是以下特征:
一是敏感多情,想象活跃。面对生活现实与自然万物,人们的感受程度,以及为外物所激发而产生的情感与想象的活跃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同是花开叶落,在常人眼里,不过是寻常的自然景观,而一位诗人则会激动不已,会生出奇思异想,会如同陆机所说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文赋》)。对于诗人与常人的这一区别,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N.威尔逊亦曾有过这样切实的判断:诗人对事物会有超出常人的“敏感性、强度、意识和激情”,“诗人必须有一种对人和自然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强烈的依恋,以至于其经验的餍足点远远高于大多数人”。[注][美]阿恩海姆等著:《艺术的心理世界》,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0页。这样的生命人格特征,自然不只见于诗歌创作,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同样如此,如麦田、果园之类,实在不过是寻常的乡村风景,而经由凡·高之笔,即大不一样了,会令人心跳眼热、情感汹涌,会成为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由这类画作可知,凡·高亦正是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好奇与独特想象力,捕捉到并表现出了寻常的乡村风景中所隐含着的生命的狂野与躁动之类难以穷尽的奥妙。同是面对鸟兽虫鱼,一般人可能习焉不察、漫不经心,一位画家,则会如同八大山人那样,从其眼神与体态中体验到生命的喜怒哀乐,生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是生命压抑,许多人会逆来顺受,一位作家,则会如同写出了《变形记》、《城堡》之类作品的卡夫卡那样,感受到人被异化为非人的痛苦,想象出别一番可怕的人间图景。正是由于更为敏感于物事变迁、人间冷暖、生命痛苦,作家、艺术家才会更具关爱万物的情怀,才会对现实与人生有着更为完满的企盼,才会对真善美有着较常人更为执着的追求,才使其作品拥有独到的人性深度与艺术魅力。
二是厌恶喧嚣,甘于孤独。与敏感于物事变迁、人间冷暖、现实压抑,以及时常沉溺于想象世界相关,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多是厌恶喧嚣、甘于孤独,甚至看上去不无抑郁之病状者。他们,正是在孤独中,倾听到了自我生命的沉吟,洞彻到了大千世界的奥妙,创作出了独具个性的作品。事实上,一位不甘寂寞、热衷于群体交际、八面玲珑、到处应酬的人,是难得有心理余暇品味人生、玄思宇宙,进入一个清静澄明的艺术世界的。海明威即曾这样深有体会地说过:“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作家的组织固然可以排遣他们的孤独,但是我怀疑它们未必能够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注]《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页。然,就外在行为而言,社会上没有谁能完全与世隔绝,故而一位作家、艺术家的真正孤独,尚不能仅就外在行为而论,而更为关键的是要看内在心灵,即是否有着鄙弃世俗、厌恶喧嚣的心理趋向。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诸如但丁、贝多芬、高更、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司马迁、曹雪芹这样一些成就辉煌的作家、艺术家,莫不是这样有着孤独心灵的生命人格者。
三是自由不羁,率性而为。美国认知与教育心理学家戴维·N.帕金斯曾将艺术家与科学家的人格进行了如下比较,认为“创造性的艺术家是一些不关心道德形象的放浪形骸者;而创造性的科学家则是象牙塔中冷静果断的居民”[注][美]阿恩海姆等著:《艺术的心理世界》,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其论也许不无偏颇,但在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生平资料中,我们的确可以更多地看到不同于恪守礼仪、时常自我克制的道德人格者,实际上也不同于巧于周旋、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人格者,或长于理性研判、冷静沉着的科学人格等其他文化形态的人格者。他们,常常是无所顾忌,顺其心性,特立独行。会像中国古代诗人嵇康那样敢于“薄名教,任自然”;会像李白那样目空一切,“天子呼来不上船”; 会如同李贽所说的常见“绝假纯真”之“童心”;会像英国诗人拜伦那样宣称“不自由毋宁死亡!”(《卢德派之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总是不完满的,人生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作家、艺术家的独特价值之一正在于:通过赤诚率性、洒脱不羁、敢于冲破既有规范的诗歌意境及其他形态的艺术形象创造,让读者在想象世界中得以情感的宣泄、心灵的抚慰,以及生命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满足。
四是冲淡旷达,超逸高迈。与一般人格不同,优秀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敏感于花开花落、物事纷扰,乃至人间苦难的同时,又会如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会以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所说的“与天为徒”的心境面对,会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宇宙眼”视之。他们,会像雨果、托尔斯泰那样,面对人间的丑陋与邪恶,不只是愤怒与仇恨,亦会以超逸的心态去包容世界,会用冉阿让、聂赫留朵夫这样一些在他们心目中亦不乏“善根”的人物去温暖世界;会像沈从文那样,同是面对战乱与杀戮的人间,在小说中,不是站在某一立场着力于渲染仇恨,以求进一步激发阶级的、民族的仇恨,而是以高迈的视野,注重用文学笔墨建立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力图通过对“爱、自由与美”之类的追求,来化解人间的纷争与仇恨。会像杨绛、孙犁那样,同样是写“文革”期间的苦难,在其《干校六记》、《鸡缸》、《王婉》等小说中,让我们体悟到的是另一种不同于“伤痕文学”的冲淡旷达的人生意味。
上述分列的生命人格特征,在不同作家、艺术家的具体生命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并不相同,某一方面可能更具主导性,从而形成了李白不同于杜甫、雨果不同于托尔斯泰这样一种生命个性与创作个性的差异,但在某一具体作家、艺术家身上,这诸多方面的生命人格特征,又是相互关联、交互并存的。其中,敏感,即类乎生命底色,为所有作家、艺术家所共有。如果缺失了敏感,一个人也就缺失了成为作家、艺术家的基本质素。敏感与孤独,又是相伴而生的,一位敏感者往往易致孤独,一位孤独者亦往往更为敏感。孤独与率性、超逸亦具有内在相通性,实质上,率性与超逸,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孤独的特异表现形态。
与主要基于文化教养、环境熏陶与自我追求而形成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等其他文化形态的人格相比,作家、艺术家生命人格的形成,虽亦与环境影响及个人的文化追求有一定关系,但决定性的因素,是源于一个人遗传性、先天性的命理机制,是涌流于血脉中的一种生命气质,或如美国生物学家帕客(G.H.Parkir)曾指出的:这样的个体人格,“如感觉的敏钝,行动的迟速,气质的特性,如忧郁或爽快的脾气,无能,寡断,诚实,节俭与可爱等,严格说来便都是大脑的机能。”[注]转引自《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这样的个体生命机能,虽有可能因外在环境的压抑而潜隐,但恐是难以从某一生命个体中完全清除的;或可因外在影响与主观追求而强化,但恐也是难以无中生有的。正如民谚所谓“山好改,性难移”。比如一位率性人格者,可能会因时势迫压或利欲诱惑而有所收敛,却是难以从骨子里彻底改变的。这样一种情况,在作家、艺术家那儿,是广为可见的。举个例子来说,如在李白的一生中,既有过穷困潦倒之时,亦曾得享过宫廷的荣华,但不论在何处境中,李白终究还是那个仙风道骨、飘逸潇洒、“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的李白。同样,一位对事物缺乏敏感者,一位不甘寂寞者,一位心胸狭窄者,你想通过诸如教育之类的方式让其变得敏感,变得孤独,变得超逸旷达,也是不大可能的。
二、生命人格的顺应与坚守
感觉敏锐、甘于孤独、赤诚率性、超逸旷达之类的生命人格特征,当然不只为作家、艺术家所独有,亦可见之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但从事其他活动者,因其职业与谋生原因,则不能不尽力予以自我克制。比如一位政治家,为了国家或党派利益,或其他政治目的,有时不能不委曲求全,不能不韬光养晦,甚至不得不口是心非,不得不铁血心肠,因而是无法孤独、难以率性,也难以超逸高迈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文学成就显赫的诗人,大多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的重要原因。另如以建立并力倡道德规范为使命的伦理学家,以研判人间公正为使命的法学家,以穷究宇宙万物之理为使命的科学家,以及工、农、兵、学、商诸色人等,也是很难像文学艺术家那样孤独、狂放、超逸的。而对于一位作家、艺术家而言,如果背离了敏感、孤独、率性、超逸之类生命人格特征,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生命。
从人类的文学艺术实践来看,一位作家、艺术家,只有顺应自己的生命人格,才能在作品流露中出更为本真的生命情怀,从而使之更为真切动人,也使之更具个性生命的质感与活力。但丁、莎士比亚、曹雪芹、蒲松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福克纳、贝多芬、凡·高、毕加索这样一些文学艺术大师,无一不是凭依其敏感、孤独之类的生命人格,才更为深切地感触到人类社会的律动,体悟到了人生的幸与不幸,洞察到了大千世界的纷纭奥妙,从而创造出了《神曲》、《哈姆雷特》、《红楼梦》、《命运交响曲》、《向日葵》、《格列尼卡》等一部部扣人心弦的小说、一首首撼人肺腑的乐曲、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绘画。表面上内向沉默,而骨子里桀骜不驯,早在童年时代就已显露出反叛个性,就敢于在课堂上当面质疑老师的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亦正是因其顺应了自己的生命个性,敢于诉诸“犹如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拳打脚踢翻跟头,折腾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口吐莲花头罩金光手挥五弦目送惊鸿穿云裂石倒海翻江蝎子窝里捅一棍”[注]《几位青年军人的文学思考》,《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的狂放笔墨,才写出了激情汹涌、风姿卓异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一系列世界闻名之作的。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一位顺应自己生命人格的作家、艺术家,有时甚至会“无意插柳柳成荫”,在不经意中获得创作的成功。中国当代作家毕飞宇,以小说语言的鲜明个性,尤其是极具张力的反讽韵味为人称道,有不少学者已从修辞角度予以分析探讨。实际上,当我们联系到毕飞宇大学时代曾崇尚留长发的诗人,曾拒绝接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奖,以及他自己说过的“对一些人我从不妥协”之类性情来看,[注]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花城》2001年第4期。其小说语言特征的形成,恐决非主要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创作技术层面的修辞问题,在更深层次上,亦恰是毕飞宇顺应了自己敏感、超逸以及骨子里的“狂放”之类生命人格特征的结果。个中奥妙,还是毕飞宇本人说得更为切中肯綮:“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尽我的可能把我的生命人格注入语言,永远不要当语言的奴才。”[注]林建法主编:《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这样一种倾注了自我生命人格,而非主要赖于修辞训练的语言,自然也就会从根底里与众不同。另如被视为美国现代先锋艺术大师的杜尚,自己大概也没想过要创造什么先锋艺术。长期留学美国的西方艺术史学者王瑞芸女士曾有过如下有说服力的论析:“杜尚是一个对艺术对人生真的看开了、放下了的人。他是把这个眼光真正贯彻到他人生中去的人。他一生活得无滞无碍,如行云流水,视富贵功名如粪土。”[注]王瑞芸:《变人生为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他将一个小便池当作自己的作品,“等于是用他自己的生活、生命本身提醒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艺术被限制在一幅画或一个雕塑中是一种狭隘。他把艺术放大为做人,放大为人生”;用杜尚自己的话说,那只不过是“做我认为有趣的事罢了”[注]王瑞芸:《变人生为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杜尚之所以为人看重、名声大振,关键原因亦正在于:此一顺应自己生命人格、率性而为的反艺术的 “艺术活动”,本身就呈现了特定的生命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巧合天缘,所作所为恰好隐含了时代所向往的艺术反叛欲望。正因如此,我们会看到,在杜尚成名之后,有不少自视为先锋的效颦者,竞相追随,却难以如杜尚那样为人看重了。其原因又正如王瑞芸女士这样论及的,那些追随者,“与杜尚彻底的反艺术是两码事。虽然这些人手里出来的作品都打着反艺术的旗号,但他们抢着进博物馆的心情比谁都来得迫切”[注]王瑞芸:《变人生为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显然,这样一种缺少了生命人格的本源动力、而别有他求的外在模仿者,自然也就难有多少独到的艺术创造价值了。
一位作家、艺术家,也只有坚守自己的生命人格,才能保持其创作生命力。唐代诗人李白汹涌的创作活力与文学成就,即与其坚守了狂放不羁的生命人格有关。试想一下,受到玄宗召见、成了翰林供奉之后的李白,如果如世俗之人那样,受宠若惊,对玄宗感恩戴德,变得唯唯诺诺,中国文学史上大概也就没有伟大的诗人李白了。中外文学史上不少作家的创作成就与艺术高度,亦均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自我生命人格的坚守。如美国当代小说家品钦,在1973年因一部《万有引力之虹》成名之后,竟仿佛一下子从人间消失了,再也不肯露面,“没让人照过一张相,人们也不知道他目前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还写不写小说”[注]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家选》(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38页。。人们后来知道,品钦当然还在写小说,是在力避世俗纷扰、甘于孤独中继续埋头他的创作,是在不为人知的近20年间,又悄然完成了《葡萄园》(1990年)、《梅森和迪克逊》(1997年)、《抵抗白昼》(2006年)、《性本恶》(2009年)等长篇小说。正是这样一位品钦,才有了更为辉煌的创作成就,才进一步成为许多读者与批评家心目中更为杰出的美国当代小说家。中国当代作家孙犁,之所以在晚年仍能文思泉涌,写出了一大批诸如《鸡缸》、《女相士》、《高跷能手》、《亡人逸事》、《乡里旧闻》等标志着新的艺术高度、境界高超、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散文,亦是与其厌见扰攘、畏闻恶声、甘于孤独的人格坚守有关的。我们知道,晚年的孙犁,“常常闭门谢客,从不主动结交官场人物,远离人事纠葛,不参加文学圈子里的各种会议、活动,也不欢迎作者到自己家里来,愿意保持一种单纯的文字之交为好,甚至家里长期不安装电话”[注]赵天琪:《我所知道的晚年孙犁》,《纵横》2005年第7期。。孙犁的这样一种坚守,无关乎政治、道德,而正乃一位作家、艺术家所需要的对生命人格的坚守。与孙犁不同,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另有不少诗人、作家,稍有成就之后,即热衷于抛头露面,孜孜于官位、荣誉、头衔,结果只能是:除了徒增些虚名之外,创作方面已看不到有什么作为了。
三、“文品”、“艺品”与“人品”
在我们既有的文艺理论中,一直特别尊崇“文若其人”之说,并相信“文品”、“艺品”与“人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西人的代表性论断是古罗马朗吉弩斯“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中国文论中则有诸如郭若虚所说的“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能不高,生动不得不至”,文征明所说的“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清人薛雪所说的“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一瓢诗话》)等等。此外,法国人布封讲过的“风格即人”,也常在此意义上受到推崇。
这类现已得到了文艺理论界普遍认可的看法,论据当然是充分的,也大致合乎文艺创作的实际。一名鼠窃狗盗之徒、心灵龌龊之辈,即使舞文弄墨,一般说来,是不大可能写出值得肯定的作品的。但深究起来,这类将“人品”与“文品”、“艺品”完全扯在一起的看法,又是有问题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即早已不乏异议。宋人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即有是论:“世或见人文章铺张仁义道德,便谓之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清人魏禧亦曾道及:“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观人。”[注]转引自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1页。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这类“人品”与“文品”、“艺品”并不统一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读者如果了解潘岳“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晋书·潘岳传》)之类品行,大概就很难相信“绝意乎宠荣之事”,“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闲居赋》)之类文字会出于这样一位“趋世利”者之手。宋诗中有一首《夏日登车盖亭》:“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其超然淡远之境界,令人神往。但这首诗的作者是曾经出任过宰相的蔡确,在《宋史》中是被置于“奸臣”之列的,其传中载有“以贿闻”、“既相,属兴罗织之狱”之类劣迹。宋代另一位在书法方面有着很高艺术成就的宰相蔡京,也是以贪渎弄权而闻名史册的。在外国作家、艺术家中,如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是以生活放荡、滥情纵欲著称的,一生中,不知有多少女性因他而陷入了悲惨命运。即如海明威这样一位伟大作家,也不无品行方面的亏欠:惯于撒谎,5岁时,他就谎称自已降服过一匹脱缰的烈马;他曾欺骗父母与女电影演员梅·马什订了婚,事实上他只是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看到过这位演员;他曾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自己在芝加哥充当职业拳击手的故事,说他的鼻子被打破,但他仍能继续还击;他曾谎称在战场上被机枪子弹击倒两次,被0.45厘米口径的子弹击中32次。[注]《海明威:深渊》,载[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面对此类事例,我们又如何理解“人品”与“文品”、“艺品”之间的关系呢?
为了进一步探明此类问题,这儿有必要首先弄清何谓“人品”?又何谓“文品”与“艺品”?在我们已有的理论中,“人品”通常是就腐败堕落、不仁不义、媚颜卑膝之类的道德人格,或滥用公权、陷害好人、独裁专制之类的政治人格而言的。而“文品”、“艺品”就比较复杂了,至少常见两方面所指:一是指作品的格调气度,二是指作品的精神内涵。就前者而言,与“人品”自然是没什么必然关联的。钱锺书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成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注]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钱先生所强调的“在此不在彼”,意思即是:所谓“文如其人”,只是就作者“豪迈”、“狷急”之类的性格特点与文章的相关格调之间的关联而言的,不涉其他。而这“豪迈”、“狷急”之类性格特点,是无关政治,也无关道德的。就作品的精神内涵而言,有许多作品,比如一首山水诗、一幅花鸟画、一件书法作品,也是不一定有什么道德与政治内涵的,对于这类的诗人、书画家,又何谈其“文品”、“艺品”?确有许多作品,尤其是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是会有道德内涵或政治诉求的,但在真正优秀的作品中,亦必会同时充满着人生感悟、生命冲动之类的复杂意绪,对于这样一些内涵复杂的作品,当然也不宜仅以道德或政治内涵的“人品”尺度去对应考量。对此,莫言有一个看法倒是很值得进一步深思:“作家的人品与文品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一些道德败坏的小人写出的作品说不准是精品,而一些道德完善的君子写出的作品却会很烂。”[注]莫言:《作家和他的文学创作》,《文史哲》2003年第2期。
与道德或政治层面的“人品”视角相比,由生命人格着眼,或许能够更为科学地认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联。文艺作品的某种风貌,肯定是源于作者生命人格的相关特征。如果就此而言,布封曾经强调的“风格即人”是对的。比如只有狂放不羁如李白者,才能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豪放气势的诗篇;只有超逸如王维者,笔下才多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的淡远情致;只有敏感细腻、多情善感如李清照者,词中才会多见“被翻红浪”、“绿肥红瘦”之类的婉约意象。在某一具体诗人、作家身上,由于既会有生命人格的主导特征,又会有交互并存的其他特征,故而豪放如李白者,也有过“床前明月光”这样的柔情之作;超逸如王维者,也写出过“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这样的壮怀激烈之作;敏感细腻如李清照者,也留下了粗犷雄健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诗。对于上述现象 ,从“人品”角度,恐是难以说得通的,因为这狂放、超逸、细腻、敏感多情,以及上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与“格调”相一致的“狷急人”、“豪迈人”之类,显然更属于与天性气质更为相关的生命人格特征,而非社会文化性质的“人品”特征。
而诸如“狂放”、“超逸”、“敏感”、“ 细腻”之类的生命人格特征,自然不可能唯“人品”高尚者才会具有,亦会隐潜于许多人身上。由于笔情墨趣的诱导,或生活变故、自然风光等其他外在因素的激发,即使一些道德人格低下或政治人格有亏的人,在赋诗作文、写字绘画时,亦有可能超越自己的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而顺应其潜在的向往生命自由、挣脱利欲束缚之类的人格趋向,使之创作出境界高超的作品。对诸如存在政治人格或道德人格缺失的中国历史上的潘岳、蔡确、蔡京,西班牙的毕加索、美国的海明威这样一些人的文学艺术成就,或正可作如是观。如潘岳虽有“拜路尘”之类的献媚丑行,骨子里实亦不乏与一般人相通的厌恨尘世纷争之意,辞官归隐期间,恬淡的乡野风情,又必会使之进一步强盛,在此期间写出《闲居赋》之类作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亦可谓是其生命人格的自然体现。蔡确也是在被贬出朝廷之后,由山光水色激活了超逸情怀,才写出了那首意绪淡远的《夏日登车盖亭》的。蔡京虽系权奸,但作为政治人物,原本就不乏“豪健”、“沉着”之类的生命人格气度,当投注于书艺时,自然也就成了值得肯定的格调。至于毕加索的滥情纵欲、海明威的惯于撒谎,从文化人格的角度看是道德亏欠,而从生命人格的角度看,则又恰是有利于其创作成功的率性、超逸之类特征的体现。
正是经由对潘岳、蔡确、蔡京、毕加索、海明威这样一些个案的分析,我们会进一步意识到,在探讨“人品”对“文品”、“艺品”的影响时,不应将“人品”简单地道德化或政治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品问题“决不能认为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而应该是一个气度问题。因此,人品的高下从根本上看取决于气度的大小。换言之,只要气度大,则无论大奸大恶还是大慈大悲,其人品必高,发于绘画,其画品也必高;如果气度小,则无论小奸小恶还是小慈小悲,其人品必下,发于绘画,其画品也必下”[注]徐建融:《“扬州八怪”批判》,《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正因如此,我们在评价相关作家作品时,也就不宜简单化地因人废文、因人废艺。
在我们的理论中,另一值得进一步深思的相关问题是:不少学者认为,只有具备审美人格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创作出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而事实上,许多创作出审美作品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本人,抑郁终生,生活得并不“审美”,也就很难说他们拥有多大程度的超出常人的独特审美人格。例如创作了许多美丽童话的安徒生,在现实生活中,就常常处于病态的苦闷与恐惧之中。因神经过敏,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觉得有人在蔑视他、侮辱他或暗算他。在充满阴郁和绝望的信件中,他曾时常悲叹他那可怜的身体——“虚弱”、“发烧”、“头晕目眩”、“筋疲力尽”。因为时刻担心被人活埋,他曾在睡觉的床头上写了一张条幅:“我睡着时看上去象死了似的!”[注][丹麦]欧林·尼尔森:《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郭德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第73页。贝多芬也这样说过:“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他甚至写下遗嘱,准备自杀。[注]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载《傅译传记五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34页。如果我们仅从审美人格角度解释诸如安徒生、贝多芬这样一些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成就,恐也是不无牵强的。而从生命人格角度,会更易说得通:正因极度敏感而惊恐于人生痛苦,正因愤世嫉俗而自甘于孤独,正因向往自由而渴望率真之类的生命人格,安徒生才想象出了那一个个安逸美好的童话世界,贝多芬才创作出了气势磅礴、喧腾着不屈生命激情的《热情奏鸣曲》、《命运交响曲》等不朽乐章。
四、生命人格与艺术成就
由于侧重于从道德或政治角度看待“人品”,故而人们对作家、艺术家文化形态的道德人格、政治人格等,往往有着更高的期许,譬如希望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的良知”、“时代的代言人”等等。一些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亦往往被作为人格楷模、伟大旗手予以褒扬与推崇。
在作家、艺术家群体中,道德品行高尚者当然是大有人在的,但也确有不少影响颇大的作家、艺术家,是说不上多么圣洁、多么高尚的,甚或是不无卑鄙低俗之劣迹丑行的。如以道德标准衡量,法国小说作家莫泊桑即恶习十足。他逛妓院,与各种女人鬼混,甚至有段时间与其他四位朋友同时共享一个女人。他曾公然宣称:“我的朋友,床铺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生于斯,爱于斯,死于斯。”托尔斯泰亦不无龌龊与卑劣:曾诱奸过家中的仆人,曾遗弃了为他生了儿子的情妇。[注][美]欧文·华莱士:《名人隐私录》,王金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深为世人喜爱的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品行亦够得上“肮脏”:一味喜欢蹂躏含苞欲放的处女,曾为美国新闻界指责为“淫徒”。另如前述毕加索的生活放荡、海明威的惯于撒谎等等。以政治人格来看,富有报国激情、时代责任感,或勇于反抗社会黑暗的斗士型作家、艺术家也是累累可见的。如中国古代的屈原、杜甫、白居易,现代的鲁迅,前苏联的高尔基,英国的诗人拜伦、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等等。但亦有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并不怎么关心政治,或刻意远离政治、避开政治、超越政治的,如中国古代的李清照、曹雪芹,现代的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20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等等。更有甚者,依据一定的政治尺度,有些作家、艺术家,曾有过为世人诟病的污点,如巴尔扎克加入过保皇党;1999年获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小说家格拉斯曾信奉纳粹观念,并长期隐瞒了自己的纳粹军人历史;身为宋太祖赵匡胤第11世孙的赵孟頫仕过元;周作人出任过伪职等等。
但上述那些道德人格有所亏欠,以及说不上政治人格,甚或有过政治污点的作家、艺术家,其创作成就似乎并未因此而大受影响;相反,有不少政治人格获得颇高评价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艺术成就亦未必一定突出。如享有“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始人”之声誉的“宪章派”代表诗人厄内斯特·琼斯,被恩格斯称赞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维尔特、日本著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度颇受推崇的革命作家蒋光赤等等。有不少追求道德纯正、恪守道德规范者,在赋诗作文时,也会缘其本原性生命人格的自我克制,而影响其创作质量。如宋代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张栻、真德秀、魏了翁等人,虽也写过不少诗歌,但大多给人枯燥之感,少有真正耐读耐品之佳作。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不少作家,在经由先进思想的教育改造之后,虽然道德人格提纯了,政治人格提升了,艺术水平反倒下降了,如艾青、曹禺、丁玲等等。
正是透过上述现象,我们会发现,与“人品”关系密切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与一位作家、艺术家的成就之间,似乎并无必然联系。而生命人格则不同了,一位作家、艺术家,如果缺失了敏感多情、想象活跃、甘于孤独、率性而为之类的生命人格,是难以创作出优秀作品的。
与常人相同,一位作家、艺术家,无论如何伟大,亦终究是血肉之躯,亦会有源于本能的七情六欲,因而其整体人格不可能是完美的。而正因其不完美,才更具人之为人的生命活力与情感热度,其作品也才会更为切近人性,更能呈现人生的斑斓多姿。如果苛求他们神圣化,期望他们承载更多超文学超艺术的使命,不仅不切实际,且势必会压抑其生命活力,遏制其作品中的情采与意绪,影响其创作成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位作家、艺术家,原本就不应是时刻听命于某些外在要求的政治工具,或处处循规蹈矩的道德奴隶,而更应是顺其心性,敢于放任自我生命、勇于扩张自我生命者。
当然,我们承认作家、艺术家人格的不完美,强调放任生命、扩张生命,并不意味着可以纵容作恶,可以容忍无耻,可以躲避崇高。作家、艺术家,在顺应并坚守诸如敏感、孤独、率性、超逸之类更有益于优秀作品产生的生命人格的同时,还是要高度重视人品修养,至少要守住公平正义、仁慈善良之类的政治与道德底线。因为文学艺术,毕竟是引领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毕竟具有推动人类不断走向完美的力量;因为德艺双馨,毕竟是人们更为向往的艺术人格标竿;因为从文学艺术的欣赏接受史来看,一个人的文学艺术成就无论多高,如果在政治或道德方面劣迹斑斑,亦会如宋代的蔡京那样,难以为人们从心理上接受,而影响其应有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