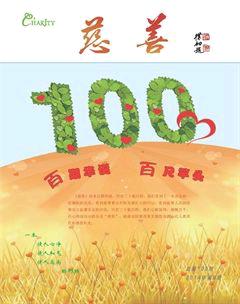母亲的眼睛
马亚伟
母亲年轻的时候,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七八岁时,母亲在戏台上唱戏。她演花旦,眼睛灵动有神采。
戏台上的母亲,扮演的总归是别人。我最喜欢母亲在家里的样子,尤其是她缝衣服的样子。灯光下,母亲的脸有柔美的轮廓,眉清目秀。她神情专注地挑起针线,有时用牙轻轻咬断线头,有时把针往头发里插一插。母亲有时会抬起头看我,她冲我笑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闪着温暖的光。
后来,母亲告别了戏台,在村里务农。我十一二岁时,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孩子多、负担重,母亲干农活不行,所以总是着急上火,生怕自己落于人后。偏偏就在这时,母亲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父亲带着她四处看病,无暇顾及地里的庄稼,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
母亲病愈后,突然觉得左眼看东西总模糊。父亲很担心,让她再去医院查查,母亲揉揉眼睛说:“没事,揉揉就没事了。不碍事,看得清,看得清。”
其实,那时母亲的右眼已经只剩微弱的光感了。她清楚家里的境况,就独自一人把这个秘密埋藏起来。以后的日子,她照样下地干活,回家做饭,做针线活。粗心的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母亲的右眼看不见了。只是知道,她做针线活的时候非常吃力。我常常见她在窗前,双臂高高举起,眯着眼睛,很努力地纫针。这时,母亲的嘴巴总会撮起来,唇上的纹路皱皱的。她一次次叫着劲,显出很卖力的样子。我夺过她手中的针线,很轻松帮她纫上了。晚上,母亲点蜡烛,对着灯芯,却怎么也点不上,左右摇摆了半天,才蒙准了。父亲总嘟囔她:“还不老,眼却早早花了。”母亲笑笑说:“花了,真花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母亲有一天突然对我说:“我的右眼一点都看不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治。”我这才发现,母亲的右眼明显没有光泽了。
我赶紧联系,去了最好的医院,找了最好的医生。医生告诉我说:“你母亲的右眼早就失明了,现在连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不可能再恢复了。”医生对各种疾病已经司空见惯了,说话的语调极为平静。可是,那几句话对我几乎是霹雳一般。在医院的走廊里,我一个人手捧着检查单泪如雨下,很长时间不敢走出去面对在外面等候的母亲。
这么多年里,母亲把自己的痛苦掩藏起来,隐忍地承受着生活的种种重担,不吭一声。这些年,我们姐妹三人每年的棉衣,父亲的棉鞋,祖母祖父的衣服,母亲从来没少做过一件。我结婚时,母亲给我做了六床被子,我生下女儿后,母亲又给我的女儿做棉衣,一年都没间断过……我越想越心酸。
母亲得知她眼睛好不了时,满脸沮丧。那一刻,我的心在疼。母亲转而笑笑说:“没事,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人家瞎子都活得好好的。我左眼没事,看得清!”她倒反过来安慰起我了。
现在,母亲的视力明显不好了。我会帮她念电视上的字幕,会在她的身边给她读一篇我写的文章,会帮着她做针线活……母亲老了,儿女就是母亲的眼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