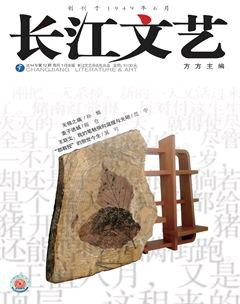王跃文:我的笔触指向温暖与光明
王跃文:当代作家,曾有过政府工作经历。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从2001年10月起,专职写小说。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2010年入围“免网杯”中国文艺网络奖最佳作家候选人。2014年8月,其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包括《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龙票》《大清相国》《苍黄》,以及作品集多部。
如果“官场文学”是一个江湖,那么“官场文学”的作者,就是潜行于这个江湖的暗夜骑士。
王跃文其实并不太喜欢使用“官场文学”四个字,尤其不喜它作为他创作的标签。他的小说其实就是现实主义,只是他塑造人物之后,连同自己的信念,和所感知的现实一起,裹挟在官场的外衣之内,任其闯荡江湖。
在人性与规则的灰色地带披荆斩棘,是灰色的背景衬托人的轮廓,还是人的形象被灰色的背景吞噬,这大概是“官场文学”追问的终极命题——所以作家们书写的还是人,至少严肃的作家如此。
但是就像“官场”太容易越轨一样,“官场文学”也太容易变成一个窥私探秘的窗口。只要有人愿意窥探这片领域中的光怪陆离,必然会有人乐意侧身“衙门”去添油加醋。作为某一种类型化的文学,“官场文学”本身就存在灰色化的隐患——官场的跌宕起伏,到底是迎合市场的曲意奉承,还是直面现实的人性拷问?官场的冷眼旁观,究竟是去伪存真的批判,还是挖私掘隐的欣赏?
写官场的作家,一定会遭遇这样的挑战。当人性的刻画,还不及那些潜规则,以及声色犬马、尔虞我诈的世界吸引人的时候,作家该如何继续这条写作之路?他们像穿行于黑暗中的骑士一样,执着火把和长矛,或者照亮深邃的黑夜,或者鏖战咆哮的风车。
王跃文也在做着这样的对抗。他对于“官场文学”这个词汇的绝决态度,已经证明他在对抗。对抗什么?对抗一种充满惯性的观念,把“官场文学”实用化、功利化的观念;对抗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其中就包括官场小说家的标签。
多年前那封给王跃文带来麻烦的公开信,已经证明这位曾经游弋官场周遭的人,其实不是一块可以靠各种潜规则就飞黄腾达的人。而今年凭借自己的乡土文学作品一举斩获鲁迅文学奖,也证明这位暗夜骑士,其实从未堕入幽暗的沉夜,始终有通透明亮的星光,为他指引远方的征途。
但是还有更多的“官场文学”正在试图扰乱视听,把类型化文字的营销,深刻地植入到纯文学的招牌里面去。不仅是“官场文学”,还有商场、职场、战场、秀场和名利场,各种类型的创作,都在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改变着阅读和写作的生态。
所以,还是应该听听王跃文怎么说,看看他对于“官场文学”持有怎样的看法,看看他对于自己心爱的乡土文学,又有怎样的情愫。我问他,官场与乡土,是不是精神世界一种张力的两端,会不会沉浸在“官场文学”中太久,然后去乡土世界——这个王跃文熟悉并感到宁静的内心世界——寻找平静呢?他回答我并非如此,不过是不同的小说素材,不同的做工和手法而已。
果真如此?
一
今年9月,王跃文来到武汉,参加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同时到湖北省图书馆举办讲座。在与读者互动的时候,有读者抛出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您原来写当今官场,如今写清代官场,这是否代表了您的怯懦?”王跃文身上的湖南人的血顿时沸腾起来,“我是说真话的人,不会搪塞你”,脱口而出。他说,自己不仅写有关官场的小说,更写了大量的随笔和杂文,同样在深刻地揭示问题。他还认为,文学并不是匕首投枪,还有很多功用。一问一答,显示出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某种小小错位,其实这里面既没有黄昏里的侠客,也没有中途止步的高人。作家守护的,是文学对心灵的作用,而并不一定在于能否改变现实。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以“官场小说”闻名,也曾经置身官场,并因为“公开信事件”而离开官场。一方面您要写官场里面人性的复杂,另一方面现实中您又坚持一份秉直、执着,那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官场生涯?
王跃文(以下简称“王”):严格说来,我的经历谈不上官场生涯。我过去在政府机关里只做过技术型干部,就是替官员写文章的秘书人员。没有做官经历,何来官场生涯?秘书人员的身份很微妙,不是官员,却要用官员的脑子想问题,用官员的文笔写文章,有时候还得替官员办事情。有些秘书工作者,做着这些替身的活,日子久了就“形神兼备”了。某天,一纸文件下来,秘书真的就是官员了。我没有等到这天,就离开了官场。
范: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官员的要求是最高的,因为从各种甄选制度中选出来的管理者,本来应该是修齐治平的代表,理想的官员,和文人甚至义士,有非常多的重叠部分。但今人看到的“官场文学”,却充满奸诈与凶险、压抑与痛苦,为什么“官场文学”会以这样的面貌为主?
王:中国自古官场,都是理念和现实两张皮。比如清代,大清律例在廉政方面规定非常严格,官员向富裕人家借钱一千两银子者问斩。但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是清代官场的真实写照。
康熙皇帝曾同大学士们谈官员廉洁,拿户部尚书赵申乔、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礼部尚书张伯行为例,说:“赵申乔做湖南巡抚时,把大小官员都参了,难道通省无一好官?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方面者。赵申乔是个清官,但他作为方面大员,要说他一干二净,朕未必相信。张鹏翮居官清廉,但他在山东兖州做官时,也收过人家的规例钱。张伯行居官也清,但他刻了那么多书,刻书一部非花千金不可,这些钱哪里来的?两淮盐差官员经常送人钱财礼物,朕不是不知道,不想追究而已。”可见,清代官场不但腐败严重,而且皇帝也见怪不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的官场,应该比古代官场进步多了,但并没有从制度上杜绝腐败,目前廉政建设的任务相当艰巨。不是现在的官场文学刻意要如何表现,而是现实有时候的确非常糟糕。我没有能力全面研究官场文学,就自己写的那些现实题材的小说而言,笔下已经很留情面了。作家反映现实的胆量再大,也大不过某些贪官的胆量,他们的胆量之大,已远远超过作家的想象能力。
范:有人把“官场文学”视为官场教材,有人把“官场文学”视为一种发泄的途径,有人觉得“官场文学”能起到警示的作用,当然也有人觉得毫无作用。您在创作的时候,会从什么角度出发?您如何对这类特定的文学进行价值判断?
王:社会上对“官场小说”的误解太深,所谓“官场教科书”一说尤其荒唐可笑。未必出了这么多的贪官,都是作家们教出来的?相反,作家们笔下写的东西,在那些贪官眼里显得很没有眼界,很没有出息。很多作家并没有“官场生活”经历,他们写的官场生活连皮毛都没有触及,更没有可能了解各种惊人的贪腐内幕。当然,文学并不需要同生活比惊奇、比恐怖、比黑暗。作家更需要想象能力、虚构能力,更需要对生活的思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的那些写官场的小说,既没有警示现实的野心,更没有只图发泄的狭隘,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笔下的生活和人物命运作些思考。这些思考未必有答案,但思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范:您也说自己是一个平淡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官场这样一种极端的环境来勾勒人性?除了您对它比较熟悉之外,还有别的原因没有?
王:我确实是个平淡的人,性格不激烈,也谈不上勇敢。但是,我内心认定了的原则,会固执地坚持。我写官场小说,当然首先是因为熟悉,有很深的感触,有种不吐不快的欲望。我见多了满口理想信仰的官场人物,做的却全是偷鸡摸狗的事。
范:您的作品中,也有《大清相国》这样“正能量”的作品。您写过很多官场,在考察陈廷敬这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在写这个人的时候,有没有被他征服,或者试图把自己的理想放到他身上?
王:我写《大清相国》,没有想过什么是正能量;而我写《国画》之类的作品,这种写作本身就是正能量。陈廷敬这个人物的塑造,首先是依据史实。历史上记载,陈廷敬学养深厚,品行端方,清正廉洁,功成名就。他晚年的时候,康熙皇帝评价他说:“卿为耆旧,可称全人。”同时,我也在这个人物身上投射了自己的理想。我敬仰这样的官员,希望这样的文学形象能给今人以启示。
范:写官场,笔耕至今,您希望在这个领域实现自己怎样的创作目标?
王:我眼里没有题材意识,而所谓“官场小说”更是我反感的说法。我这样配合采访而用了这个概念,实在是勉强为之。我是个没有文学野心的人,成不了也不指望做成伟大的作家。我的所有文学努力,都是尽力而为,不使读者太失望就行了。
二
《漫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与善的深情礼敬。余公公和慧娘娘,坦坦荡荡地互相欣赏,互相扶助,两个普通农民的关系如光风霁月、高山流水。既诚恳认真,又刚强坚定的人格,如同老玉包浆,焕发着朴素而浑厚的光芒。小说叙事娓娓道来,散淡家常,古老的乡村、纯净的心灵相得益彰,诗意的乡愁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跃然纸上。——鲁迅文学奖《漫水》授奖词。
范: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出自今年,那就是您以“官场小说”知名,而以乡土小说收获“鲁奖”,同时您曾经仕途顺畅,一路上升,但您在《我不懂味》一书中也坦言对当代的乡村有所隔膜。怎么看待这种自身文学创作的错位感?
王:我对当代乡村的确有些隔膜。我的乡村叙事小说,几乎写的都是我过去熟识的旧时乡村。《漫水》这个中篇小说,故事的中心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今天对过往的伤悼。沈从文八十多年前写《边城》的时候,当时的湘西茶峒早已不如他笔下那般纯美了。沈从文在那些有关回乡的散文里,真实记载了当时的湘西也受到现代生活的侵蚀,乡下的小伙子会在大白天玩手电筒,比谁的手电更亮。文学,也许更多的时候是在回望过去。
范:个性平和散淡的人,其实才是与乡村一脉相承,尤其是与传统的、理想化的田园相契合。我觉得您的乡土小说的写作,文风上有一种“平淡之味”,比如从《也算爱情》、《桂爷》到《漫水》。您在创作的时候都想些什么?是什么状态?
王:日常化叙事,应是我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我写那些所谓的“官场小说”,也是写生活的日常状态,而绝少离奇曲折的故事,更是刻意拒绝所谓宏大叙事。越是日常化的生活,越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写这样的故事更能反应生活的本质。我笔下的“官场小说”同乡村小说有“浓淡”反差,也许是因为这两块生活本身的成色存在差异。官场无风三尺浪,而乡村有风也是月影婆娑。《也算爱情》其实也是颇有些不平淡的,但小说里的人物,哪怕是吴丹心那样被政治扭曲了人格的人,也有可爱可怜可叹之处。《桂爷》写的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而深层却有着乡村人物的大尊严、大温暖。
范:您的乡土小说,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您会在下一步的创作中去书写当下的乡村吗?会或者不会,为什么?
王:我前面说了,写不好关于当代乡村的小说。文学有时候需要距离。我目前正在创作的一部写乡村的长篇小说,大概从六七十年前写起,写到我熟悉的上世纪90年代。
范:您说最喜欢自己的乡土小说,喜欢的是其中的什么?是文中展示的自然散淡的生活状态?是那种最接近自然的质朴人性,还是什么?
王:我写了不少关于乡村的中短篇小说,那些小说虽不怎么好,却都是自己最看重的。
我之所以喜欢自己的乡土小说,除了喜欢文中展示的自然散淡的生活状态,以及乡村人物身上的质朴人生,写作本身的过程也是令人陶醉的。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把自己置身于家乡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下。笔下的人物,尽是我熟识的习性、声口和形象,他们都是家乡的地域文化陶冶出来的。
我感触最深的是在创作中篇小说《漫水》的时候,体会到乡村人物语言是那么的有意味。他们有自己的语汇,有自己的修辞,有自己的幽默,可惜文字符号不可能完全表情达意。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用心留意,某些很土的乡村方言也可以在词典里找到读音和意思吻合或相近的字。我并不认为严格地使用方言才是乡村小说成功的必由之路,方言文学化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种,不少经典作家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比如周立波对东北方言和湖南方言的处理都到了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地步。我的那些乡村叙事小说虽存在很多不足,但我在学习借鉴民间语言上也有些心得。我使用民间语言的时候,学到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词汇、修辞,而是家乡人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等,这些都通过他们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
范:“官场小说”和乡土小说在您的创作中,是不是构成了一种张力?您是不是在官场文学中体验过紧张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压力之后,在乡土小说中去寻找释放和皈依?怎么看待左右手两种文学之间的关系?
王:我在各种题材的创作之间穿梭跳跃,仅仅是不同时期兴趣的冲动所致,并不是刻意为之。读者朋友们注意到,我写不同题材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就像做衣服,西装同衬衣,面料肯定不同。语言是小说的材质,只看这部小说是西装,还是衬衣。
三
今年采访王跃文,一定不能不谈他的《爱历元年》。作家的年龄到了一个程度,一定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在我的采访中几乎屡试不爽。因为年龄带来的对生命对人生的感知,总是在潜移默化之中突然跳出来,把人吓一跳的。《爱历元年》的写作就来自王跃文所感知所思考的中年危机。
范:《爱历元年》描写中年危机,您认为中年危机的本质是什么?作家是否会面临中年危机?
王:中年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只有自己进入中年才知道这个生理期是真实的。刚刚进入中年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
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都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人生的意义也许还没有敞亮显现。另外,父母开始老迈,孩子尚未成人,事业成败早已成局,过去的岁月有无意义也值得怀疑。中年危机是桩桩件件的事实,而不是玄妙的概念。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这种宿命感也许都在中年时期强烈地凸显出来而已。《爱历元年》涉及到很多话题,中年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
范:从特定的文学题材,写到自己所亲昵、熟悉的生活故土,再到正在观察、面对的生活现实,这与您自身的生活变化,尤其是心理变化是否相关?是怎样一种内心轨迹,促成了这样的变化?
王:人走进中年,自然而然开始回望人生。这时候,心开始变得更加柔软,感时伤世的情怀油然而生。很多过去看重的东西,此时感觉轻如鸿毛,比如宠辱得失,功名利禄;而过去没怎么顾得上的东西,此时在心里变得沉甸甸的,比如家人间的陪伴,朋友间的问候,甚至陌生人一个善意的微笑;这时候人也变得更加简单,比如开始喜欢听鸟声,听风雨,看日出日落,又回到爱数星星的童年。《爱历元年》里写了很多看似琐碎的闲笔,实在是我内心最柔软处血脉的跳动。
范:书写日常最大的难度是把平淡的生活写得有味,您是否如此认为?您如何去塑造平凡人?现实中的我们很难被身边某个人打动,您如何让人物动人?
王:我习惯了写日常生活,写生活最琐碎的故事和情态。这对作家是个考验。当年编辑约我写《国画》时其实是很担心的。《当代》杂志副主编周昌义先生曾在《文坛那些事儿》一书中讲述过这个故事。他感觉我的中篇小说都没有太曲折的故事,写得琐琐碎碎,支撑小说的是流溢于文字间的某种味道。他说靠某种味道支撑一个中短篇是可以的,支撑长篇小说则令人担忧。而他读了我的《国画》稿子,发现居然就靠某种味道把一部长篇小说撑起来了。我理解周昌义先生所说的味道,应该是我在小说中表现的细腻的生活肌理、可以触摸的质感、读者可以感同身受的对生活的理解,等等。我写《爱历元年》同样是这么做的,我会把很不起眼的生活琐碎写得很熨帖,尽管让人感觉“悠然神会,妙处难与君说”。
范:可以谈谈您的阅读吗?
王:我读书真的是先天不足,都是后来恶补的。我的中小学阶段除了课本,几乎没有书读。我就读的中小学都没有图书馆。大学时我循规蹈矩,老师指定的必读书目,我都认真去读,主要是古典作家的作品、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那时,我一天到晚手捧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很遭同学们鄙夷,因为我显得很老土,还在看现实主义的作品。那时同学们中时髦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加缪的《鼠疫》,以及贝克特和卡夫卡的作品。我很少看这些书,也觉得很心虚似的,但我确实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大师迷住了。我尤其对托尔斯泰情有独钟,他对人的灵魂的探究,他表现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道德的反省,都给我很大的震撼。
读书也是有奇遇的。张爱玲说,亘古洪荒,忽然有一日相遇,也不过是轻轻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理解她所说的意思,就是奇遇。1988年,我因事经过湘江边的一座小城。小城很是清寂,窄窄的街道还是青石板路。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县城一样,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照例要去逛逛。不料在一堆特价书里发现了一套1985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下册,原价5.85元,打三折,1.75元。我买下了。我与这本书的相遇,觉得就是缘分,就是奇遇。
范:“我很想写一本没人看的书”,我觉得这是一句反讽,您觉得这句话的讽刺意味在哪里?如何看待“没人看的书”?
王:畅销的书未必是好书,没有人看的书必定不是好书。这是我一惯的看法。我的小说写得并不好,很多毛病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实在要感谢朋友们的错爱和宽容。我曾在微博里说,我不敢承认自己的作品是经典,但都是真诚和血性之作;不管对我的作品有多少批评,我敢说自己笔触的终极指向都是温暖和光明的。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