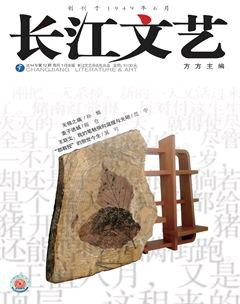扬州一梦
赵柏田
从徽州到扬州
在我的老家徽州,男人长到十六岁就必须出门学做生意,外出经商一般有两个优先选择的去处,一是杭州,一是扬州。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堂兄张沄就毫不犹豫地定居杭州了,他一次次地向我发出邀请。最后我还是来到扬州,做起盐业生意。
我选择扬州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有多喜爱,只是这座城市里做生意的歙县老乡比较多。尽管这座大运河西岸的繁华城市在四十年前满人入关时经历过一场惨绝人寰的屠城,但这时候已渐渐恢复了元气,成了国内最大的盐业中心。朝廷专管盐业的两位大员巡盐御史和盐运使都驻节在这座城市。
我投资盐业是因为我有办法从官府搞到一种叫“引”的准销证。有了这张政府批文,我就可以向划定的区域贩运一定数量的盐。我购入一“引”的价格是一两三钱银子,据此可以贩运二百二十五斤盐。我的生意主要是在武昌、汉阳一带。但我一次也没去过武昌。跑脚头的都是一些运商,他们赚大头,我作为一个投资人,一直都住在扬州城里,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
我赚了一点小钱后,到处都盛传我富甲一方腰缠万贯,登门或写信请求我捐赠的亲朋好友不计其数。这些人大多是靠别人馈赠勉强度日的落魄文人,体弱者向我讨钱治病,体健者借钱远行。有一位朋友离开扬州前往京城时,问我衣箱内是否有旧皮袍可赠他御寒。大名鼎鼎的孔尚任来扬州,我的一位侄子负责接待,因囊中羞涩,向我索白银数两,说是要购买鹿茸等礼品送给这位偶像,我拿出几十两银子都没皱一下眉头。
对这些找上门来的求助,我基本上都一一予以满足。我一直牢记着父亲的教导:一夜暴富,其祸非浅。虽然我不算什么暴富之人,和我住在同一街区的无一不是巨商大贾,他们才是真正的暴发户,但父亲说得好:尚礼义者,必不妄取,其道近贫。资本天生就是带着血腥的,我这么做也是减少一些身为商贾的原罪吧。
诸君可能好奇的是,从商大半辈子,我到底有多少身家?对此我也不想有什么保留。生意做得最顺遂的几年,我在扬州新城东南角买下了一进宅院,此地在马王庙东,离通向大运河的通济门不远。我一说新城,诸君可能会惊哦一声,因为世所共知,扬州城由一堵自北向南的城墙隔成两部分,从前,官府和权贵的家宅通常在西边的旧城,东边新城则是做盐业生意发达了的商户们的居住区。这座城从战乱中恢复的几年间,东部新城突然膨胀了开来,拥入了大量新主人,出现了许多带着精致花园的豪宅名园,这些新主人大多是帝国经济复苏中掘到第一桶金的徽州富商,他们挟着资本的威势,购置大片田产,广置山石楼阁,生活奢靡无比。说来惭愧,我虽然住在这片富人区,我家宅院实在平凡无奇,但我还是很得意于宅院里的两处建筑,一处是我的书房“心斋”,一处是我编刻书籍的“诒清堂”。它们使我区别于那些脑满肠肥的暴发户们。这两处建筑落成、朋友们前来祝贺时,我还在屋前亲手种下了一排垂柳,恭迎来宾。
我在扬州城郊还有一片地产,收取田租。在距扬州城约二百里的如皋小城,还有一处别业。在老家徽州北乡凤凰村,有田一顷余,一个远房亲戚替我打点。在南乡的柔岭,还有一处置于我名下的房产,是先父留给我的,但在1694年的一场大火中,这片房产连同祖上遗物已全部焚毁了。
家父曾经金榜题名,任职刑部,外放山东督学,虽然后来因祖母去世丁忧三年,他再未踏入仕途,成了一个隐退乡间的老学究,我唯一的哥哥一向体质孱弱,经常吐血,是个俗称的痨病鬼,他去世后,父亲更是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我身上。但成败未卜的科举之路上,除了十五岁那年中了个秀才对他堪可安慰,以后的十几年里我一直名落孙山。
是我圣贤书读得不够多吗,还是八股文做得不够漂亮?父亲认为是考运未到,在他的竭力主张下,二十岁那年我来到京城,入读国子监。国子监生俱可参加顺天乡试,而顺天府乡试中额的比例较他省为多早就不是秘密。父亲满心以为这么做是为我成功添加了重重的砝码,但因我取得学籍的时间稍晚,并没有取得参加那一科考试的资格。再在京城待三年,费用委实太大,于是不久我就带着一个州同的虚衔回到了扬州。
我当然明白,像我一样虚衔待任者为数众多,即便我等上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州同。要获得实授,还是要参加考试。但不久传来的一个消息让我彻底蒙了,南直隶的督学大人作出了一项保护地方考生的新规定,鉴于国子监生均已获得任职候补资格,一律不得参加南京乡试。我毅然转向投身商贾,就是源于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对一个心仪仕途已久的人来说,功名之心早成了附骨之疽,怎么能轻易根绝呢?在扬州做了几年寓公后,当我听说朝廷为筹资征剿厄鲁特部噶尔丹公开捐官时,我当即以白银一千两为自己捐得翰林院孔目的虚衔。我的一个远房叔父在老家听说我捐得官衔后,写信询问,“贤侄捐纳经衔,是何衙门?”他还以为我真的要风尘仆仆跑到京城去任职哩。还是一个熟稔医道的朋友洞悉我此举的真实用心,他说我花出一大把银子去捐得一个翰林院的末席,实际上不过是医治内热的一把清凉散而已。我在回信中调侃说,不知此一把清凉散,较之您老的一味逍遥汤,哪一个喝起来更可口些?
在语词的密林里
自小我就体质孱弱,胃口不好,菜中就是有一粒芥子大的肉末我也畏若毒药。如果吃到了油腻食物,我会连日腹泻,若不巧有客来访,那真是苦也,腹中蛙鸣一般,坐不了多久我就得往厕所跑。不只如此,我的耳朵也不太好使,与客对谈,十句之中能听清三五句算是好的了。我之所以是这样一个弱柳体质,原因在于先天不良,家母怀我时曾患疟疾,一连几个月都遵医嘱只喝梨汁。
但我与朋友们欢聚时就像换了个人一般,议论风生,妙语联珠。平时那种病恹恹的神态一扫而光,只觉得全身充满力量,思路也分外活跃。孔尚任先生任河道督修官时,在扬州住过三年,他发起的雅集,我是常客。其间规格最高的当数1686年深秋那一次。那天傍晚下着雨,十六位文士齐聚孔先生官邸,赋酒联诗,就连前朝著名遗民冒襄也带着儿子冒丹书从如皋赶来了,我虽不才,也叨陪末席。那天与会诸君听着潇潇夜雨,喝酒、吟诗到天明方始散去,孔先生在自家门口放了一个诗筒,让那些因故未能与会者将自己的诗作投入筒中,后来他把那次雅集的诗篇汇成《广陵听雨诗》刊刻,公认我的诗为第一,有孔先生写给我的信为证。
孔尚任先生把我评为雨夜诗会的领袖人物或许言过其实,但那一晚相聚的十六人,大多都是我极熟的朋友,这样的场合,我自然没有理由感到拘束。孔先生对我表示好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聚会时我带去了许多书籍送给他,包括我自己刚出版的两部诗文集。在我们的时代,出版文集还是一桩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论是国宝级巨匠还是地方上默默无闻的文士,都梦想着有朝一日把自己的大作付之刻版,刊印天下。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个人既要有出众的才华,更要有超群的财力,才能把自己的著作刊刻成书。苏州有个老作家,公认诗文双绝,他七十多岁了还没有自己的一部集子,最后他的门人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在他死前一年集资为他刻了一部稿。我这样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声望的文艺爱好者,凭着手上几个钱,年纪不大就出版了两本集子,肯定有许多人对我不服气。
我那个私家书坊名叫“诒清堂”。我家书坊的刻本,通常会在每页的版口下脚印上“诒清堂”三字,包括我自己的所有著作在内。1684年春天我出版了第一本文集,这是一本大杂烩式的集子,里面收罗了几十篇小品文和一首华丽的长赋,基本上都是游戏笔墨,还有一篇为皇帝南巡而作的颂扬文字。一位年长我三十岁的老名士在序文中盛赞这些文章与两千年前的滑稽之雄庄子寓言一脉相承,都是以小观大的佳作。这篇序文我足足排队三个月,花了十两银子才到手。
饶是如此,这本书在坊间还是大受欢迎,它漂亮的版式和精美的刻工让各家刻坊争相模仿。尽管这本书形式大于内容,但它的刊刻问世对我还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它表明,我已经完成了从盐商到文化人的成功转型,从今往后,我就是扬州文人大家庭中的一员了。
接下来几年,我的写作方向突然转入一个幽秘的领域,我热衷于汉字的排列组合之妙,走上了一条摆弄文字以娱世的崎岖小径。我走在语词的密林中,这里采撷几片,那里摆弄几下,寻章摘句,翻新花样,皆能收到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这都缘于汉诗运韵和遣字的奇特,它有着拼音文字所不具有的丰富和多变,简直炼制丹药一般神妙。比如说我最爱玩的“回文”,它既可以从上往下、从左向右读,也可以从下往上、从右向左读,用不同的读法读出的诗虽有相似,但语义却绝非一样,上下颠倒或左右移位之后,字和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主语变成了宾语,动词变成了名词,思念变成了怨恨,湖泊变成了大海。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走在这语词密林里的人,在我之前一千余年前的公元四世纪,南北朝时的女诗人苏惠就在一幅织锦上绣出了变幻无穷的《璇玑图》。
我为此投入了无限的热情和心力,但在正人君子们看来,我离严峻的学问正途越来越远了。前面说过的我的一个远房叔父,此时已官拜御史,他在京城收到我寄赠的几本著作后,特意写信来说,贤侄的文字虽然琳琅珠玑、粲然夺目,毕竟是雕虫小技,名不副实,还是要出经入史,图其大者,到时必定“实至而名自彰”。御史大人的话在我只是耳边风,此后我再也不给他寄书了。
此时,我在语词密林中探索的兴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些字、词、韵,在我睡梦中都吵吵嚷嚷,我必须给它们一个秩序,重新安顿它们,才得以安生。我开始设想一部叫《奚囊寸锦》的秘密之书,这本书总计由一百首诗组成,用数量不等的汉字拼成各种图形,比如三角形、圆形、树叶形等等,所以这本书也是一本由一百幅图形组成的书。但后来我的盐业生意破产了,这书就一直没有刊刻出来。
共同写作的书
真正带给我无上荣光的,是我将近五十岁那年出版的一本叫《幽梦影》的小书。一般人想当然地以为这本书谈论的是梦境,读过它的人会知道,这本小书谈论的是犹如电光石火般易逝的生命本身。我的朋友江之兰说,多病者多梦,一个人辗转病榻时就会被梦绑架,梦见牛尾,梦见蕉鹿,梦木撑天,梦河无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幽梦影》这本书与病无关,与梦无关,它的核心乃在一个“影”字。这个影是什么呢,就是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暼,就是那些让我们的灵魂愉悦、奔放乃至颤栗的一瞬间。
是啊,生命中有那么多美妙的瞬间,都无可奈何地逝去了,一个真正懂生活的人应该凭借娴熟的技巧抓住它,就像鸟儿抓住脚趾下的枝桠一样。这正是我在这本书里首先要阐发的问题。
侍弄文字大半辈子,我明白,所有的文字语言,总是带着我们灵魂的印记,是心的影子。虽说梅花之影妙于梅花,然则,没有花之妙,又何来影之妙?生命是本源,它如莲花之一瓣,伸展得愈是阔大,其上承载的一滴水珠才会更加圆润。也正因为此,我认为人活于世的一个重要功课就是磨砺我们的情感,锻打我们的感官,使之更加灵敏、更加锐利。这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与自然万物协调起来,自然所固有的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不仅仅寄寓在绘画、戏曲和文章里,更应该渗入到我们整个的生命里。譬如说插花的艺术,我的一个发现是,插花的瓶胆之高低大小,须与花相称,而色治理之浅深,则应与花色相反;鉴玩古物时,器皿上的冰裂纹是极雅致的,但这纹路宜细不宜过分肥大,如果用作窗栏杆,那就太不经看了。“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一种于虚空的美感中发现观看与距离之关系的喜悦如清风一般罩住了我,谁说我发现的不是世界的秘密呢?
当我用警句、格言说出这些发现、这些诘问的时候,圈内的朋友们对此表现出了无比热情。他们说,我别出心裁的写作是一次发现。他们说,我说出的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眼前所无的那种东西,即所谓的共同经验。他们接着我谈论《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的一段话说,如果说《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忆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那么张潮的《幽梦影》就是一部趣书、一部快书。当1697年春天这部格言集刻成、送到朋友们手上后,他们寄来了各种各样的跋语、小序和题词,跟我讨论他们阅读后的感想,有些甚至把评语和批注直接写在了书的空白处。其实在这部书稿正式刻成前,我的手头已经收集了一些朋友们的评语,并把这些评语用小字刻成双行,零散地穿插在正文之间,考虑到朋友们会出于礼节性地予以批注,我已经在那些评注的后面留了一些无字的空白处,以便将来补入(这些预留的无字空白因在木版上未经刻刀触及,在书页上显示为一片黑色)。
如果把初版上的评语比作第一层沉积物,那么,这些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新增加的批注是又一层沉积物,它们一层层地叠加上去,每一层都有着独特的风格,有着绝不重样的故事。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一项个人写作,已经成为一桩公共文化事件,成了一项集体性写作,而我的这本小书也已然走在了成为经典的大道上。
如果从这本小书初版的1697年算起,补刻、加印一直到1707年才基本结束。原先疏朗、简洁的页面,已被挤得满满当当。我原创的格言不过二百余条,收入书中的评语则多达近七百条,平均每一条格言都有三四条评论与之构成对话,评论的字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文。它就像一个众声喧哗的声音仓库,里面封存着一百余位朋友的声音。书中最初的评语和新近补入的一批评语已经时隔十年,在这十年中,有些朋友已经去世了,但在这本书里,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他们虽死犹生,继续与年轻的一代进行着热烈的对话和辩论,他们的智慧不时在书页中闪烁。我想,这是《幽梦影》的最大魅力之所在,不是我张潮一个人写下了它,而是一个时代的文人们共同写下了它。
撒向京城的网
一些朋友打趣说,一个旅行者来到扬州有三件事必做:登平山堂,吃蟹粉狮子头,看张潮。某次,杭州的朋友陆次云来扬州,酒宴中对我说,还在途中未抵扬州时,有朋友说,君此去,当往晤张山来(山来是我的字)先生矣。既到达扬州,多位文友询问:君曾晤山来先生否?我听了一笑置之。这么些年来,虽然我薄享文名,但我的声名事实上从未越出维扬这一帝国最富庶的地区,我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名扬四海,《幽梦影》这本小书的成功,使我把目光瞄向了遥远的京城。
我的目标是年轻的王爷岳端。此人是本朝开国元勋努尔哈赤的曾孙,他的祖父就是让人谈之色变的名将阿巴泰。小王爷对汉族文化充满了热爱,学诗、学画、读典籍,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来自南方的文人学士,有两位就是我的朋友,一位是浙江人周之枢,一位是扬州人张鸣珂。凭借这两位的关系,我给王爷殿下发出了第一封信,表达了敬仰之情,亟盼得到他的顾盼,随信还附赠了先父的著作全集和我的一些作品。信寄出了好久都没有回音,我沉不住气了,向王爷身边的两位朋友打听。张鸣珂说,文字之交,说深颇深,说浅也颇浅,改日你再修一书就是。
1696年冬天,突然时来运转,一个叫朱襄的朋友转来了岳端小王爷的信。信中赞扬了我的才华,盛邀我赴京前去一会,信中还附了一组七言绝句。小王爷的古文功底不甚好,只能说粗通音韵平仄,但收到信还是让我喜不自禁。我即刻回信说,“即欲趋叩红兰殿邸,躬谢高深”。但扬州与京城相距甚远,我病恹恹的身子怎受得了舟车劳顿之苦,此事延搁了许久,我还是没能动身,只得托朱襄向王爷转达我的歉意了。
其实见不见王爷倒不打紧,只要他愿意替我作序推荐,为我扬名京城文坛助一臂之力,我愿足矣。京城毕竟不同地方,京城文坛即便放一个屁,满天下也都能听闻,何况一句来自王爷的褒奖呢。几个月后,我收到了朋友们寄来的岳端王爷的新著《蓼汀集》。他赠我的那组七言绝句,赫然出现在这部刻工精致的著作中。此时适逢我的《幽梦影》刻成,我不敢怠慢,第一时间把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打了两包寄往京城,一包六册寄给朱襄,一包四册寄给刚被岳端王爷罗致到身边的我的徽州同乡,一个叫广莲的僧人。在信中,我托他们帮忙,恳请王爷读后赐评。到了年底,广莲传来了好消息,说王爷读到这部格言集十分喜欢,已经答应写一篇序文予以推介。但我望穿秋水,也没有等来那篇序文,我写信催问,广莲说,可能王爷前阵子太忙,没顾得过来写吧,他向我透露,王爷雅好字画,特别喜欢徐渭的真迹,如果你能搞几幅来,讨得王爷欢心,这序文的事就有着落了。
市面上徐渭的真迹很少,且索价奇高,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花去一大笔银子,才搞到了他的两幅真迹,一幅小品,一幅水墨芭蕉,另加一轴查士标的书法。1698年秋天,我把这些价值不菲的礼品寄往京城,不久传来消息说,岳端王爷愿意“屈尊”收我为弟子了。
尽管为了编织京城这张网耗去了我无数精力和钱财,但我想要在首都文艺圈里崭露头角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王爷始终没有交出他承诺的那篇序文,也没有为我的新作《幽梦影》写下哪怕一条评语。不只如此,广莲、朱襄答应我向京都名家索求评语一事也毫无进展,王士祯侍郎、高士奇学士和诗人曹贞吉等等这些执掌京城文艺界牛耳的大佬们可能把我的书拿去垫了桌脚了。我费尽心力把网撒向京城宽阔的水面,不仅没钓起一条大鱼,连小鱼小虾也一无所获。
我的出版生涯
每次从扬州回徽州老家,我走的都是从运河转入新安江的水路,中途必在杭州盘桓几日,访亲拜友。有时,在吴侬软语清晰可闻的小巷客栈里醒来,我忍不住会想,设若我选择了住在杭州,展开的命运或许会是全然不同吧。
1694年夏天的回乡之旅,我在老家住不多久就出来了。因为有一场约会在杭州等着我。我要见的是杭州秀才王晫,一个我闻名已久的出版人。在这之前,我们已有数番信函相通,我寄赠了他诒清堂新刻数种,他也把自印文集《文津》回赠了我。
王晫家在杭州城北一条叫松溪的小河附近,距运河上的北新关不远。他把会面地点选在了“霞举堂”。其时正值王晫的新著《今世说》杀青,这部脱胎于南朝刘义庆的当代逸闻录成了我们谈话的中心。交谈间隙,我打量着这座对我来说已颇不陌生的宅堂,间架甚为高敞,但数处檩条朽烂,明显着是需要修葺了。看起来王晫的刻书生涯没给他挣下多少钱,只是依仗着老底子厚实,维持风雅于不堕罢了。
果然他跟我叹开了苦经,说写作和出版计划皆受挫于财力不逮。对他的这些苦衷,我自然颇有同感,做出版,不管哪个时代,都是一项烧钱的活计,我要不是仗着做盐业生意挣下的几个钱,只怕早就喝西北风去了。我邀请他参与我主持的几部文选的选编,他未置可否,相反的,他热烈鼓动我参与到他已经着手在编的一套丛书中来。这套丛书所选文章题材多样,文风庄重与诙谐并出,他已经给这套书定名为“檀几丛书”,据说这个书名来自一张著名的“七宝灵檀几”,那张檀几有特异功能,几案上的文字,随意从哪一个方向看去,文字辄现,且随着光线明亮的变化,语义也会随之变化。
最后商定,由我负责出资刊刻,王晫主要负责选编。我回到扬州不久,王晫就已寄来了一大包他前期选编的文章。以后大概有三四年时间,我们的通信主要围绕着这部丛书的选编和出版工作。尽管时有龃龉,但反复辩驳,我们总能形成共识。共同做一件喜欢的事是多少难得啊,我们有必要为一些小分歧分道扬镳吗?
这部书的初刻本,花去了我六十两银子,六十两银子不算多,但如果我说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六品官一年的俸银,大概也没人会以为我出得少了。事实上这部书刊印没多久,我们就已在计划推出续编。就在此时,我接到了朋友孔尚任的来信,信中说,他的一个诗人朋友、也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王士祯在京城读到此书,大为激赏,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文章供我选用。接读此信,我欣喜欲狂,众所周知,几十年前王士祯初涉仕途,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负责本城司法监督的扬州推官,他白昼办理讼案,夜里常和文朋诗友们欢饮达旦,本城红桥一带还保留着他和朋友们雅集、修禊的旧址。一个名声显赫的大人物主动要求加盟,这个机会我怎能轻易放弃。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王大人能屈尊将文章交我出版,实在是备感荣幸。我从王士祯的集子里选用了三篇,一待清样出来就寄往京城,同时我附了一函给孔尚任,托他向王先生讨一序文。
奇怪的是,就像当初岳端王爷为《幽梦影》答应作序没了下文一样,王尚书的序文也一直没到。我不死心,又将另一部分清样寄给王士祯,并于年底再度去信汇报刻书进展。全是石沉大海。我决意不等了,1698年春天,这套书印毕,我拣出两部寄往京城,一部呈送王士祯,一部赠给从中牵线的孔尚任。大人物都忙得很,他要真没空回信,也只有随他去了。
其实我的出版生涯在这部书问世前的十年就开始了。刚踏入出版界的我气冲斗牛,什么样的选题都想做。我的出版计划中没来得及实施就夭折的包括一部讽刺寓言集、一部游记、一部语音学著作和一部兼具道德、经济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布栗集》。有时我想,我死后,这些未曾问世的书会在另一个世界和我相遇吗?
为我在入行之初博得巨大声誉的是八卷本的《虞初新志》(后来扩展到二十卷)。虞初是汉武帝时的一个小吏,时常穿着黄衫,坐着牛车,满天下跑来跑去采访异闻。我把他入了书名,是想表达我承续的是唐人传奇、甚至《搜神记》以来伟大的叙事传统,而不是一味以搜古、猎奇为尚。今日坊间把我这部书与乡间学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同列“小说”,真是岂有此理!须知道,我这部书的选编标准有三,一是文章所记人和事必须是当今或前不久发生的,二是须有较高的文学含量,三是所记事实,奇特古怪固然好,又须不失真实。这一来就把那些飞仙侠盗、牛鬼蛇神全都拒之门外了,也就是说,我所选编的,乃是一部完完全全的非虚构作品,这又岂是蒲松龄之流及后起的仿造者那些稗官小说能同日而语的?
当然,要从浩如烟海的时文中找到符合这些标准的名家之作,近乎在黑暗中摸索。吴伟业、朱一是诸公与我家有世交,曾为家父文集作序,我家藏书中有不少他们的著作,选编起来尚不太难;尤侗先生的文章,我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欢,很早就买了他的《西堂杂俎》,集中收录的那篇,就是采自那本集子。名姬董小宛的那篇传记,是冒辟疆先生亲自寄来的。但好多作家新出的集子,家中所无,我只能给朋友们写信,托他们代为寻觅、推荐。
为了编好这本书,我披沙拣金,潜海采珠,不知燃去了多少松油,也不知抄钝了多少管毛笔。但发现一篇好文章的欣喜,足以抵过所有的劳累。一个叫徐芳的前朝翰林,隐居不出,专事写作,时人都把他看作一个鬼怪故事作家,但我读了他的几篇写实风格的作品后,觉得鬼怪故事不过是山岩上滚下的几块石头,他这座山岩下的矿脉,还是现实主义的,所以毫不犹豫地从这个作家的两个集子中选用了八篇。余怀记叙秦淮河往事的《板桥杂记》,后来为他带来巨大的声名,我收入此书时还只是刚写成不久的稿本。但我最大的困难不是搜来的文章不够多,而是朋友们推荐的大多很难达到我前述的三条要求,不是文笔老套,就是故事了无新意。直到我遇到陈鼎,一个从云南旅行回来经过扬州的传记作家,读了他那部有着百科全书般野心的《留溪外传》,我才感慨天下好文章的种子还是没有死绝,他那部稿本实在是个宝库,我只是从里面选用了一篇八大山人传记和几篇动物故事,写狐、写牛、写狗,他也如写人一般生动,我一直还记得他写那只烈狐的几句话,“如海棠一枝,轻盈欲语”。另一个让我刮目相看的新作家,是前面说到的那个从杭州跑到扬州来看我的陆次云,他早年在江西做过县令,辞官后专事写作维生,此人性情诙谐,一肚子好故事,我选了他的两篇传记和一则谈西湖寺院的文章,在我看来,写西湖山水的文章多矣,当以陆兄为第一。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周亮工和钮琇两位作家。有一天,有人送来一套临野堂刻本《觚賸》,说写这本书的钮琇真是锦心绣口。这个古意盎然的书名一下吸引了我。有人说,“觚”是上古时代用来书写的木简,也有人说,觚是一种国家典礼时使用的铜制酒具,既不圆,又不方,故名为觚,后来成了政事的代称。木简也好酒具也好,我揣想钮琇之所以取了这个怪怪的书名,是在意指他写的不是大历史,而是有着体温、蒸腾着烟火气息的边边角角的小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实在深得我心。我打听到钮琇时下正在广东某地做县令,且此前曾在河南项城、陕西白水等地做小官,怪不得他的笔下如同打开了一扇扇奇异的窗口。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写女侠“云娘”,一帮男人在她面前直如污泥,真是有六朝志怪的文风;一篇写熊廷弼的传文,说熊大人督学江南阅卷时,边上置酒一坛、剑一把,读到好文就浮一大白,读到烂文就舞剑一回,以吐胸中闷气。印象至为深刻的还有他写北京妇人去摸城门门钉的习俗,能摸到的姑娘可以找到如意郎君,结过婚的则可保一家平安,这种博物式的写作读来真是忍俊不禁。我选了他的一篇吴六奇将军传文,又从吴、燕、豫、秦等选了八篇,想着有一天能与这个我喜欢的作家把酒论文,却总是没能遇上他。
周亮工先生曾为家父文集作序,我编此书时,他已去世三十多年,我家所藏只有一部他早年的《赖古堂集》,他后来新刻的集子都没有。适逢亮工先生的公子周在都擢升扬州同知,我找到他索求其父著作,在都兄竟然还记得亮工先生与家父交往的事,慨然相赠周亮工大作《读画录》、《印人传》、《因树屋书影》等数种,后来收入集子的十余篇艺术家传记,就是从这些他赠我的集子中采编的。
与王晫的合作告一段落后,我单枪匹马开始了另一部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之所以决定撇开合作者王晫单独来做,是因为我决定把合编的《檀几丛书》的续编更名为更容易讨上面喜欢的《昭代丛书》,遭到了他的反对,认为这将会影响新书在书坊的销售。我认为,以“昭代”作书名正体现了我作为一个出版家和文选家的与时俱进,本朝开国五十余年,平三蕃、收台湾、征讨厄鲁特部噶尔丹,不特武功之盛为前朝所无,文教之隆也超越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眼下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所以让我们的出版工作得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甚至得到最高当局的关注,不是更有意义吗?王晫借口怕影响销量反对我改名,实际上是鄙视我的颂圣行为,认作是一种向权贵的主动趋附,唉,他老了,有此陈腐之见也随他去吧。
此书既然是颂扬当今的文治之功,入选诸家必须是群星荟萃,足够彪炳千古。所以皇帝宠臣和当代巨公们的“高山仰止”之作必予以优先考虑。其他我约稿的对象诸如毛奇龄、阎若璩、毛先舒、吴肃公、孔尚任、魏禧等虽非朝廷权臣,也都是文坛巨星。为了让此书有足够强大的阵容,我还约请了五十位文坛前辈挂名“编校”,这些人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已经老得行将就木,当然不可能真的来帮我选文、校样。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编选原则,不好明说,但我必须心里有把尺度,那就是不能把那些谈论明清交替的作品收进来,以免与颂扬盛世的主旋律相悖。戴名世先生曾交与我一文《孓遗录》希望我编入,文笔苍劲有力,堪称大家力作,但因所叙是满人入关前他在家乡所见民不聊生的乱象,我只得回信告诉他,“缘拙选名《昭代丛书》,故不便以明季流寇之惨录入,是以未获借光耳。”遭到退稿的戴先生老大的不开心,再也没搭理我。后来戴先生因《南山集》案发下狱被处死,证明我还是有先见之明。
我的前一本书《幽梦影》已经进入了一位亲王的书斋,焉知此书不会上达龙廷?我的计划是以一年一集五十种的速度推出,就像长江之浪一波接一波地向帝国高层冲击。当务之急,一是要收到讴歌当今王朝昌明盛景的好文章,一是要争取拿到有力人物最好是当朝大佬的推荐序文。
书稿编成后,我致信主政江苏四年的巡抚宋荦,请他赐一序文。几年前宋巡抚驻节扬州主持赈灾,我曾与之有过一面之缘,向他赠送了数种著作,交谈时他语气霭然,对我印象不错,为了增加成功率,寄出信后我又求助于一位经常出入巡抚衙门的一位姓姜的苏州朋友,托他有机会在巡抚大人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姜朋友告诉我,宋巡抚对我初编的书稿交口称赞,但什么时候写序没说,他答应合适的时候会再去催问。不久,传来了宋巡抚夫人去世的消息,我即刻赶往苏州吊唁,想着当面向巡抚大人请求赐序。但我的殷勤和姜朋友的协助都没能打动巡抚大人的心。书的版子已经刻好,冬天到来之前如果再不开印的话就需待来年开春了,无奈之下,我突然想到一人,此人即年过八旬的文坛前辈尤侗,我向他求援,老爷子一点也没有官场中人的那种臭架子,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就欣然命笔,写就序文一篇,总算替我救了场。
期待中的有力序文一篇也没有来,这书还要不要出下去?我还是不死心,这套书出到第三集的时候,我再次致信刚从左都御史升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祯。之所以厚着脸皮向王尚书再次开口,是因为之前我已经选编过他的许多文章,这部书里又准备选用他的一篇关于汉水地理的文章。但王尚书的回信只是修订了他自己的那篇文章,并推荐了他的一个已故兄长和两位亲戚的文章,写序的事提也不提。我再次致信,他却装聋作哑,对我的请求一直未予回应。唉,那些权贵们的心,真是坚逾铁石。
在我的有生之年,怕是再也看不到荣耀降临了。书还在一本接一本地出,但对那些当朝大佬和权贵们,我已心灰意冷。他们当他们的官,我做我的书,本就两不相涉,可笑我一次次地乞求他们给予承认。于今想来我的出版生涯真是写满了屈辱,说来还是名心太重,自取其辱啊。
树犹如此
1699年夏天,我落入了一个被人设计好的陷阱,生意接连败北,所有积蓄血本无存,只剩下田地、房子等一些不动产。更凶险的是,我还被构陷入狱,虽然不久就放了出来,但上下打点,我的家当已差不多全败光了。
在我人生陷入最低谷的时候,我曾请求平素肺腑相待的一些同行予以帮助,哪知道他们不仅不施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人心的势利和险恶,在我是亲见的了,但这一觉醒还是迟了些,为了躲避债主的催逼和这些中山狼们的构陷,我不得不搬到乡下去住。我刚离开扬州城,就传来消息说,债主们找不到我,把我的书房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把“诒清堂”前我亲手种下的一棵柳树砍了。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柳树的颓然倒下,兆示着我的扬州一梦至此已断。几十年间,听着柳枝间的清风,我在“诒清堂”里做着著书、刻书、印书的梦,如今梦随风逝,只有那走入千家万户的版刻书页,或许还会在寒风的摩娑下瑟瑟作响。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