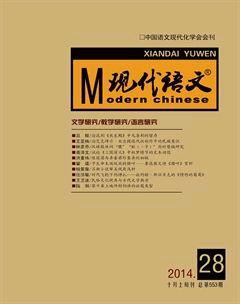男性视角下的爱情幻想
摘 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两位女性围绕一位男性而展开的爱情故事,我们姑且称之为“双美”故事。这些故事大概可分作共嫁一夫、兼有情人、又觅佳偶和引为知音四种类型。结合作者自身经历,“双美”故事实质上是男性在现实中失意落魄、无人理解,自身价值无法满足而形成的幻想。此外,“双美”故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初肯定个人情欲的思想,但其对女性情欲的肯定依然禁锢在家庭伦理和宗嗣观念中,是男性视角下的表述。
关键词:《聊斋志异》 “双美”故事 寂寞幻想 情欲 家庭 男性视角
在《聊斋志异》众多的爱情故事中,有不少故事表现两个美女恋上一个男子,建立家庭并相处和美,我们姑且称之为《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故事。一般的文学史教材都认为,聊斋的情爱故事反映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反封建礼教的观念,并对妇女抱有同情和尊重态度:“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鲜明的对比。”[1]然而,聊斋故事,特别是“双美”故事,却是在男性视角之下的爱情幻想,传统的诠释无法深刻触及“双美”故事的真正内涵。
一、“双美”故事概述
《聊斋志异》中,二女共事一夫的“双美”故事不在少数,《莲香》《巧娘》《白于玉》《连城》《竹青》《青梅》《小谢》《嫦娥》《寄生》《萧七》《阿绣》……这些故事虽情节各异,但均有一共通之处,即所有男子均能享尽齐人之福,家庭美满幸福。对于故事模式,可略分作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写两女共嫁一夫。这类故事在《聊斋志异》中非常普遍,所占篇目最多。典型的代表有《莲香》《小谢》《嫦娥》《连城》等等。故事中,书生结识两位美女,两女均对书生情真意切,或为人,或为鬼,或为狐,或为仙,但最终都能以姊妹相称,妻妾和睦,全心全意为书生创造美好的家庭生活。
《嫦娥》中嫦娥、颠当一狐一仙,俱归宗子美。《阿绣》中两个阿绣,一狐一凡,俱有情于刘子固。《莲香》中,桑生与狐女莲香相好,后又结识鬼女李氏,后来李氏附于张家燕儿而生,莲香投生韦姓少女,二人都嫁与桑晓。《小谢》写了不信鬼神的陶生结识两个爱捉弄人的女鬼,后二女均借尸还魂,与陶生喜结良缘。
其次,写男子兼有外室。《青凤》《白于玉》《巧娘》《竹青》《狐妾》等都是这类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男主人公本有妻室,在外结识佳人之后而发生一段爱情或建立夫妻关系。有些是春风一度的姻缘,有的被纳为妾,妻妾各守其分,妻贤妾顺。其中,情人或后纳的妾室为主要人物,是主人公的爱情寄托,家中妻室是伦常宗法的一部分,很少涉及情欲,甚至家中妻室只是顺带提及,作为隐形的背景。作者着重描画的是婚外恋情。
《青凤》以耿生和青凤之间曲折的爱情为主,对其婚外恋情进行浓墨重彩的勾画,家庭隐藏于故事之后。故事对耿生之妻并无正面描写,其妻只是传宗接代的一个工具,而青凤的存在,才是耿生的情欲寄托。
再次,写相继觅得佳偶。这类故事先写一位女性与男主人公相识,后来由此女引发出另外一名女性,不论结局如何,这位女性都为男主人公奉献了自己的爱。这类故事以《青梅》《红玉》《荷花三娘子》《辛十四娘》等为典型代表。
《青梅》中,狐女青梅引见王女阿喜嫁于张生,阿喜过门之后,青梅“执婢妾礼,罔敢懈”[2],不仅“双美”俱归,而且张家子孙繁盛。故事《红玉》与《荷花三娘子》也是如此,狐女红玉不仅指引冯生娶妻冯氏,又在冯生遭难时帮冯生再造其家,更敦促冯生求取功名。有了红玉,冯相如才得以在三十六岁时,“腴田连阡,夏屋渠渠矣”。荷花三娘子也是经狐女引见才嫁于宗湘若为妻,为其生子持家,虽然最后离宗生而去,但也给宗生带来了幸福和财富。
另外,写引为解语知音。“双美”关系中,“一妻一友型是较为中规中矩的关系模式:一为书生的原配妻室,一为书生的红颜知己。”[3]《娇娜》《宦娘》《香玉》等都是这样的篇章。
蒲松龄在《娇娜》中曾坦然道:“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孔生在娇娜遭遇雷霆之劫时以死相救,娇娜又“以舌度红丸入(孔生口),又接吻而呵之”,使孔生起死回生。孔生可以为娇娜而死,娇娜也视孔生为知己,两人的感情模式早已超出平凡的男女之爱。《香玉》也如出一辙,在香玉不在黄生身边时,绛雪自来“少慰君寂寞”,但又不同于普通的男女之爱,黄生也坦言:“今对良友,益思艳妻。”“良友”之称,即为知己,自和“艳妻”不同。
综观整部《聊斋志异》的“双美故事”,大致脱不了以上几种类型。不论是男子一妻一妾,还是兼有情人,或是得一知己,两个女子总是围绕着男性,男子坐拥“双美”,“‘二美和谐、友好,全心全意让男人享受到嫡庶和美、多子多福的幸福生活。”[4]
二、男性的寂寞幻想
蒲松龄少时才华横溢,19岁就考中了秀才,但之后却屡试不第,终生仕途失意,落魄沉沦,最后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到私塾做教书先生。在蒲松龄的大半生中,他始终寄人篱下,生活贫困。况且,蒲松龄毕生立志求取功名,屡屡挫败,心情郁郁,颇不得志,加之离家在外,生活困顿,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聊斋自志》中,他曾道出自己作《聊斋》的目的,他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志异》中相当多的爱情故事是以“艳遇”为开端的,数量众多的“双美”故事也可以视作蒲松龄的情感诉求和宣泄。蒲松龄长期客居在外,“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聊斋自志》),聊斋故事中,每每描写寂寂长夜,大多忽有不知名的艳女出现,给书生带去欢乐与安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无法在深夜走入书斋,给书生带去欢乐,使书生飞黄腾达。所以,这种美好的幻想只能存在于小说中,只能作为作家浪漫情怀的寄托。
在《聊斋志异》的“双美”故事中,莲香“夜来叩斋”,继而“息烛登床”;红玉初见冯生自称是邻家女,紧接着“与订永好”;《荷花三娘子》里,狐女也是在与人野合之时被宗湘若撞见,然后跟宗生“殢雨尤云”“积有日月”……基本在每段故事里,男主人公都有一段艳遇,且缺乏一定的感情铺垫,女子就对男子不离不弃,或嫁之为妻,或为其另觅佳偶,为男子奉献出一切。故事中的书生在美丽女子的关怀和爱情的滋润下,得到了慰藉与满足。结合蒲松龄自身的身世经历,这些情节恰恰可以视作蒲松龄的寂寞慰藉和排遣。蒲松龄之妻刘氏长期不在蒲松龄身边,蒲松龄又需要养家糊口,夫妻的生活重心定然离不了柴米油盐。然而,蒲松龄本人“雅爱搜神”,“喜人谈鬼”,当面对困窘的生活和平淡的夫妻关系,他只能进行一场浩大的精神漫游聊以自慰,来充实自身的精神世界,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所以他构造了一个个神奇香艳的“双美”世界,书写了多种多样瑰美奇幻的艳遇,造出了虚美幻境来弥补现实世界的残酷枯燥,让“双美”围绕着书生,为其带去诗情画意的爱情,也给自己的困窘平淡找到慰藉。
当然,在“双美”模式中,蒲松龄也透露出另外一层的心理。落魄的书生在现实中、仕途上、男性世界里寻求不到自身的价值和理解,这样的失落与痛苦无处发泄,所以只能寄托于虚幻境界的女性身上。作家希望出现一位美丽的解语花,与自己心心相印、惺惺相惜。《青梅》中,蒲松龄在篇后的“异史氏曰”中一语道破道了心声:“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必以死;曾俨然而冠裳也者,顾弃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青梅本是妾室,而蒲松龄却称其为“夫人”,在俱得“双美”的同时,又将二人比较高下,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对青梅的赞赏与喜爱,并极力提高其地位和评价,这说明作者在兼得“双美”的同时,更看重女性对男性的理解和二者心灵的契合,在男性心中,知己之情和落魄相助更多了一层纯洁神圣的光辉。就如蒲松龄自己所说:“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剩于‘颠倒衣裳矣。”
三、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情欲与家庭观念
蒲松龄生于明末,卒于清初。晚明时期,社会思想及文学思潮都受到“主情浪漫”的影响,然而,清代以来,“经世致用”和“伤感质实”的思潮也逐渐取代了明代躁动狂热的浪漫思潮。但是,即便这样的思想在清初受到了“围剿”,但是却没有完全消失。王夫之是清初的大思想家,他说:“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君子与小人同有之情也。”[5]在他的思想中,仍然要求从自然生理角度来讨论共有的“人情”。在清初“颜李学派”的思想中,颜元也“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对人的欲望加以肯定……李塨则继承了颜元在人性论与伦理观方面的观点……主张情欲的正当合理性。”[6]所以,“肯定个人情欲的愿望和追求美好的爱情仍然是清初部分文人和市民的潜在心态……《聊斋志异》中许多美丽动人爱情故事,正是这种心态的形象反映。”[7]
《聊斋志异》的“双美”故事刻画了众多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蒲松龄在故事中塑造的女子几乎都是将爱情作为自己生活的重心,她们似乎是为了爱情而生的,对于婚姻,她们主动出击,积极追求,可为情死,可为情生。就如作者在《香玉》后所作的评述:“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聊斋女子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情深意重,追求婚姻自主。“双美”故事,乃至整个《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都是如此,对女性形象和女子爱情的刻画,深刻体现了清代主情浪漫的思想,肯定了女性个人情欲的合理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双美”的关系模式是一种光怪陆离的畸形关系,这些美好奇幻的爱情故事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女性对封建礼教与包办婚姻的抗争,并且对女性的情欲以及其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进行了肯定,然而,在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蒲松龄的思想却依然没有冲破性别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他始终是站在男性立场上,以男性的视角来构思故事。而且,他是一个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人,热衷于科举,积极入世,将宗嗣关系看得极其重要。
因此,蒲松龄刻画的男性角色的人生归宿不仅仅限于娶妻纳妾、艳遇美女或得一知己,“双美”故事设置了贤妻、佳妾和睦相处的家庭,几乎每个故事中的“双美”都会尽力维护平衡的家庭关系。《阿霞》中,景生为阿霞休妻,阿霞却说:“负夫人甚于负我!”景生也因休妻而被冥中削禄秩。作者这样写的意图很明确,认为只要破坏了宗法关系,就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当情欲和伦理发生冲突时,最具有思想价值的爱情和情欲仍旧要让位于子嗣绵延和家庭伦理。《阿英》中,阿英虽与甘钰情深意笃,但苦于无嗣而替丈夫另纳姜氏。
由此可知,虽然《聊斋志异》肯定了女子的情欲,肯定了其对爱情的追求,但是,其对女性情欲的肯定仍旧是在男子视角之下的,是在维护宗法和家庭基础之上的,对于爱情和情欲的追求不能破坏家庭的完整,不能影响家族的绵延,不能违背宗法伦常。在《聊斋志异》的“双美”故事中,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种欲望爱情、子嗣家庭二者兼得的心态,这种心态恰恰是在男性视角和男性主导的文学话语下诞生的。
注释: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关于《聊斋志异》引文皆引自该书,不一一注明出处)
[3]曾丽容:《同枝异花,各擅其妙——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情结》,《聊斋志异》研究,2013年,第2期。
[4]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5][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
[6]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许嘉璐等.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三册)[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杨麟舒 陕西安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