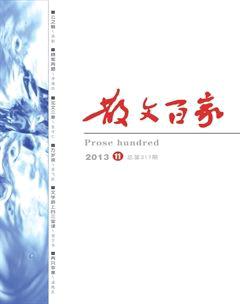水月(五题)
蒋静波
水月
家乡河道纵横,出门皆水。根植于心的,是水边的月亮。
家门口弯弯曲曲的小河边,连绵着一大片芦苇。傍晚,天尚亮,月亮已经出来了,像是怕羞,总要在河对岸的芦苇丛中躲上一会,才一跃而出,静静地停在苇尖上,仿若用苇叶系着一只银白色的氢气球,伸手可及。
夜色渐浓,月亮渐高,在河的上空盘桓。孩子们早上了岸,吃了饭,来到河边,却不敢下水,怕大人口中力大无边的“河水鬼”披着长毛、瞪着绿眼将人拖去,只好趁着朦胧月色,以贝壳当杯、以水当酒、以瓦当碗、以草当菜,在岸边办家家。
“砰砰砰”,月下的捣衣声,拖着长长的回音,从这个埠头传到那个埠头。“哗啦啦”,衣服在水中上下翻飞,河水漾起了波纹。月亮颤了颤,颤成了一粒粒碎银,一条条银簪。
水上划来一只小船,“咿呀”泊在埠头边。男人跳上岸,见四下无人,弯腰,扮鬼脸,百般哄劝,女人才忸怩下船。男人抓住女人的手,朝自己的脸“啪”地一巴掌。女人掩嘴一笑,踏着清辉,和他回家。
那一夜,白天劳作互不搭理的姑娘小伙,依在桥边,轻咬耳朵,指月盟誓。姑娘随手折枝芦苇,编个同心结,编只凤凰于飞,插在小伙的衣袋。后来,父母棒打鸳鸯,姑娘含恨投水自尽。月亮照着姑娘惨白的脸,照着悔恨无边的亲人。
月光之下,水边,白亮亮的一片。是谁,临水而伫,捧着书,似看非看;是谁,在河畔拉起《二泉映月》,满腹心事诉与明月;是谁,在桥头那边,仰头轻哼“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重温少年的情怀;是谁,在河边的地里,牵着老牛,还在耕田,“哞——”的一声,穿破了月空,犁开了夜幕。
宁静的水月,永挂在记忆的夜空。
夏夜
太阳下山了,泼几桶水,河边过来的风便把夜幕吹开。
阊门的道地苏醒了。桌、椅、凳,次第登场。人们或坐、或躺、或靠,随意,自在。上风处,焚一把艾草或臭蒿,熏得蚊子四处乱飞。“啪”的一声,女人将巴掌重重落在男人的背上,骂一声“该死的”,倒不知是骂蚊子还是人。
天空铺了层宝蓝色的丝绒,缀着数不清的星星,粉的、紫的、白的、蓝的,五彩缤纷,闪烁不停。这头,婆婆叫小孩猜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铜钉。”那边,奶奶复述着牛郞织女和嫦娥后羿的天话。
奶奶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当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奶奶念叨着,地上的一个好人上天堂了。真的代表地上的一个人吗?我是哪一颗?我的家人是哪几颗?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吗?银河两岸真的有牛郎织女吗?……望着星星,我的脑海满是疑惑。
萤火虫提着一闪一闪的小灯笼,随风曼舞。小脚婆婆念着“火萤团,团团,人家门口摆金团”。我翻出透明的玻璃药瓶,窜到墙门外的草丛边,见到光点,捉住,塞进药瓶。药瓶也成了“灯笼”。不知萤火虫是否明白,为何她炫目的亮点竟成了自身致命的弱点?
男人们摸着被蚂蝗叮得红肿的小腿,谈论着国家大事,激动处,唾沫横飞,挥斥方遒。女人们摇着蒲扇,说收成,道家常,不时呼一声孩子。老人们成了孩子王,将收藏几十年的鬼怪、精灵的故事,豆子般倒了出来。孩子们听时兴致盎然,听后毛发倒竖,草木皆兵。借一片月光,妈妈用风仙花,染着我的指甲。
偶尔,来了兴致,父亲吹起口琴、拉起二胡,大胆的姑姑或大姐姐咿咿呀呀唱起了歌,人们的喝彩,时重时轻。阿叔捧来了刚摘的西瓜,拳头轻击,豁然四裂;阿婆端来一甑刚结的木莲冻,任人自取。
东房的小叔,吹一声口哨,朝小河走去。身边的小姑,一甩长辫,也不见了踪影。夏夜,开始了另一个故事。
“喵”,一只野猫蹿上屋顶,众狗轻吠。夏虫的合奏,时断时续。不知何时,孩子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爬满墙头的喇叭花,张着嘴,不说一句话。
弄堂
在老家出门几步,便要穿行弄堂。始终数不清家乡有多少条弄堂。只知道,二间三间房子,或者一间和一块空地,也能夹成一条短弄堂。
弄堂不宽,青石板地,泛着光泽,淡淡的,似陈年的故事。
在这里,蹒跚的孩子,学会了走路,奔跑;年幼的孩子,骑在弄堂的石槛上,咬手指,流口水,羡慕着大孩子的游戏。我们用单腿,跳过一条条弄堂的石槛,跳得鸡飞狗跳;我们摔泥炮仗、翻跟斗、飞三角,废寝忘食;我们穿线绷,一条线在十指间穿来绕去,穿出喇叭、五角星、铁塔,穿得两眼放光。当大人们将山上斫来的柴、田畈挑来的菜籽秆、稻草码在弄堂内,弄堂里会飘出好闻的清香。我们捉迷藏,寻野果,摘树叶,游戏花样总是层出不穷。
“嘭咚、嘭咚”——货郎客人摇着拨浪鼓,挑担进了弄堂。女人们翻出牙膏壳子、鸡毛鸭毛、烂铁皮,换些针头线脑、玻璃丝带,孩子们兑几片麦芽糖、几粒玻璃珠子。弄堂里,一片欢乐。
端淘米篮的,遇上挎割草篮的,在弄堂里扯开了长长的话题;夫妻有理说不清,女的跨出家门,跳到弄堂,嚷着叫邻舍评理;吃饭辰光,弄堂里回响着母亲声声焦急的呼唤。
弄堂有明暗,两边都是房子的,便暗;一边是空地的,则亮。大人们喜欢亮弄堂。弄堂亮,家才亮。我家处在暗弄堂,前半间,白天也要点灯。亲友上门,父母叮嘱又长叹“走好,唉,这个暗弄堂”,满怀着歉意。
夏日的暗弄堂自有妙处。午后,父亲斜躺在弄堂的长竹椅里,边喝茶,边听收音机,或借着微光看书。我和妹妹躺在其后的草席上,挤眉弄眼。一阵清风,穿弄而来,舒坦了我们每个毛孔。“卖棒冰来——”,那沙哑的吆喝声总会适时响起,我们变着法儿,从大人手中接过钱,飞窜般买支白糖棒冰,闭起眼,慢慢地舔,舔到只剩一根小木棒。
奶奶堂屋门口,是亮弄堂。大人们空了,喜欢席地而坐,或依柱而立,讲着山海经。一张方桌,半张在弄堂里,半张在堂屋内,我做着作业或随意翻书。屋梁上的小燕子,张开稚嫩的小黄嘴,叫个不停。偶有一只蝴蝶,飞来停在我的花裙上。抬头,弄堂口的午时花,灼灼地开。我的妹妹,正从对面的弄堂里,向我挤眉招手。
邻家的姐姐,穿着红嫁衣,在鞭炮声中,正要迈过弄堂石槛,突然转身下跪。弄堂中的父母,倚着木壁,泪流满面。此时,我正背着行囊,穿过另一条弄堂,到异乡求学。秋风将青灰的弄堂,和我奶奶孤单的身影,剪成一帧画。
炊烟
总是踩着晨昏午间的时点,于粉墙黛瓦上,升起缕缕炊烟,向着蓝天白云,升高,飘去。无风时,它不急不躁,对着小桥流水,向着广袤田野,转身,回眸,将身影拉得纤长;清风徐来,它纱裙飘逸,一飞三折,于若有若无间,融入天空,寻找它的天堂。
田间劳顿的男人,抬头,看见家里炊烟升起,如听见了无声的呼唤。扛起锄头,走过田塍,在水渠小河边洗洗,回家。眯着眼想,桌上,必端上了热腾腾的菜了吧;杯里,必斟上了香醇的酒了吧。野外玩耍的孩子,见了炊烟,收起野性,向家飞奔。顺手拣几只田螺,采几个蘑菇。咧着嘴笑,炊烟下的妈妈,会夸我懂事了吧,或是递给我一根煨年糕?
奶奶的话,伴着锅里大米的清香,始终萦绕在炊烟中。懵懂的我,记住了爱惜粮食、勤俭持家是做人的本分。大人们出去了,孩子们闲得无聊,点了柴火,将铁锅烧得嘞嘞响。掀开锅盖,一锅金黄色的锅巴,香气扑鼻。在外的母亲,见了炊烟,一笑而过,从不点破。
炊烟喜欢热闹。最先冒出的那一缕,是一种信号,继而阵容壮大,不久,家家户户的屋顶都飘起炊烟,如天上的仙雾。整个村子笼上了神秘的色彩。若是谁家的烟囱仍无动于衷,有人会细问端详。
午后,谁家冒出了炊烟,一丝,一缕?邻舍循烟而来,寻到琴姑娘家。女主人正将一碗长面蛋递与一个陌生小伙,琴姑娘含羞陪坐。琴姑娘相亲了!消息在炊烟中弥漫整个村庄。
邻舍
下雨了,谁将我外晒的物什收起?来客了,谁替我端水递茶奉点心?生病了,谁向我嘘寒问暖送真情……邻舍,是洒落心田的一抹暖意。
有时候,邻舍是母亲,温馨而细碎;有时候,邻舍是父亲,有责任,敢担当;有时候,邻舍是朋友,能信任,可托付。
碗是流动的温情。左邻刚盛来烤毛豆,右舍也端来了红烧泥鳅,乐得我大快朵颐。为易于辨认,许多人家碗底号了字,或号上花草鱼虫。有时,不知是谁端来了一碗菜,看碗底字号,便可明了。若没号的,洗了放在碗橱,有人会打开门擎,悄悄取回。
奶奶在镇上饮食店上班时,每逢邻舍凑到柜台寻她,总是格外照顾,不是多放一只馄饨,就是重煎一根油条,或是买只大饼相送。回家时,篮子是意外的惊喜:你一方豆腐,我一包菜籽,她几尺蓝布,他一斤黄糖……再清贫的日子,也能漾起欢乐的水花。
欺侮人,最好问一声邻舍是否答应。那一年,外村恶亲纠集几人,手持竹棍,以为西屋叔叔人单势薄,前来挑衅。谁知东屋伯伯一声吼,吓得恶亲落荒而逃。若是有人遇上难事,众邻舍便是纾难的及时雨。
邻舍间是藏不住秘密的。收成好坏、人缘紧疏、家庭关系、四亲八眷,邻舍心里自有明灯一盏。难怪处对象的,千方百计挽人探听邻舍的口风。邻舍在说好话时,若有些许迟疑,或皱下眉,这门亲事准黄。
邻舍的孩子,青梅竹马间,渐次长大。在野外,挑野菜、抓田鸡、烧灰篷;阊门里,跳皮筋、爬乌龟、捉迷藏。悄悄演戏,你扮落难书生,我扮千金小姐,她扮机灵丫鬟;偷偷看禁书,抄歌词,分享心中的秘密。你知我的底细,我懂你的心事。将时光度得有声有色。
那一个雪夜,邻家大哥哥娶来了美丽的新娘,不知为何,突觉失意。待到来年,抱着他俩的宝宝,却欢喜着教宝宝喊姐姐。
老家渐远,亲爱的邻舍消散在时光里,铭记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