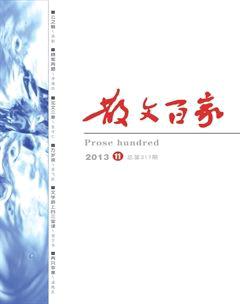山间书香(外一篇)
陈荣力
位于四明山西北麓、环浙东第一大湖四明湖畔的余姚梁弄镇,是后唐时即“人烟凑集”的浙江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抗战时期有“浙东延安”之称的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心脏。虽栖居于大山一隅,这些年来,梁弄正以自己的湖光山色之美、人文故迹之胜和红色遗址之灿,吸引着越来越多寻访探游的脚步。然而与许多去梁弄的游客一样,数次到梁弄,我却一直无缘踏入梁弄学弄路上“五桂楼”的大门。
史料记载,坐落于梁弄学弄路上的“五桂楼”,由性喜藏书、一生笃志力学的梁弄乡绅黄澄量(号石泉),为收藏其五万余卷的积书,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出资建造。之所以取名为“五桂楼”,乃是黄氏仰慕其北宋时同中进士、同朝为官的先祖黄必腾五兄弟,取宋高宗赠其“五子还乡”的诗中“仙藉桂枝香”之句得名。黄澄量出资不菲建造“五桂楼”,出发点是为了收藏尽一生之力搜集的五万余卷的图书,但其根本的目的更在于嘉惠后人。“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为确保其藏书的不致失散,黄澄量还留下了“黄氏经籍,子孙是教,鬻与假人,即为不孝”的训诫。继承父亲的志向,黄澄量的儿子黄肇震亦致力于收集图书,使“五桂楼”的藏书增加到六万余卷。太平军进浙东,“五桂楼”的藏书有所散佚,黄澄量的孙子黄联镖、曾孙黄安澜经过多年搜罗,且添买善本,至同治年间,终使“五桂楼”的藏书又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也正是凭了黄氏一家四代的坚守和努力,“五桂楼”——这个地处浙东山区古镇的私家藏书楼,其藏书之丰竟有“富甲越中”之誉,并被称为仅次于宁波天一阁的“浙东第二藏书楼”。
终于闻得荡漾于山间的那一脉浓郁的书香,得益于一位余姚友人的陪同和引领。“其实外地人知道梁弄还有‘五桂楼的并不多,要想专门去看‘五桂楼的更少了”,友人的话语里,颇有些“珠藏深山惜未识”的感慨。而在我,倒更像热油上滴入的一滴水,让一睹“五桂楼”的欲望,变得愈加嗤响骚动起来。
踏上与下街洞门弄毗连的学弄路,一幢四周被三米多高院墙围着的建筑,于一片江南的民居中,卓然鹤立。推开东侧院墙的大门,半亩大的庭院内,是三间坐南朝北的晚清木结构二层楼屋。清代书法家胡芹所题的“五桂楼”的匾额高悬其上,同时悬挂的还有一方“七十二峰草堂”的匾额。友人看出了我的迟疑,介绍说,“五桂楼”当年是梁弄最高的建筑,登“五桂楼”远眺,则可见四周山峦起伏、四明山七十二峰连绵环抱,故“五桂楼”又名“七十二峰草堂”。“七十二峰草堂”的题书,出自同样是晚清书家的吕屐山之手,其虬劲、华茂的笔划,与“五桂楼”的精致、端庄相得益彰。
“五桂楼”一百三十多平方的建筑面积,其体量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大。但仔细察看,众多为藏书而设计的独特之处,让人叹为观之。如“五桂楼”十来米的建筑高度,比一般的二层楼屋明显高出一截。究其原因,乃“五桂楼”的屋顶呈“众”字型,明看二层,实为三层,顶上的暗阁,平时用来隔热防漏,利于书籍的保管,凡遇战乱,暗阁则多藏善本。暗阁中至今仍保留着一根记有当时建楼时各种尺寸数据和梁架构件符号的竹竿——“柱百竿”,相当于现代的建筑图纸,以便于后人的修缮。与暗阁异曲同工的是东西两边山墙上十堵梯度收缩升高的风火墙,既能挡风防火,又是个性鲜明的装饰,更与院墙连成一体,较好地弥补了高院墙带来的沉闷和压抑。或许是主人建造时的精致和讲究,或许是后人养护维修的得法,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五桂楼”的墙、柱、门、窗、桁梁、构件、基石、瓦档依然保持着昔日的周正与倜傥。而镶嵌、装饰于建筑上下、腰间、柱子、门窗上的木镂护栏、雕花窗板、卷蓬顶饰以及卵石庭院、花坛中“八骏图”、“麒麟送子图”等石雕、浮雕,更让一幢精致、端庄的“五桂楼”,在二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散发着华滋、雅儒的书香。
与建筑相对应的自然是“五桂楼”的珍贵而丰富的藏书了。“五桂楼”楼下为客厅和讲学会友之所,所藏之书皆置楼上二十几个高大的木制书橱。《光绪余姚县志》曾这样记载“五桂楼”的藏书:“举凡鹿洞谈经之作,龙门经世之文,漆园藏室之言,唐勒景差之制,以至九章算术,五垒兵图,星宫风角之渊微,王相握奇之阴奥,三乘秘藏,衍香象于元宗,九仑仙经,刊飞龟于丹帙,网罗略备,囊手无遗。”黄澄量的玄孙黄安澜所刊 《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统计,“五桂楼”藏书计一千五百多部六万余卷,3666种,其中经部475种、史部416种、子部504种、集部430种、丛书1820种。这些藏书以清代刻本为基数,又颇多宋、元、明代的善本,其价值之珍贵,不说连城,怕也是金钱所难以计算的。“四明山上云汉章,五桂楼前经籍光。闻道宗衮昔建此,罗网欲过千顷堂”,当年闻“五桂楼”之名远道而来的文人所留下的诗句,不仅道出了“五桂楼”的声名和影响,一句“罗网欲过千顷堂”更让我们依稀触摸到了在那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年代又地处浙东大山一隅的黄氏一家四代为此所付出的斑斑心血、所遭遇的种种艰辛。“五桂楼”的藏书除解放初浙江省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调去大部外,现尚有古籍近万册,其中善本19部625册。
难能可贵是,除了毕生藏书,黄澄量还有比较开放的藏书观念。“积财与子孙,不如楹书与子孙”。他不仅自己“得一书,添一目,读一书”,也要子孙同样登楼展视楹书,以训淑德性,扩大见闻,增长识力。或许这样的“登楼展视楹书”,正是黄氏一家四代坚守于藏书、搜书,终使“五桂楼”“富甲越中”的精神滋养。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黄澄量还大胆地打破一般藏书家不让外人阅读的陋习,凡“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只要不借,恣其阅览,且供食宿。因了一幢“五桂楼”,地处浙东山乡的梁弄,竟吸引了众多文人学士跋山涉水竞相前来。而黄澄量的这种观念和行为,事实上也让自己在无意中成为构建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雏形的破冰者。
“在文化的苍茫浩淼前,人不过是棋子;这庭院的地这庭院的天,就是历史和时间对弈的棋盘。”站在“五桂楼”桂枝摇曳的庭院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英年早逝的湖湘诗人江堤的这句话。如果说卓然鹤立于浙东山区古镇的“五桂楼”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化奇迹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奇迹面前,我们确实不过是棋子,甚至连黄澄量也是一枚棋子。只不过他的这枚棋子,饱蘸了四明山乃至整个浙东文化和山水的渊薮,由浓浓的书香结晶而成。
老楼如雪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日子,等待着一个下雪的日子。只有当这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我才可以伴着窗外飘落无声的雪花,思念关于老楼的一些故事;我才可以蘸着露台上渐堆渐厚的积雪,写下关于老楼的一些文字。不是我的怪异,也不是我的固执,每当念及老楼,每当欲写老楼的文字,我的思绪总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飘忽不定,什么都转瞬即逝。我知道只有当雪花无声飘落的时候,老楼和关于老楼的一些故事,才会像洗影的底片在记忆中渐渐定格、清晰;只有当积雪渐堆渐厚的时候,老楼和关于老楼的一些文字,才会像入水的鱼儿在电脑上慢慢游动鲜活。
其实,老楼于我冥冥之中就是一种渊薮。
早在二十年前,我便有机会成为老楼里栖息的一分子的。那时的老楼人声鼎沸车马稠,是主流也是强势,入驻老楼更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但因一个偶然的因素,我最终与老楼失之交臂。此后十多年,每当走过老楼,我总想我这一生恐怕永远不会有机会走进老楼了。然而世事乖张,六年前当入驻老楼几近失落和失败的代名词时,我却走进了车马冷落人声稀的老楼,成了已成边缘和弱势的老楼里的一分子。
就像许多过时的风景一样,栖息于老楼里的日子,更多是清冷和寂寞的;而发生在老楼里的故事,也多少带有点春雪的苍白和无奈。记得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刚到老楼,兀然发现楼梯口立着一个憔悴的中年汉子。起初,我和他都有点愣怔,及至回过神来,我们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作为高中时坐过两年的同桌,二十多年后的初次重逢,我们彼此的欢欣里已不免岁月沧桑的感慨。老同学有点慌惶,忐忑了一阵终于说出了来找我的原因。原来是儿子中考差了几分,需拿出几万元的助学费,而长期务农的他家境一直窘迫,于是无奈之际来找我这个当年关系最铁的同桌帮他托个人情减免一点助学费。我想了想,操起电话找了我认为有能力帮也肯帮的几个人,然而电话中的回答不是干脆拒绝就是婉言搪塞。当老同学一脸怏怏地走出老楼的时候,我才蓦然醒悟:当我走进老楼的那一刻起,我其实已不具备打这种电话的话语和资格了。而不久后的一次饭局,当我偶尔得知一位朋友的儿子恰恰是靠了我打过电话的其中一位的帮忙减了将近一半的助学费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境竟出奇的平静。
又一个下雨的傍晚,一位昔日很谈得来的异性朋友,匆匆出现在老楼。对这样的突然造访,我就像看见陌生的亲戚一样不免诧异,因为自搬进老楼时来看过我一两次外,整整一年多了,她再也没有走进过老楼。她说她是到附近办事时顺便来看看我的。十来分钟的面面相对,我们竟都尴尬得无话可说。外面的雨依然很大,她却起身向楼下走去,及至脚步声在楼梯消失,我才发现她的伞忘了。匆匆追下楼去,正好碰上返回取伞的她,密匝的雨幕中,她慢慢地撑开伞,淡淡地说了一句:“以后我怕再也不会来了。”
如果说人生的各个时段如一幕幕独立的戏剧,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栖息场所——或华屋旧宅或老楼新宇,无疑就是上演这些戏剧的舞台。舞台变了,上演的内容和角色理所当然也要改变,这原是颇正常也挺符合与时俱进规则的。所以,尽管老楼里的日子更多是清冷和寂寞的,老楼里的故事也多少有点苍白和无奈,但扪心自问,我对此从未悲凉、怨怼过。包括对打过电话的那些人和那位真的再也没有来过老楼的异性朋友,我始终怀着将心比心的认可和理解。我常想,如果不是走进老楼,我或许很难有这样的认可和理解,至少在我这个年龄段还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十分感激老楼。
老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仿苏建筑,骨子虽有点马虎,但容貌不乏那个年代的文化元素。无数次从老楼里进进出出,我甚至想,再过几十年,老楼作为一处文保建筑也未免不可能吧。但老楼说拆就要拆了,原因当然不是老楼已成危房,而是拆了要建二十几层高的真正的高楼。清楚地记得搬出老楼的那天,正好下着春雪。漫天飘扬的雪花将我匆忙的脚步打得湿漉漉的,而屋瓦上、天井里积雪的反光更让暗淡的老楼显出一片格格不入的惨白。站在行将消失的老楼前,我的眼前依稀浮现出那些隔三差五来老楼里走走、看看的人。他们大都已脸似橘、鬓如霜,有的甚至已话语迟钝、步履蹒跚,但他们抚摸老楼的目光无一不灼灼如火。这样的目光常使我唏嘘,更让我感奋难忘。
农谚曰:“冬雪是宝,春雪是草”。对一个到处都生长着塔吊、脚手架等现代植物的城市来说,老楼的历史、记忆、故事等怕早已被许多人视作无用的春雪了,拆掉老楼也况如拔掉一根草那样的轻巧和天经地义。而在那些期望着在塔吊、脚手架等现代植物的缝隙里还能找到几许历史根蔓和记忆枝叶的人看来,老楼哪怕真的况如春雪,那样的雪也分明闪烁着岁月黑炭燃烧成灰的辉光,散射出青春蜡烛奉献为泪的晶莹。
其实在老楼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是沉静而快乐的。正如一位常来老楼的文友所言:“你在老楼的日子就像积雪融化后滋润的草,虽不起眼,但绿得平凡,绿得自由舒畅。”
———评郭庆财博士《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