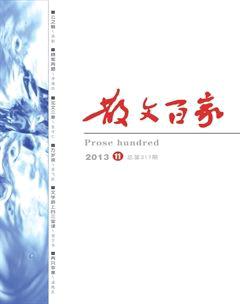稻子上的乡村时光
李天斌
我总会梦见一株稻子:它就长在乡村的怀抱里,头顶是斑斓的星空,四周蛙声如鼓,一条汩汩的小河在身边不知今夕何夕地流淌;泥土和风不断亲吻它的肌肤,就像情人之间的爱抚,亦像一份地老天荒的相守。
很多个夜晚,我都会跟着父亲,枕着这样的一株稻子入眠。夜是寂静的,寂静得我能听到天籁般的窃窃私语——石头、野草、虫子它们,就像一些精灵,不断从地底下探出头来,温柔地对着稻子低语。我天真地想,作为一株稻子,它是幸福的。一株稻子,近似众生眷顾的神祇。
在这样的梦境里,我恍惚也是一株稻子了;至少,我觉得在我的身体里,有一株稻子,正在那里生长拔节。
一株稻子,当它从泥土中探出头来,我们的牵挂,就在那里放着了。
几乎每天,我们都要朝着一株稻子跑:看看稻子是不是又长高了;田水是深了或是浅了;太阳和风雨,是跟稻子亲近或变脸了?我们总怕稻子们遭受任何委屈,每天都要跑上很多次,比起热恋中的男女,我们对一株稻子的难舍,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候,一株稻子,它所牵动的,是一个乡村的所有神经。
所有的村人,每天都在围着一株稻子转,直到稻花香了又香,那转圈的人仍然乐此不疲。只是他们并不会觉察,转着转着就有人老了,时光也悄没声息地走远了。一株稻子,它所见证的,是生命与时光相互消耗的过程。
在这样的消耗中,我一不小心也跟着长成了大人;并一次又一次目送很多人随稻子而逝,其中就有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从一株稻子的身旁转过去,就不见了。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一株株稻子,年复一年地长在乡村的土地上。
一个人呱呱落地了,稻香就通过母乳,进入他或她的身体。仿佛在前世,一缕稻香就在那里等着他或她了。继而,他或她开始稻里来,稻里去。到最后,他或她自己也长成了一株稻子,恍惚之间,竟然分不清是稻子住进了自己的身体,还是自己住进了稻子的身体。
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在乡村,每个人的前生都是一株稻子;每一株稻子的前生,也都是我们自己。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你不将自己视为一株稻子,如果你不能在一株稻子上安身立命,你就一定会遭到人们的鄙视。村人们都会骂你不务正业,说你败家子。譬如那些游手好闲的,譬如那些偷鸡摸狗的,因为无法安心于一株稻子之上,所以往往名列其中。
这样的人,到最后还会被乡村所抛弃。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中,因为姑娘们觉得不可靠,所以总有娶不到妻子的,他们先是满不在乎,到最后就慌了神、就后悔,但终于无可挽回了;偶尔有娶妻的,也因为对一株稻子的认识的分歧,夫妻间不断地争吵,到打架,一直到离异……
到此,一株稻子在乡村的位置,越发显得不可替代了。
我的父亲就不止一次指着一株稻子训诫我。在父亲心中,一株稻子的生活,就是我一生的生活。从下种、插秧,一直到收割,每一个程序,父亲都忘不了要带上我,他不能让我做一个不懂得稻子的人。
从布谷开始啼鸣的春季,一直到金黄布满田野的秋日,几乎每个早晨,我都会被父亲催促着从床上一骨碌爬下来,有时来不及洗脸,带上必要的农具就往田里跑,我也曾因此对父亲怀着深深的不满。但多年后才发现,父亲之所以逮着我不放,其实正是缘于对我的担心,他怕我不小心成了被乡村抛弃的人。
不独父亲如此,几乎所有的乡村父亲,都怀着这样一份担心。
在一份担心下,你往往就会看到,一个孩子,当他刚刚长到犁耙一样高,父亲们就迫不及待地指导他学习耕种了。如果那孩子一开始就学得像模像样,做父亲的就会喜笑颜开,一逢人就夸奖孩子,除了自豪外,还有几分显摆的味道;反之,如果孩子学得不好,做父亲的脸上便免不了愁云遍布,越看孩子越觉得没劲,有的甚至还会叹息,总觉得养了个没出息的娃……
一株稻子上的梦,从一开始,就紧紧地系着一个乡村的阴晴圆缺。
在乡村,作为一个懂得稻子的人,是倍受尊崇的。
譬如什么时候下种最好,什么样的泥需要什么样的肥,泥土要翻到什么深度最为适合,什么深度的水最适合稻子生长,什么颜色的稻子一定是患了什么病等等。如果你能说出这些,在乡村,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
这样的人在乡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必定要请他出面主持。譬如老人过世了,新房落成了,儿子娶媳妇了,女儿嫁人了,甚至是谁家婆媳吵架了,邻里之间扯皮了,都必定要请他出面——在村人们看来,一个懂得稻子的人,也一定是懂得人间道理的,更是值得信服的。
一株稻子,延伸到生活中,就成了乡村某种精神的写照。
很多年,父亲总是以这样的人作榜样来教育我,希望我长大后也能跟他们一样了不起。我也曾为之努力过,尤其是,在星空斑斓的每一个夜晚,当我跟着父亲枕着一株稻子入梦时,还梦到过自己就是端居其上的王……只可惜我终于让父亲失望了,一直多年,尽管我也曾为之作过努力,但我始终没能成为村人尊崇的对象。在一株稻子之上,我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
入夏了,一株稻子就在乡村的田野里风情摇曳起来。
此时,太阳一天比一天更催人了,加之几阵风后,一株株稻子,就迅速长高起来。父亲说,这时候只要你留心,就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音;父亲还说,稻子的声音是夏季里最动听的音乐,能听到这歌声的人,一定是有福气的庄稼人。为着这句话,很多年我都觉得诧异:父亲只是一个朴实的庄稼人,却能将一株稻子赋予诗意,这算不算一种奇异的风景呢?
风吹来,层层翻卷的稻浪,以及铺天盖地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一层柔柔的水流漫过身体,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一份滋润,似乎春雨润物,细腻而晶莹;似乎有一层绒绒的光,在那里充盈、扩散,再充盈、再扩散……
每一次从稻田边走过,我都会为之心生喜悦。有时候,我还会学着父亲蹲下来,一遍遍抚摸每一株稻子——那时候,我是多么地想做一个有福气的庄稼人呵,但每一次,我都没能听到父亲所说的声音!在渴望走近一株稻子的路上,我是否曾因为这一距离而心生失落呢?不知道。
一个确切的答案是:我就此记住了一株株夏日里的稻子,它们铺满了乡村的田野,绿色从每一个角落争先恐后涌出来,风景般装饰了每一双眼睛。每个人,都喜欢与之对视。每一块稻田旁边,都会有一个父亲或是孩子的身影晃动。每一株稻子都迎接过亲切的目光,每一株稻子都是热闹的。每一株稻子更是神秘的。很多年我总是在想,一株稻子,当它在夏日里风情摇曳时,是不是就告诉了我们什么?
究竟告诉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很多年我都没有想明白。
在乡村,一株稻子,貌似简单,却是最难解读的时光与事物。
也是在夏天,当太阳一日烈过一日,稻田里的水就一点点干枯了,就连河流里的水,也逐渐消失,仅剩下细细的浅浅的一层,宛如细若游丝的气息。为了及时给稻子补充水分,为了抢夺有限的水源,村人之间的争执,不可避免就发生了,有的甚至还发生了打斗。原本和睦亲近的关系,因为一株稻子而发生了改变。
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童年的河滩,那个被太阳晒得无比干涸并紧张无比的河滩。那时候,我正望着我家某块被晒得焦黄的稻子无所适从,突然就听到了河滩上因为争水打架的消息。我跑到那里时,打架的姓王的两兄弟已经头破血流,双双倒在河滩上,痛苦地呻吟不止;两兄弟的子女也互相撕扯着,骂声、哭声不绝于耳;村人们穿梭其间忙着劝架,就像一群纷乱的鸟群……而尤其让我无法释怀的是,经此后,两兄弟成了路人,一直到他们死去,一直到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和解。一株稻子引发的仇恨,竟然如此固执,如此经久不息。
还有我的堂三叔,也是在某个夏日,独自到某个深洞里抽水给稻子补充水分,结果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把他从深洞里捞出来时,他白发苍苍的母亲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抽打他的耳光。她在风中不断摇晃的颤巍巍的身子,她那一份撕心裂肺的疼痛,一直让我难忘。还有一个在村里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某年某个秋月,村里的伍大爷爷用火药枪打死了某个偷窃他家稻谷的人,却不料此人竟然是他亲哥哥……还说此后,伍大爷爷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再后来就疯了;每到夜晚,疯了的伍大爷爷总要跑到某块稻田边哭泣——一直多年,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梦魇,总会在不经意间将我击中,让我沉重,让我思索……
让我不止一次想:作为一株稻子,在乡村那些生生死死的情愫里,它究竟隐喻了什么?
现在的乡村,一株稻子,却已归于平静,并还有些落寞了。
从春到秋,偌大的田野,你几乎看不到稻子的身影。一方面,村人们都外出打工了,一株株曾经让他们活命的稻子,现在已无法养活一家人,于是只好放弃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工厂见缝插针地挤进来,于是众多的水田被征拨,即使那些依然对稻子一往情深的、想要年复一年种下稻子的,也只能叹息一声,算是对稻子的告别了。
到此,一株稻子就像美人迟暮,逐渐沦陷下去,似乎就要走到尽头了;一个乡村的时光,也像年华不再的岁月,越走越窄了。
具体到我的父亲,他也无力再种下很多稻子了。他逐渐苍老的身体,已无法像往昔一样承载一株稻子的重量。但他每年都坚持要种下一些,每年我也都要回村去,跟着父亲在多年前的水田里一起插秧,一起看望水田,一起收割稻子。只是那情景,早已不像最初的那般温馨与诗意了。最初美丽的梦境——那些如鼓的蛙声,石头、野草、虫子的低语,早已不复存在。只是父亲不会知道,当我在一片撂荒的田野里看见父亲种下的那些少数的绿色,就会涌起无限的荒凉——我始终觉得父亲就像一个最后的留守者,在一株稻子走远的背影里,我看见的,似乎是那最后的时光……
不过,我还是会陪着父亲,因为我深知,在父亲心里,一株稻子,它不单是一株可以活命的草木,更是一株传世的粮食;一株稻子,在他而言,正如我心目中最初的神祇。所以,我一定会陪着父亲,直到他彻底老去;直到一株稻子彻底消失在乡村的视野之外;直到整个乡村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