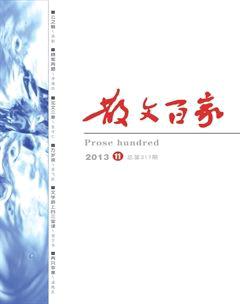敬畏神秘(外一章)
张大勇
神秘是旅行者远方的召唤,神秘是阅读者敏慧的邂逅。喜爱旅行和阅读的我,对神秘一直葆有无限的趋向性和敬重心。我所谓的“神秘”,自然是形而上的划属。
神秘与地球同在。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迷”,表达的是一种敬畏与敬重。但在启蒙运动的前夜,自然、天文的,时间、空间的,一些未知无不戴上“神秘”的面具。无知者有畏,加上被无良之徒的利用,于是就有了诡秘,就有了迷信。民间的“跳大神”、“大师”的巫术,几多朝代的“天子”也不能幸免。更为可笑和可叹的是,在吾国,在科学推开天窗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神秘”全部交由迷信托管,是非颠倒,人妖不分,于是灾难降临,国运蹉跎。让盲目崇拜抽薪扬汤,让领袖走下神坛,是苏醒后国人的共识。对“迷信控”之类“神秘”,鄙人也是深恶痛绝。为“去神秘化”之正行,额手称庆,拊掌叫好。
早在八十余年前,民国大师钱玄同,就对同乡、同学的鲁迅“画”过像,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他笔下的鲁迅,轮廓不乏清晰,光彩不乏照人,但其身上无法回避的“三道疤痕”也是触目惊心:多疑,轻信,迁怒。只是一直以来,仍有国人不愿意承认钱玄同所认识的鲁迅,他们只愿以耀眼的光华,遮掩去鲁迅身上的疤痕。这种“神秘”,无疑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美化与神化。
而真正意义上的神秘,是圣洁的,它既与物质联姻,又与精神恋爱。但它决不是带有目的性的诡秘,也不是带有多解或无解性的玄奥,更不是盲从性或荒谬性的迷信。它可以是模糊,但不会糊涂;可以是美化,但不被媚化;可以是神话,但不被神化。它可以是鬼谷子,但绝不是张悟本;它可以是易经,但绝不是马航。
大自然是神秘的。气象学家洛伦兹的“蝴蝶效应”,埃及金字塔的前世今生。自然界的神秘还有马里亚纳海沟、百慕大三角洲,还有于宇宙之外的存在。我们正握着科学之匙,为自己、为后人打开一道道神奇与魅力之门。但自然界的有些神秘是解剖学等学科无法穷尽它最后和全部的魅力的,它必须交给漫长的时间。
人的器官也是神秘的。诗人孙昕晨在随笔《回家》中说:“童年的胃是一个人最初的记事簿,而味觉之门是有密码的。”这是舌尖上的“神秘”。味觉之门用神秘之手推开:舌头上的味觉太敏感,太神奇,小小一匙之地,不同部位各有分工:舌尖最容易感觉甜味,舌缘两侧前部最容易感觉酸味,舌根最容易感觉苦味。有意思吧。也正是味觉的神秘,才有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一红再红。
神秘附着于人文、附着于精神,我以为不可以藉助科学将圣洁的、有着正能量的神秘全部撕碎给人看。我们应当像尊重宗教信仰一样,让一些美好的神秘锁在深闺里,埋在心底里。托尔斯泰说得好——“天国不在外面,但在我们心中”。只是,只是时间的快马不曾懈怠,后工业化的贪欲仍是急鞭猛抽。当下,电子化的盛极其行,科技手段的飞扬跋扈,“神秘”不再神秘,虽非沦到一丝不挂的田地,但遭受扒剥的世象并不鲜见。过去的去神秘化似乎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这年头,神秘不再,业已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又一种“乡愁”。
鄙人不是故作高深,耸人听闻;不是在作伪命题,争抢 “麦霸”;更不是要人心复古,重归浑沌。随手拈取一些世象,权作佐证:文娱明星身后一批又一批的“狗仔队”;走到都市的大街上,到处是摄像头;谁谁有个动静,立马上网“人肉搜索”;一些所谓的“前卫人士”对历史文化采取的“虚无主义”;一再“瘦身”的书店书架,摆的多是官场发迹术、商场博弈心理学,还有理财经、健康读本,更夹杂一些相面术、手相学之类的灰色书籍。还有,与钱玄同似乎有“异曲同工”的,是近来在文坛上十分走红的台湾作家张大春。他的新著《大唐李白·少年游》甫一问世,世面就有叫好声鹊起。这位人称“武器齐备的侠客”,用“融历史、传说、小说、诗评于一体”的独创手法,一夜之间挑落了年轻李白头上的光环与面纱,诗仙不再神秘,只不过是个“自媒体”,是个以诗“干谒”送人的投资取巧者。这与钱玄同的“春秋笔法”,不是一档子事。张大春与李白相距太远,想象的动车只能开往戏说,不能抵达诗仙的原乡。这样的“去神秘化”,令我瞠目结舌,不肯苟同。
我们谙知:真正关乎心灵、关乎爱情的密码,是窥探仪器所不能窃取的,是厚黑学等功利学术所不能破译的,是一家之言的想象与强加所不能公认的。大圣人孔子几千年前就曾慨叹过人心像天体一样难识,这“难识”就有神秘的成分。我们不能屈膝于神秘、献媚于神秘,但也不能践踏神秘、娱乐神秘。正确的做法是——敬畏神秘。
我有必要将“广大”的命题切入到文艺创作上,因为业已贴上作家标签的我,以为有一点“优势”,有这份责任,更重要的是“文题”又切合我一直坚守、呵护并敬畏的形而上“神秘”的指向。
无论是私人化的还是集体性的,文艺创作需要“神秘感”,文学作品需要“神秘性”,因为“神秘”更接近美学、接近心灵。马尔克斯斩获诺奖,颁奖辞中道出他作品魔幻和现实主义交织,还有他的“马孔多镇”的神奇而真实;毕加索著名画作《蓝色房间》,常人看到的似乎只有异样笔触描绘的裸女淋浴的形象,实质上它画中有画;百年昆曲,在常人的耳朵里只是一种“不同的声音”,但在白先勇的心头,它是“此曲只应天上闻”的仙乐。用冯骥才的话说,多少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式微,一是我们不懂它的至贵,不懂得它的神秘;二是我们也没有让它葆有神秘感,它已是沦落风尘的、可有可无的大路货。
钱钟书的小说写得好,“鸡蛋”好吃缘何要看“母鸡”呢?但有一些读者就是凭着“窥探欲”而打搅这位不喜热闹的大师。文怀沙人长寿,精气神足,有人对其养生秘籍刨根问底,老人家答曰:“平生只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神秘似乎不再,其实“半美人”反而愈加“朦胧”。有好奇者问黄永玉为何“不近女色”,这位可爱有趣的小老头儿贴着问者的耳朵,大声告之:“我阳痿呀!”真耶,假耶,大家会心一笑后,一种近乎圣洁的“神秘感”油然而生。那日在京听课,蒋子龙先生感慨如今“人成精了,文学怎么办?”他的“天问”是哲学的:一者,人成精了,“神秘”实则已不神秘,精怪只是名利的奴仆;二者,文学不再“神秘”,灵魂怎么办?灵魂是神秘的、抽象的,是我们精神的庙宇,我们怎么来礼待它?我们不能让它淋上滂沱雨水啊!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门户洞开的当下,在全民娱乐的时代,听听星云大师是怎么说的:“我不一定要叫人家信佛、敬佛、念佛,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行佛”。保留心头的一点禅境,这就是神秘,是我们的心灵所需要。
留一点神秘陪陪心灵,就像远方之于旅行者,就像敏慧之于阅读者。敬畏神秘,现在还为时不晚。
文脉延绵
那日,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编剧张建勤讲课,他告知我,不日将参加一场由南京作家、学者、报人发起、组织的“文字的活法”研讨,属沙龙性质。在后来的《江南时报》“文艺范”副刊上,果然就读到了这方面的资讯,他们为当下“文字的活法”而操心,体现的是当代文化人的责任,值得点赞。
我必然联想到另外几位文化人,同样令我心仪和感动不已,现一并辑录于后,以示敬重,愿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彰扬斯风。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一位有着责任自觉和良知担当的文化人,他叫邓康延,先后在深圳、北京、南京、重庆等地举办“《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向观众立体化展现民国时期十位前贤的图像影视资料,前贤的姓名如雷贯耳: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先生回来的时代,就是黄金时代”。展至一处,观者如潮,人人叫好。作为纪录片的策展人,他动情地说:“我不拍,很多人和事会被岁月湮没。”
不一而足。我不能不说到家乡阜宁籍著名电影导演夏振亚,十多年前,他揣着同样的衷情和愿望,顶着酷暑、冒着严寒,连轴转地将沪上朱屺瞻等年事已高的书画大家生活和创作影像抢拍下来,制作成弥足珍贵的“活”的档案资料,他也动情地说过同样的感慨:“再不拍,就来不及了!这是我的责任!”
这样的担当、襟怀、良知和敏感,鄙人又遇到一位,他叫李钟声,粤地一位资深记者和作家,新著《岭南画坛60家》,被业内誉称为“一本独特的岭南美术‘群英谱”。他在书中以人为经、以画为纬,品画为表、读人为里,对名望、成就均高的本籍、本地的书画家进行全景“记忆”。其中,他对年逾古稀、病疴在身、以擅长美女人物画驰名的林墉的“深度”的人物速写和对艺术、生命的思考、感喟,令人唏嘘,眼角含暖,心头生春。
再说上海老作家邹身坊先生。邹先生的父亲,曾和弘一法师、丰子恺先生有过交集。在他七八岁时,其父教他兄弟姐妹唱过四首歌,其中一首正是弘一法师的《送别》,另三首分别为《月》、《雁》、《贫女》。尤其是《贫女》同《送别》词韵一样美,其乐曲都来自欧美,歌词均是国人创作。它和《月》、《雁》的歌词是不是均出自弘一法师之手,由于七十余年的光阴湮没,成为悬念。邹身坊老人考虑到自己和兄弟姐妹都已步入垂暮,待他们辞世后,这几首优美歌曲就鲜有人知晓了。于是老人家不忌高龄,赴上海、浙江图书馆等处,查找解放前后出的歌曲书集和音像资料,寻找除《送别》外的另三首歌曲,没有斩获。他立即动用记忆守存,把它们默记下来,以《几首早期的抒情歌曲》一文,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完璧”,不让其在音乐文献中消失,编、读者肃然起敬。
还有。为了不使昆曲艺术家“人走戏失”,香港民间人士叶肇鑫发起并出资的文字影像作品集《昆曲百种 大师戏说》,去年10月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浦睿文化正式出版面世。该作实则是项浩大“工程”、煌煌巨献,可谓是昆曲立体化、多视角的“档案馆”、“教科书”,旨在抢救和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剧。集结了全国张继青、侯少奎、汪世瑜(《昆曲百种 大师戏说》的策划者兼艺术总监)等29位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以“一人一说、一戏一题”的形式,对昆曲600年流行和积累下来的109个传统折子戏及其戏中的表演艺术做出系统和完整的阐述,通过文字与影像实录对照互现的方式整理出版。
令人动容的是,叶肇鑫并非富豪,至多是个广义上的文化人,这位“票友”凭着对中国传统戏曲之美的一腔挚爱,他全身心、事无巨细投入这个项目,还投入了完全个人出资的600万元人民币。2008年秋酝酿和立项,5年来,每每难以为继之时,叶肇鑫和汪世瑜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在录制进行到一半时,叶肇鑫不得不卖掉在上海的一处房产。
前述是我今年阅读的意外获得,是“附加值”。我也深知:过去、现在、将来,国内、国外,这样有担当、有责任心的文化人,虽不是恒河沙数,但也不是寥若晨星,他们都是西哲所言的“持烛人”。我集中地、忠实地推介这几位文化人,手法上没有捣鼓什么花哨(我说得再美妙,也没有他们做得好)。我以为:自己也是一个贴上作家标签的文人,写下此篇,也算是尽到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