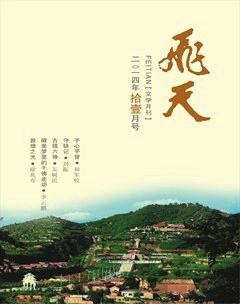杨光祖的文学评论
侯川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诸如人情评论、圈子评论、红包评论、学院评论等等,充斥文坛,颇受读者的怀疑、责备和反感。杨光祖也就是于此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之路,积十数年之功,倾尽心力,以文字的桀骜不驯、观点的新颖独特,及大胆直言、犀利文风,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杨光祖,生长于通渭这片有着深重的历史伤痛与自然之痛的土地上,后又长年生活、工作于黄河之滨的金城兰州。文学,让他魂牵梦绕,文化,让他脱胎换骨。他的文化思索、文学追寻,伴随着他生活和工作的整个过程。是家乡的土地、美丽的黄河以及令人难以想象的海量阅读,滋养了他的艺术生命,给他带来了奋发向上和追求完美的动力,带来了思考、探索与创作的灵感。杨光祖日积月累,厚积薄发,近年来在文学评论方面呈现出一股强劲蓬勃之势,在国内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
杨光祖说,批评是一种致敬[1],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夫子自道地表明了自己的独异风格。在评论中国当代小说时,杨光祖往往拿伟大作家及其作品来比照,深入细致地分析我们当下作品的不足和欠缺,充分体现了一种贯通古今文学的历史眼光,表现了他关注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渴盼伟大作品问世的赤子情怀。在全社会都乘坐物质主义的列车向欲望的纵深处飞驰的时候,他却在思考这个民族关于“天空”的一些问题。
欧阳修曾说,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2]应该说,“慎许可”,是一切成熟的有识见的批评家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在评论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杨光祖往往抱着非常严谨审慎的态度,从不轻易言说,而且眼光十分挑剔,哪怕一个细小的瑕疵,也逃不过他的法眼。因此他在评论界被誉为完美主义批评家。当年杨光祖给《白鹿原》写评论,其中有比较严厉的批评,在《小说评论》发表后,陈忠实先生打来电话,给予充分的肯定。他那洋洋万字的《雷达论》,不溢美,不掩饰,平心而论,直抒胸臆。“极具个性的论说,无任何套话和陈言,发掘我之为我的特性,抓得很准,心有灵犀,看到深层,知我来去。实为有风骨见性灵的好文章。”看到评论后,雷达如是说。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带灯》一经面世,便好评如潮。然而杨光祖通过细读慎思,发现了《带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贾平凹最近的长篇小说《带灯》里却没有过得去的细节,因此,我们感觉女主人公带灯与那个小镇总是那么虚幻,不真实。作品没有‘揭示出事物本身的内容,只是闭门造车而已,到处充满着‘任意性。”[3]独具慧眼,力排众义,无所畏惧,敢于直言,体现了杨光祖一以贯之的批评作风。不仅如此,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带灯》存在的硬伤:“《带灯》最大的败笔就是‘与远方人的通信。”[4]并深入细致地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证,其眼光之敏锐,批评之大胆,思维之严密,令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完美主义”,其实还表现在杨光祖对于自己的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无论读、写、论,他都是慎而又慎的。在文章的语言修辞、章法结构等方面,都是反复斟酌,再三再四,直到满意为止。古人有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5],“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杨光祖在为文之道上的修养和识见。
杨光祖多次对当下中国文学存在的低俗之气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尖锐的批判,并深刻地分析了历史、现实以及作家个体存在的诸多原因。在揭示当下的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时,敢于撕破,直指病灶,幽默冷峻,发人深省。面对优秀的作品,精彩的文笔,杨光祖往往情不自禁面露喜色,评论起来那自是笔下生风,文采飞扬,如有神助。而面对一些粗制滥造之作,或者反人性、反人类,价值观错位,低俗无聊之作,杨光祖则毫不顾惜人情颜面,给予严厉的批评。杨光祖曾经对贾平凹的《废都》和余华的《兄弟》作了严厉批评,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精神以及他在文学艺术上完美主义的追求。“他的文笔的酣畅,严谨而又能通脱跳踉,平实之中每每闪动着剑戟的寒光。”[7]韩石山对杨光祖的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杨光祖的文学批评具有强烈明晰的差别意识,对于作者和作品的高低优劣,他评价时观点鲜明,态度明确,毫不含糊。文学批评的差别意识,来源于海量的阅读和火眼金睛的鉴别力,来源于大无畏的求真勇气和过人的艺术直觉。在《批评是一种稀有的才能》一文中,杨光祖大力提倡求真意识,并对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文学界忽视或扭曲文学批评价值的错误认识,给予冷静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他呼吁人们重新认识批评的地位和价值,了解批评的独立意义和自由精神。杨光祖非常看重艺术直觉,反感那种理论过剩的教条主义批评。这些,正是一位优秀批评家的艺术魅力和艺术生命所在,而杨光祖毫无疑问是具备的。杨光祖具有良好而敏锐的文学直觉,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文学才华,对文学抱有旺盛的热情,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都蕴含着他在文学和思想方面深藏于内心的破茧化蝶般的梦想与追求。
古今中外杰出的文学家或批评家,他们不管是搞创作,还是批评,一般情况下文体是不存在问题的。司马迁、柳宗元、鲁迅就具有很强的文体意识。然而现在,我们若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很多作家、批评家在文体意识方面竟然是糊涂者多,清楚者少,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杨光祖无论在批评还是创作中都有很强的文体意识,他多次撰文强调“回到汉字”,期盼那种穿过黑暗的声音。在文学的“形式”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面对当代作家疯狂的长篇小说情结,他在《长篇小说热与作家的文体意识》一文中,严厉批评有些小说作家缺乏文体意识,强调优秀的作家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体”。杨光祖对于文体意识的论述,对当代作家在文学艺术上走向成熟走向完美,必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杨光祖的评论文章不仅问题意识强烈,观点新颖而独到,擅长以小见大,撕开一个口子,直捣黄龙,而且他一直将评论当美文写,他的评论文字没有学院派的那种佶屈聱牙,更没有那种理论的生搬硬套。他的理论如盐入水,是内化于文字之中的。杨光祖的文学批评深刻、尖锐、冷峻、幽默,字里行间,蕴蓄着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和深切独异的生命体验。他不管是评论名家,还是熟人,只论文学,不讲情面,既有高度,又有深度。面对一些粗制滥造、低俗无聊甚至价值观错位的作品,则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的批评。对于文学新人,则爱惜有加,常常寄以厚望。当然,他的散文,也有着评论的尖锐深刻,有他自己的哲学,乱中不乱,齐而不齐。他通过散文的书写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包括文学、艺术。杨光祖的散文篇篇读来真实深挚,幽暗唯美,洋溢着人文情怀。其中明灭着灵魂深处的幽光暗影,发作着难以言说的隐痛,跳荡着或隐或显的生命旋律,显现着思想历程的艰难坎坷。读杨光祖的散文,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庄子的超然,还有一些鲁迅的峻急,仿佛看到了鲁迅的那种“盗别人的火”而“煮自己的肉”[8]的灵魂撕扯。
二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有了深刻独到的思想,他的批评才会发出鲜活的生命之光。刘勰的《文心雕龙》,首篇即是“原道”。这里的“道”,其实就是作者的批评思想,它是贯穿于整部《文心雕龙》的。杨光祖的批评思想,大体来源于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以儒家的责任与担当及道家的生命观与宇宙观为主的贯通百家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我和杨光祖本人曾经闲谈,涉及儒道,感觉他读儒道经典,理解非常深细,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见解。例如,他对孔子深恶“乡愿”之行为,就表示非常赞同,并以之指导自己的批评,这对我也是颇有启迪和教益的。还有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思想,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也因此认识到,当下的作家、评论家,是普遍缺乏“弘道”的精神和责任的。他们最喜欢的,应该是道弘自己,或者压根连道也没有,只是造出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弘”自己而已。对老庄之道的研究,也极大地激发了他对文学艺术规律及境界的思考和探索,并自觉地以之指导自己的文艺批评和创作。
他在《道与艺术》一文中,经过对“道”的体悟研究以及名家大师在艺术创作上的“得道”现象,针对现实,发表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可惜,现代化,打乱了这一切。所谓现代化,也就是技术化,甚至工程化。而技术,是非常无‘情的,它只是制作,不是创作。”“西方的反现代思想,与庄子是相通的。我说,中国人天生后现代。但如今的中国人要进入中国传统文化,还必须打破现代语汇、现代思维,回到传统的语汇。否则,用现代人的思维理解古人的思想,难免楚河汉界。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尽管读,且不要管那些专家的理论,或研究成果。古人说,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无‘道,导致了当代学人的轻浮、狂妄,及浅薄。”这样的言说,出自灵魂,发自肺腑,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对当下的作家及批评家不无启迪作用。
二是西方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长期以来,杨光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与文学著作。他阅读这些著作,绝不是为了装点学人的门面,为了写论文写著作准备材料,或为贫乏的思想找几块遮羞布,而是精神的探险,思想的追寻,是对思想伟人的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穿越,是对人类的思想高峰的攀登与阅览,是与这些伟大灵魂的一次次交互对接,是对自己灵魂的救赎与安抚。
还是在《守候文学之门·后记》中,他再次这样写道:“你既然选择了文学,你又选择了在信仰的前提下去从事这项工作,也就是说你把文学当做了你安身立命之所,那么由此导致的所有结果你都必须毫无怨言地承受,包括贫困、误解、侮辱、屈辱、精神的煎熬,当然也包括光荣、荣誉、友谊,等等。”读杨光祖的文学批评,我一直在心里存有一个问号,他究竟是哪来的似乎永远也使不完的热情和劲头?这时,我总算弄懂了,原来杨光祖的文学批评与艺术追求,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坚实的信仰支撑的,他始终是站在别人望尘莫及的思想高地上的,这些是眼下一般的文学之人很难具备的。
青年文学批评家唐翰存有一段话说得好:“我发现,他的批评背后的确有一种好的理念在支撑着。他大概受了中外哲人有关批评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影响,那种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怀疑的精神,敢于说真话的勇气,以及在学理层面上讨论问题、接受别人反诘驳斥的态度和胸怀,都是自觉贯彻在他的言行中的。”[9]这是颇具眼光的见解。
当然,杨光祖是绝不摆理论迷阵、不玩概念游戏的。他说,理论如盐,是内化于文学批评之水里的,看不见,但可以尝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杨光祖的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批评,也包括散文创作。也因此,他的文学批评,他的散文,有一种深水潜流之美,及“随风潜入夜”的阅读效果。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杨光祖的评论,以及散文,是发自灵魂的写作,其中有心灵的隐痛,生命的颤抖。
杨光祖为人性急,常有时不我待之叹。我隐约发觉,他身上似乎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焦虑之症,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文化焦虑症。他的内心世界似乎很深地镌刻着“文化”二字。当他有话可说、有书可读、有文可撰时,则显得较为平和自如,而当无所事事之时,他则满脸流淌着焦虑、抑郁之情。在与我的交谈中,诸如“一定要多看书”、“要写出好文章”、“多向高手请教”、“多读古书”、“读些外国的好书”、“不要浪费时间”之类的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有时因为某事跟他多说了几句话,他会出乎意料地突然发出怪怨之声,你看,又浪费了我多少时间。我不知,此举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是否曾经招人不满,而在文学批评中,我发觉,杨光祖的“文化焦虑症”有时难免会给他的性格与心情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不利于他对作家与作品的客观评判。比如,一个作家,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也相当艰难的。其中难免走弯路,甚而至于失败。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或稚嫩,或失误,或成熟,或健全,或失败,其实有生命的律动在里面。由于性急,躁狂,一时做出存在偏差甚至错误的“断语”,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不过,从思想与艺术的追求和探索的角度讲,我倒感到了他的“文化焦虑症”的可敬之处。杨光祖,是否因他的“文化焦虑症”,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过种种不堪呢?“但这一年的读书、写作也没有别人想像的那样轻松,因劳累导致的严重的精神衰弱及强迫症,使得我经常处于一种焦虑之中。经过一年多的折磨,无论肉体,还是精神,我都明显地趋向成熟了。”[10]这段独白式的文字,证明我的感觉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趋向成熟”之说,可能是一种迎合俗世之心的说法吧,而在我看来,他钻研国学,痴迷老庄,深读哲学,醉心艺术,近年来使他逐渐在摆脱情急躁狂之状,抵达一种明慧通脱之境。
众所周知,一个成熟的文学批评家,应该有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建构。目前,我们尚未见到杨光祖在文学批评方面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和见解,甚至可说是他自己的尚在蕴育探索之中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却已在他的批评文章及专著中初露端倪。例如,我们在他的《守候文学之门》第一章第一节《批评的伦理底线与批评家理论主体的建构》中,就能看出杨光祖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具有过人的见识和较高的水准,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诸多理念及大体的框架结构,似乎正在蕴酿成形之中。我们期待着,在这方面能够尽快见到杨光祖的最新成果。
注释:
[1]杨光祖:《批评是一种致敬》,《南方文坛》,2012年第5期
[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杜甫传赞》,中华书局1975年
[3][4]杨光祖:《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6期
[5]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岳麓书社1991年,1009页
[6]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情采》,中华书局2013年,286页
[7]杨光祖:《西部文学论稿·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9
[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09页
[9]唐翰存:《批评的勇气——读杨光祖<西部文学论稿>》,《甘肃日报》,2004.12.10
[10]杨光祖:《守候文学之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