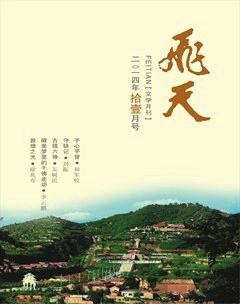醒里梦里的千佛走动
李云鹏
可以这样说,敦煌是段文杰贴身的符号。
有过四五次与段文杰先生近距离的接触,而活动与话题,无一例外都关乎敦煌。对于段文杰,这是他毕生的主题。岂止是主题,段文杰的自我表白是:“秉烛前行在文明的宝库里,除了敦煌已成精神信仰外,心里无他。”
精神信仰!不是寄托,而是信仰。你掂掂这分量!
把敦煌定格为自己精神信仰的这位敦煌学的大师级人物,这位苦行僧般厮守莫高窟半个多世纪的追梦者,这位掌孤灯于幽暗洞窟,临出380多幅精致壁画摹本的艺术家,名响中外的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他身上体现出一代敦煌学人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可师可范的炽热情怀。我国新时期文学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在1981年访问敦煌时,有几句颇为中肯的评价:“敦煌石窟还应供奉两位现代的尊神:常书鸿,段文杰。他们二人可称为现代敦煌的守护神。”还加了一句,“两位大有功于敦煌石窟啊!”那是在一次晚饭后,冯牧和相随的我们几位年轻朋友在敦煌街头散步时轻言轻语若有所思吐说的感慨。早此一年,另一位访问敦煌的香港诗人何达先生,亦有动情的慨叹:“敦煌不可不看,这段文杰不可不见。”
我是这两次访问的随行者。其后的1993年陪同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唐达成所率中国作家代表团;1994年陪同在兰州举行的全国文学期刊主编研讨会的老总们,又两次走访敦煌。段文杰先生对我们这些访者的热诚及对敦煌事业的赤子之心,丝丝缕缕,应该是写在作家们心壁上的鲜亮一笔。
日月轮转,时间已过了二三十个年头。在段文杰先生三年忌日之时,翻阅他的《敦煌之梦》巨著,一些昔往记忆的碎片在我脑海里依次浮现出来,先生几个时段的形象慢镜头然而清晰地向我走近,慈和的微笑,博学在胸的幽默的谈吐,以及,因忧愤而生的有时峻厉的神色……清晰如近在眼前的灯火。
清晰在我至今记忆中的,是1980年8月香港诗人何达到达敦煌次日,段文杰先生带我们到重点洞窟亲自讲解的情景(随后几日又安排李永宁先生持续讲解,和被何达叹赞为敦煌“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满腹古今的绍介)。这应该是何达先生关于敦煌的第一课?对于第二次来敦煌的我,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课,我有一个小学生必须的恭谨。
一支手电筒的微光,不时定格在壁画、彩塑的某个精粹的细部,段老诗意的讲解,高山流水,使壁上的物事生动了起来:飞天翩翩酣舞于天宇,长袖甩出了近乎幻化的至为优美的曲线;九色鹿的绝对胜过当红芭蕾舞星的奔姿令你只想把她揽入怀中;而连环画中以身饲虎这一类的故事,也能使你入迷,像孩童时享受外婆那令你百听不厌的古老故事。听着他的讲解,那古老艺术有声的熏陶,不由你进入敦煌艺术的奇美境界,久久地沉醉其中。我尤其忘不掉他讲解时的神态:幽默风趣,神采飞扬。听他讲112窟敦煌壁画中堪称旗帜性的反弹琵琶伎乐天,他眼神和言辞里透出的那种自豪,有一种山青水秀之妙。讲到酣畅处,那确乎是眉飞色舞的情状,近乎着意的炫耀——对敦煌历久远风尘而光芒不谢的中华文化瑰宝爱到极处的一种着意的炫耀。我因这炫耀而被深深吸引。
这与我初次接触敦煌时的情境有着太大的反差。
那是1956年树叶转黄的仲秋时节。一支在修建的兰新铁路瓜州(当时称安西)、敦煌段上执勤的我所在的部队,时有驱车上瓜州、敦煌县城采购日用品的差事,我趁机约一位战友走了回莫高窟。此处用“走了回”,既有时间仓促,只草草过了五七个洞窟,也用以状当时完全处于对敦煌艺术的蒙昧无知。那时莫高窟是开放的,洞窟无门,可以随意往观。两个不满20岁的小兵,面对千年岁月磨洗的壁画塑像,不识不解,进入不了我们的欣赏范围,那距离不好说有多遥远。自然也不知这地方有个段文杰。无知总是可笑的,无知甚至是可怕的!回驻地,我的那位同龄战友只以“没意思”三颗字回答了战友对莫高窟此行的询问,我脑子里也没有比同行战友高一档的说辞。这与此刻的情境是何等的不同!我是说,段老的讲解,真知灼见,说是心灵的倾诉,一点儿也不过分。香港诗人何达在新疆的一次座谈中提到敦煌时有此评说:“听段文杰、史苇湘、李永宁们谈敦煌,强似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你听不厌,你会迷上敦煌的。”
我不敢说迷上敦煌,而段老的此番讲解,近乎是对我早前对敦煌认识的一种颠覆性的改造。一个奇妙的净土世界在我眼前娓娓显现,耳旁似有悠远隋唐的钟磬声悠然飘来,气氛中便添了一丝苍然古意。这个古丝绸之路的驿站,这个集千年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艺术殿堂,已不是1950年代我初访且不认识其价值的那萧瑟秋风中的莫高窟了。此刻在我眼里辉光四射。我也有了台湾诗人向明感于“那一窟一窟的历史骄傲”挥洒而出的《莫高窟随想》中的同一感觉:
面对如此庞大逼人的一首史诗
我胆怯得
不敢随意造次
何达来敦煌,了解到他曾去过英法等国,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巴黎圣母院……段老便有一种急切淘取境外信息的虔诚,请他为院内专业研究者绍介所见。何先生到达的第三个夜晚,段所长就组织专业人员座谈。段老听得是那样认真,偶尔还插入一些提问。记得在将近结束时,何先生恳切地建议:“各位专家都应该多去这些地方走走。那是个大世界!”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场内掌声起处,分明有段所长带点儿幽默的笑声。应该是赞同,又似乎含有一些无奈的成分。苦笑?这使我又想起滞留敦煌期间的一段近似苦涩的小插曲。
一天,在研究所的小院内。一位外国老太上厕所(蹲式的简易厕所,说俗点,高档了一点儿的水泥槽茅坑而已)出来,当院一边整理衣裤,一边呜里哇啦吼叫。我听不懂,问何先生:她吼什么?何先生苦笑说:法国老太,法语:“中国的厕所太可怕了!”在是否将此事转告段所长的问题上,初时何先生有点儿犹疑,大概是怕伤了主人颜面?我知道当时各个单位经费的窘迫状况,以为通报通报未尝不可,或许这老外的“中国的厕所太可怕了”上达之后,能使主管部门有所触动?便怂恿何达先生传话。当晚段所长来我们宿处,诗人的何达先生一定是有了成竹在胸的构思吧?在许多闲话之间,以一种轻描淡写的随意穿插,颇艺术地提到那令人尴尬的“厕事”。神色凝重的段老紧闭嘴唇,重重地点了几下头,遂露出一脸苦涩的笑:“谁不想有个像样些的水冲厕所啊!”他拍了拍衣服口袋,我们意会:囊中羞涩!那是刚刚从危难中走出不久的依旧穷困的中国的1980年啊!
颇出我们意外的是,打破短暂郁闷的,是他起身时爽然抛出的像是玩笑,我认定是心语的:“何先生,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拎着爽朗的笑声走出门去。
面包!牛奶!其实是段文杰对进入新时期的我们中国的信心满满的期待。在这里,需要插入一段重要的记事。1980年代初,对于中国是百废待兴之年,敦煌亦然。这时一位伟人的到来,为敦煌注入了生气。1981年8月8日邓小平视察莫高窟,陪同参观的段文杰向小平汇报了研究所的工作和面临的困难。小平同志说:“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指示有关负责同志给予关注并解决困难。那一刻,段文杰精神陡然一振,有一种曙光在前的感觉,曙光照耀着莫高窟的感觉。应该说,这是敦煌久存困境的转折点。在邓小平视察之后的年月,令段文杰欣然的是,他那句借自影视中列宁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放言,得以应验,或者说,开始渐渐地有序地应验了。敦煌是件大事啊!
某晚,何达与段文杰又扯到了《丝路花雨》,以敦煌莫高窟艺术为题材的享誉国内外的那出大型舞剧。一个是该剧的顾问,一个是该剧在香港演出时以文章推誉的“粉丝”。由“丝”剧衍及敦煌艺术这面历史镜子的方方面面,兴致浓到俩人似乎谁也不想中断话题。从旁聆听几乎不插一言的我,享受着两位长者酣畅的交流。
仅一出《丝路花雨》,他俩就有得谈的。来敦煌前,何达先生在兰州与《丝路花雨》剧组有过几回座谈;我与“丝”剧文学脚本执笔者赵之洵也有过交流。对于段文杰为“丝”剧的成型所做的贡献,有着一些了解。我们记得诗人赵之洵对段老的推崇:“段老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流的顾问,他为我们这出舞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甚至激醒了我们的灵感。”
反弹琵琶的舞者,在这洞窟里舞了1000多年,还没有飞出五尺窟檐。甘肃歌舞团一批解放了手足的“牛棚”囚犯,欣喜地在112号洞窟前靠岸。欣喜地得着段文杰悉心的指点。在回答《丝》剧编创人员“敦煌壁画众多舞姿中,什么舞蹈动作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提问时,段先生成竹在胸地推出:“112窟的反弹琵琶最有创造性、代表性,舞姿也很美。”反弹琵琶伎乐天遂生动地复活于舞剧《丝路花雨》之中,成为《丝路花雨》舞剧中最靓丽的标志性的形象。诗人的赵之洵称此为“段老一语为舞剧点亮了诗眼”。此前我们已从赵之洵口中得知,剧中老画工“神笔张”的起名,也出自段老的神思。
听到何先生的赞说,段文杰却只有轻描淡写的一笑:“我不过给剧组介绍了一些我们的研究心得。是艺术家们复活了敦煌,使更多人通过舞台形象亲近了敦煌,功在他们。”
《丝路花雨》把敦煌舞开来,18种器乐不鼓自鸣,古色古香的敦煌大路展开在世人面前,犹如一匹色彩斑斓的丝绸。
由《丝路花雨》想到,对于段文杰,敦煌不也是一个追梦的舞台吗?这个灿烂无比的艺术世界,是他终生情感的寄托。追求,磨砺,苦难,欢乐,酸甜苦辣,一一内涵其中。他的蹈步,充满坎坷仆跌,而痴心不改。“神笔张”的形象中,有无段文杰们的某些身段或曰元素?我在想。
藏经洞,始终是段文杰心头一块不能愈合的伤口。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散失四万多件!莫高窟所藏仅是劫余之后的700多件!对于视敦煌为“精神信仰”的段文杰,无疑是“剜我心头肉”般的巨创。每触及,激愤之情便溢于言表。恼恨无知王道士贪小利而使珍贵文献流失之罪过,愤于窃取者的肆无忌惮。对何达,对冯牧,对我辈,交谈中每有提及,常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在指说被洋窃贼剥取壁画的空白墙面时,他用“丑恶之至”四字倾泻他的愤懑。记得1981年的冯牧曾问到散佚国外的敦煌文物归回的前景,段文杰一脸凄然:“现在只能说是心存期望。”十多年后的1994年我有机会重提此话题,段老脸上仍写满烦忧:“我现在还不敢乐观。”又愤然补了一句,“小偷又多半是无赖!”
然而段文杰始终存乎于心的,是散佚在外的敦煌文物的“完璧归赵”,并为此不遗余力。在世界各国游历、考察,一方面,“感受到敦煌艺术在国外的非凡魅力”,并为此“十分欣慰”;一方面,却又“在异国的夜晚屡屡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是因为:我听得到在现代、豪华的国际展馆中,有散落的敦煌珍宝在哭泣”。看到这存于《敦煌之梦》中的心语,我便理解段老对藏经洞事何以有如此分解不开的纠结。每在接待中外专家学者友好人士和传媒记者时,不断呼吁收藏有敦煌文物的国家和个人,将敦煌失散的文物“完璧归赵”。我便理解1994年段文杰访问俄罗斯时堂堂然的发声。令段文杰震惊的是,藏经洞的五万多件文献,流落俄罗斯的竟达一万多件!在参观某博物馆时,见到打着敦煌印记的文献,他心潮难平:这应该是中国的馆藏,中国展厅的展品!不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面对俄方人员,77岁高龄的段文杰就有底气十足、理直气壮却颇具外交风采的发声:“我热切地盼望你们把这些文物归还给我们。”
1994年,《飞天》杂志社在兰州承办全国文学期刊主编研讨会,老总们之前就有参观敦煌的冀求。开幕式我们邀请段文杰先生莅会。段老此前有过一次大手术,尚在恢复期,却欣然赴会并讲了话。爽然应诺:“敦煌石窟为老总们全面开放!”欢欣雀跃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总们久久地以掌声回应了段院长的美意。段老随后先于会议结束赶到敦煌,在莫高窟大会议室接待了全体老总,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依然一触及藏经洞话题就有“伤口”的发作。谈及被盗文献、壁画时,段老的绝对异于往常的神态,见出他心灵深处的啸动,这是他久久不能释怀的话题。用一个啸字,是因为他谈及此等话题,声调近乎啸叹,有意控制中的啸叹,令听众不由动情。这使我想起80年代一次他亲执电筒为我们一行访者讲解,当他说到敦煌艺术的价值,说到壁画被洋窃贼盗走之事时,那句“不管在千山万水之外,不管在哪一国的博物馆里深藏,闪耀的还是中国的光芒”。听者的我不禁怦然心动。我其后几乎是原原本本地将其纳入我的一首诗中——《认识敦煌》:
我在洋窃贼们的贪婪里
认识了中国敦煌的价值
他们窃取的珍品
不论远离千山万水之外
不管在怎样的殿堂陈列
闪射的依旧是
中国的光芒
确切点说,他的话成就了我这首诗。“你临摹敦煌的瑰丽之诗,有诗人悄悄地临摹了你”(拙诗《临摹者》)。台湾诗歌名刊《创世纪》选发我一册诗集的几首短诗中,就有这首短仅七行的小诗。惟我清楚,其实是对段老心底呕出的诗一般话语的光芒的赞赏,和我们的台湾诗人朋友对“中国光芒”体肤相亲的认可。尽管《创世纪》编者不会知道这其中的因由。
对于段文杰,一个关乎敦煌的敏感话题——来自一位日本学者的“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每言之,总令他情伤。这情伤,甚至含有某些不能承受之重的羞愤。说耿耿于怀,应不为过。1980年对香港诗人何达,1981年对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文艺评论家冯牧一行,都言及这一沉重话题。如果说对何达因其香港身份(那是中国的1980年啊)而多少吞吐有所节制,对冯牧则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倾吐:“中国没有人才吗?有一个安静做学问的环境吗?”那是积苦在心不须明言的激愤之语。他没有亮出答案,那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做学问?段文杰们有缠绕多年的烦恼: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似是而非的红专白专,揉搓了一茬又一茬无所适从的学者;敦煌研究所,不少专业人才在一连串的运动狂流中被呛水乃至被淹没。搞得段老自谓“伤痕累累”。但他避谈自己的磨难岁月。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位被“运动”多次揉搓的人。文革中流放犯一般举家发配到边远农村的日子里,压在段文杰背上的,不止是农田、水利工地、养猪圈沉重的劳动,更背负着足以让你喘不过气来的沉重的精神压力。尤其是,同那些相偎数十年的莫高窟的隔绝,对段文杰,近乎高墙无期刑拘的煎熬。段文杰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敦煌艺术,以及保护这些艺术的研究和思考。不管身在何处,他说:“心里装的还是敦煌”,“多少回梦里也有千佛走动”,“凌空飞舞的伎乐天向我飞来,仿佛要弹拨一曲天庭妙乐,抚慰我的心灵”。常常拖着疲累的身子,挑灯夜读,撰写笔记,记录心得,继续着他的敦煌艺术的研究。看到段老爱子兼善追怀父亲在村舍昏暗的煤油灯下专心读写的画幅,那以局促方凳为桌,圪蹴在自钉的半尺矮凳上的身影,给我一种悲壮的感觉。
什么叫矢志不渝?这就是。在琵琶声咽而断了反弹绝响的日子,封禁不了的仍是千佛洞的飞天在脑海里春燕恋巢般飞旋的神采。
焦虑,痛切,兼不服。但现实是无情的。这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敦煌的研究确实滞后了一些。日本的“集团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港台也成果时出;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却是十多年的空白。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不是在敦煌所在地的中国,而是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段文杰如此痛切地忆说当时的心境。
但这是必须坦然面对的现实。1984年,研究所改制扩编为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段文杰,在院成立后的职工大会上,慷慨陈词:“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
特殊的鞭策下,自有特殊的动力。是刻苦磨砺,也是明志:中国的学者是有充沛的才情和志气的。作为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段文杰朝乾夕惕,带领研究院一班人马,埋头于改变局面的苦斗。敦煌研究院的员工们,应能记得那些年研究院的一眼窗户,每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必会亮起的一眼窗户。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伏案挥洒着他的激情。段文杰的很多研究文稿,就是在繁忙的院务之外的一个个深夜熬出来的。我们说到“苦斗”,这眼灯明半夜的窗户,其实是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史苇湘、李永宁等等老中青学者们苦斗的一个缩影。段文杰是领头雁。
“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一论,也呼醒了散处全国各地的敦煌研究学者们决心争一口气的豪情。段文杰在这个激情洋溢的时段,以一个研究者又兼组织者的双重身份,广泛联系国内敦煌研究学者,广泛延揽人才,向一个预想的高地发起有力的冲刺。创办了《敦煌研究》期刊,汇集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参与了煌煌《中国敦煌石窟》五卷本的编撰工作。策划和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会议,策划和主持了多次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组织对外展出……有序地推动着中国敦煌学的发展。
存忧于心的,还有古窟的保护。这是敦煌研究一个重要方面。198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太多的“古文明”保护的压力,历史地落在他们这一代学人的肩头,使这位敦煌研究学者忧心忡忡。段文杰有此话:“没有保护,研究就无所依凭。”
千年岁月无情的磨蚀,加上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风沙漫于窟顶的侵凌,洞窟年久造成的危崖,大面积的病害,威胁着壁画、塑像的生存。这是久久燃烧在段老眼里、心头的忧患。1981年的冯牧,面对岁月剥蚀的壁画,曾问到有无办法根除其害,段老多少有点儿茫然:“科学或许会找到一些更理想的办法。”而其后多年,他倾尽心力于敦煌壁画的保护。主持制订了《莫高窟保护工程规划》,将国内外研究的成果科学地应用于莫高窟的保护,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危崖加固工程,修复了大面积的病害壁画和彩塑,不断探索和建立最佳保护环境。
他意识到,与岁月无情磨蚀的抗争,仍是艰苦而漫长的。月牙泉是一面镜子。如今的敦煌,风光得可以拥抱全世界;月牙泉,却瘦得几近一片柳叶儿了。对于敦煌,这或者是一种近乎橘黄色的警示?直到生命最后时日的段老,应该仍存有他的忧思。记得某次与段老说到月牙泉的渐次萎瘦,段老有一声长长的吁叹:不似往日了,老庙也拆了,水也小了!芦苇丛已经稳不住几只水鸟了。
孜孜矻矻十多年,任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尴尬历史。在我们上世纪90年代前的几次访问中,这“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几乎是段老每与人谈绕不开的话题。而其后,对1993唐达成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和1994年期刊主编会的到访者未再提及。我知道,敦煌艺术研究的天平,已经明显地不可动摇地倾斜于中国,世界不能无视中国的敦煌,世界同样不能无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中国几代学者一部部敦煌研究的学术专著,令世人瞩目地引领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话题应该不复存在。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7月15日刊有该报记者专文介绍敦煌遗产保护的成就,认为莫高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敦煌研究院的成就已经使它享誉全中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对敦煌成为典范充满了希望”。而这是段文杰及其前其后几代人的心血凝就。
在敦煌艺术研究曾经的重镇的日本,段文杰学术身份的改变,可以视作是一个标牌性的象征:享誉国内外的敦煌艺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等。“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如果说敦煌是件大事,谋于这个大事的第一方阵中,段文杰有着他突出的位置。在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年之际,段文杰获授“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绝对地当之无愧。在他退居第一线后,他仍时时牵恋着那片佛土。在他永久告别佛土之时,他必定欣然于继任者樊锦诗们光大着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在研究和保护方面继续着的重力推进。
2006年段老最后一次回到莫高窟,其时已腿脚失灵的老人,是由爱子兼善用轮椅推行的。在窟前栈道上,在九层楼大殿前,在莫高窟的牌楼旁,在枝繁叶茂的白杨林阴道上……他毕生敬奉的事业的故地,他厮守一生的家,目过处,他心潮起伏,久久流连其间,不舍离去。
心偎千佛,敦煌便成为他永久的厮守。我有《永久的厮守》为段老唱赞,摘句:
你就甘愿是此方一块
西部飓风也移挪不动的
心形的化石
即使最后不能搏动了
也仍是敦煌永久的厮守
我的记忆拉回到1980年。某日傍晚,三危山突显一溜光环。段文杰院长用清爽的川腔对在莫高窟外只一线细流的大泉河边散步的香港诗人何达先生和我欣然指说:“佛光!这就是三危佛光!”夕阳晕染的三危山峰顶发出一团奇幻的光芒,段老用一种近乎虔诚的语调继续着他的遐思:“心诚者可以看见千佛走动。”又自语似地补上一句,“千佛走动!”
那一刻,千佛似乎已在他的眼中翩然移动;那一刻,隐约间,我有沐浴于一种异幻佛光的感觉。
净土。千佛走动。醒里梦里的千佛走动……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