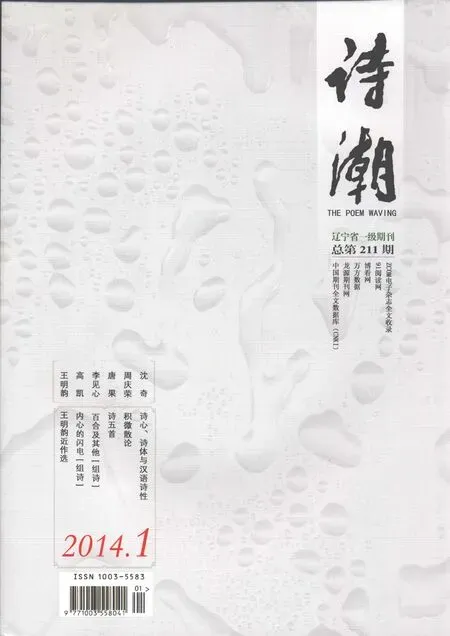积微散论
——与散文诗有关或无关的思考
周庆荣
积微散论
——与散文诗有关或无关的思考
周庆荣
△河床·河床
陈从周的《说园》我非常喜爱。他讲:山有脚,河有岸,路有形。凡河有岸,它就有河床。河床使水不四处泛滥,河流使水对土地和事物有了意义。散文诗写作时容易走神,容易飞笔,一大堆语言要对付,一大堆情感要抒发,象征或渲染似乎源源不断。怎样在心中先有河床?再多的水在河的概念下流动。
对于河床,往事如烟,只有水在上面流过。而且,有意义地流过。
△进步
不光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那种,而是时间乃单向的,它不等你。你坐守在往事里,会过早地坐在岁月的角落,如你甘愿寂寞,且又理解并深悟哲学的那种孤独,当然不会有什么。虽旧,但可能连时间本身都会对你肃然起敬。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甘心如此,而且会根据自身经验想在当下继续发挥作用,显示存在。这样一来,进步,便显重要。我对耿林莽先生的敬重,不只因为他是我的苏北老乡,或平常联系较多,而是在他不断出现的文字里,读出他一如既往地与陈旧相告别。文字干预生活,尤其是对丑恶现象的针砭,他没停顿在往日的功成名就上,而是和年轻人一道,看到散文诗依然在路上,而且长路漫漫。拥抱新生事物,同时尊重一路走过来。这是寻常的态度,而恰恰又是了不起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写作中进步的前提,也是散文诗编辑工作和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前提。邹岳汉先生是我记住的又一个人。因为时间和机会,我未能与更多前辈直接交往,但我相信所有对散文诗倾注心血并从不拒绝进步的人,我会感念在心。
△认识母爱
浙江诗人江一郎有一首写母亲的,大概是说母亲老了、瘦了,他轻轻一抱,毫不费力地轻轻抱起,诗里面却泊着母爱全部的重。
母亲的爱是单程车票,它不需要回报。每个写作者都有具体的母亲的面孔,易记起他认为最能体现母爱的细节,易正面不加抑制地抒写,比喻又易重复。
母爱的博大、无私似乎广为人认同。它有无选择性缺陷?有无溺爱和纵容?这样说,不是对母爱神圣的质疑,而是母爱在生活中一定会有发达的根系。当然,哲学上或类宗教的诠释是另一回事。人类的第一个女人,是所有生命的母体。谈及此话题,灵焚的《女神》可反复阅读。
写个体的母亲和写广泛意义上的母爱只有有机地结合、广泛才能深刻和生动。1991年,我在写《飞不走的蝴蝶》时,就是试图从多个层面来表达母爱。
△简单——事实和能力
不光是生活观的问题,在写作中重墨用在重点。学会简单,文字才能精光四射。一切的病大都与肥胖有关。
疯狂的,荒芜的,用剪刀或镰刀,裁掉。
唉,实际生活中的简单,其实有更多的无奈。
比如,亲切的面孔越来越多,一些陌生的本应成为新的亲切,但杂事和俗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且许多困难只能坚强面对。这样,只能推掉许多聚会,这当然会造成误解。
往简单处想,最好简单。从做人角度,力所能及地帮助,但世界上哪一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之简单自己,不为别的,只为了能有多一些的时间读书写作——在日益繁重的俗事之外。
△战斗斗什么如何斗
年轻时,读鲁迅是过瘾的。他敢于与同仁较真,敢于与社会较真。
把无聊的喋喋不休或日常思怨压低,最好省略。最好的时代也罢,较惆怅的时代也罢,我们一不小心活在这个时段。那就认真地活。
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战斗。他们有这个权利。曾写过《战士》《深夜,突起的心事》《不怕鬼》等,由于工作接触与观察到的还算丰富。人间不公不善不美的,一定需要人去斗争,不然放任自流会毁了长城。蚂蚁军团在于协同作战,它们一般不去互相敌视,这解决了斗什么的问题。
如何斗?握笔的人常常手无缚鸡之力。因年少时调皮,我的身手还算可以,但如仅靠蛮力,一定会头破血流。文字里有光,刺破或缩小黑暗;文字里有温度,温暖那些依然冷的人;文字里有高尚,让那些整日里卑鄙的人自惭形秽;文字里有力量,让仗势欺人的不得不收敛。当然,若想令文章彻底让世界如我们所愿,一定显得天真。
不是我不愿走出自己民族的属性和局限,而是我经常对人类期望过高。比如对日本,我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们的处事和对社会规则的遵守上确实有许多让人称道,但每当日本不敢面对曾经的战争屠夫行为时,我就真的想当一回士兵。就斗呗,地球都不在了,其实也没关系,宇宙和宇宙之外,谁知道今后太空的灵长动物是什么。如此一激动,广大的朋友们千万别当真。
△理想
概因去年出版的散文诗集定名为“有理想的人”,诗友们每每会问:为何这么大胆,还用这个词作为书名?我答曰:我那些庸常的文字看来你没细读。
一个平凡人能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理想?我的理想其实已经走出了理想。只是想让麦子更是麦子,让花更像花,让人更像人。让我们众人都能眼里有众人,从而相安无事地活着。
大话与高调要完成对天下麦克风的总动员,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现实主义地写作,理想主义地让自己有点精神。
△灵感等待恒远
写这些思考,其实更是写下我信口开河的说话。当我遇到烦恼时,我往往将烦恼扔下,走向另一种语言,自我安慰,甚至自我疗伤。
典型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踩到哪儿。写作的背景材料很多,大多在写作之外。外部的事物令人眼花缭乱,看准了什么,我们如何应对,有恒远的措施,更多的是需临机处置。灵感来了,它与恒远如何关联?
秋天,撒麦种,这时候不说麦子。这时候说等待。以温柔地发呆的方式看着冬天的麦苗,在下面的季节,在天气热烈时,看完麦子最后的模样。
我们的生活,它往往不允许我们一两个季节专门地温柔地发呆。它以多种方式吹着哨子,让我们大家都选择迫不及待。
他们何止只瞧不起诗歌?
日常生活里,不少朋友对我挺不错,我们在一起斗地主、打麻将、侃大山。我不认为这些就是庸俗和无聊,我觉得这是生活的真实。问题出在我读诗和写诗上。谈到诗歌,他们都戏言:那玩意儿管什么用?都老大不小了,应该全力以赴做自己该做的。是啊,他们何止只瞧不起诗歌?
好在,诗歌之于我,只是内心的原动力,我用诗歌的景象幻化我面临的诸多复杂,一切暂时远开去。天地可以宽,我可以片刻幸福。
△他们也可以承认诗歌
每年,总有许多从来不读诗的人可能是为了给面子,将书要了去。再见面时,不少人一开口便是诗
歌。三教九流的朋友,能忘却各自的角色,让某个时刻与诗歌有关。
写作和阅读者的关系,其实很简单。不无中生有,让语言在普世情怀里生根,让众人觉得文字仿佛与他们有关。
伟大的朴素,要拒绝多少炫目的奢华?他们也可以眼里从此有了诗歌,这样的诗歌应该是怎样的诗歌?
△时间、时间
看着秒表或撕下日历,以为时间就是这些?全部的内容,与人类有关的,更多的是无关的,都装在时间里。充满生机与腐烂、高尚与卑鄙、和平与战争、爱与恨,都在里边。时间这玩意儿,总在关键时给我们的生命作个总结,然后,它继续朝前走,它不会转身,它不会迷恋。我们所在的这个阶段辉煌也罢、险恶也罢,它都不纠缠。一马平川或崎岖坎坷,它只管走它的。文字里所显现的时光的痕迹,缅怀或期待,都是与人类有关。
时间对于世间人与事物是一视同仁的,它的表面的麻木不仁里,其实在等待我们对它的态度。不说这些态度了,会老生常谈。
我只想说对时间的要求:既然什么都装在时间里,能否把那些奸的、贪的、欺行霸市的、鱼肉乡里的、疾病和战争等等,不装在它里面?或者多腾出些面积,多装些美好的、高尚的、温暖的?
对时间提这样的要求是愚蠢的,时间只是一个单方向的容器,它一边行走,一边把一切装在袋子里。往里边填空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散文诗,是否也应该往时间里填些新的名堂?
△骨头
骨头重,我可以去想象血肉,如骨头轻,血肉再丰满,也可惜了。
我喜欢阅读有骨头的文字。三年前,读过金所军的几首诗,至今印象深刻:《七十年代的葵花》《秋天站在树梢上》《黑》《不当老大已经很久了》等等,里面的骨头重且硬。诗人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多年前就会背,我的一位有豪侠情怀的兄长,常常在酒后背诵。就是这样,硬骨头,再具血肉丰满,别人想忘记都很难。
△诗人印象
几天前,一位诗友与我闲聊,讲时下女诗人的作品大多走不出情感范式。我认为,写作断不能漠视情感,只是情感的方向可以更加宽泛一些。这几年,读到不少女诗人的散文诗,印象较深的有宋晓杰的“或沉静,或叹息”系列,语伞的“庄子”系列,爱斐儿的“非处方”系列,珊丹的“草原”系列,丹菲的历史地理诸章,还有金铃子、白月、水晶花、清荷铃子、青蓝格格、宓月、弥唱、夜鱼、原晓菲、姚园、李见心、染香、王妃、枕秋、转角等人的作品。
其实,辽阔且深刻,并非只是男诗人的专利。相反,有些男诗人的作品奶油味十足,有些血性、有些深度的作品,正如人一样,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呼唤。
△焦虑与忧患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社会现象里有许多从理论上讲是不应该重复出现的,但它们就是不断存在。焦虑是一种病,但不焦虑可能病得更厉害。有两种情形:一、事物已经这样美好了,你还焦虑?二、事实已经如此糟糕,你还不焦虑?如果把焦虑的方向放在这些问题上,写作中实际已经超越了个人日常的情绪。忧患意识是格局的范畴,觉悟的范畴。写作的人有时虽食不果腹,也要先为天下寒士吁请。
耶稣说:难道焦虑会让你们活得更长久?对于那些迫切想改变自己阶级成分或迫切往上爬的人,他们当然有理由焦虑,直至精神压迫症。诗人的觉醒,是告诉众人明天的悲剧可能阻止不了,但我们努力过。
由人类的过去,我们有理由希望未来更加美好,但从人类的所作所为,悲观油然而生。我预感到了可怕,然而,正是为了有希望,我们必须忧患。
△本性
大学时,很喜欢读斯宾诺沙。他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愿意坚持自己的本性。虎希望永远是虎,石头希望永远是石头。(博尔赫斯在一章散文诗里似也曾提及。)也曾在泰戈尔《吉檀迦利》里读出泛神的痕迹。尊重事物的本性,“花更像花,麦子更像麦子,人更像人”。(原谅我再次引用,有为拙作做广告之嫌。)这原是平常的,不平常之处出在对人的本性的认知上。本善?本恶?或善或恶?说不清了,所以我们都有强烈的期待,期待人的本性回归到纯洁与美好。能回
归吗?还是一直善在旅途?诸多偏离事物本性的现象对我们笔下的文字影响几何?不逃避,但能否同时也不放弃?
△让泉水发挥些作用
2009年夏天,在湖北丹江口的一次散文诗笔会上,我曾就散文诗创作的现象说过几句粗浅的话:泉水在山里时,很洁净,也很清静。没有浊世的那么多是非,似乎在守住自身的高洁。这很易与文人的心性相通。因而,大多数散文诗作品把重点放在泉的净与静上,品质和操守囿于远离尘嚣上。这种品质和操守的可靠性一定会让人生疑。我提到泉水应该走到山外,走进庄稼地和花草树木。让庄稼丰收,解决人间温饱;让花草树木茂盛葱笼,解决人间美丽。泉水在这种行走中对事物和人类就会起些作用,泉水就会变成有意义的泉水。当然,意义的过度解读会导致功利性的赋予。意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精神和物质,险恶江湖和卓尔不凡。存于一念,却凝重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