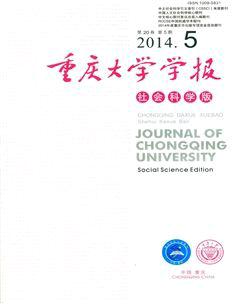公共安全意识变迁与门神造型的衍变研究
戚序 张红琼
摘要:门神是人类社会硕果仅存于中华大地的特殊的艺术形式,是华夏民间美术最为重要的源头。传统门神作为反映中国民间对公共安全的一类社会心理和祈福形式,从内容到形式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任何事物的现代性都可以从传统中找到根源,因而门神造型的衍变,既与历史的传承性和制度的阶级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又因为公共安全是一种社会存在,即主题的时代性和发展的动态性而重构。在当下,审视公共安全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并诠释其对门神造型衍变和重构的意义,是一种文化自觉。
关键词:安全;意识变迁;门神造型;现代诠释 ;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5015706
一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安全内容和表现形式,甚至同一社会制度背景下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或不同发展时期,也存在人们对安全的不同诉求、不同理解和期盼。通常,安全既指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或感受,又指国家、社会、个人所处的一种客观状态;当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就不存在恐惧,即为安全;而且国家、社会、个人都是如此。这样认知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笔者讨论公共安全意识变迁对门神造型衍变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人们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无论是基于生存还是发展,安全都是永恒的话题,都是人及社会的“第一需要”;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乃至个人都关注公共安全的话题,甚至说没有安全的发展就是非科学发展。然而对于公共安全的理解,笔者以为有两个维度:一是公共安全指维护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保障社会处于良性运行状态的社会体系,包括制度、体制、机制设置等内容;二是指涉及并影响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正常生产、生活的一类社会失范(社会问题)。由此,无论是从社会体系的角度考量,还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判断,“公共安全”都是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组织化进一步严密,安全保障进一步系统化的产物”[1]。
讨论一个时代或时期的“公共安全意识”的产生与形成,既是强调与这个时代或时期的公共安全社会体系或社会问题(社会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更是突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历史领域活动中的人来支配的人的主体性。虽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视角解读公共安全,对应着人们的根本利益问题、人与社会发展的成本问题、人与社会的文明进步问题、人与社会发展的质量问题等等差异性,但是“公共安全”的本质在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这也是笔者提出“公共安全意识变迁与门神造型的衍变”命题的认识论基础。
一个时代或时期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客观反映,并具有历时性(“文化堕距”现象)和共时性的特征。这种“意识”反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会以各种形式呈现,其中就包括人类的造型等视觉符号的形式,如门神造型的本源就是出自于“人的安全”的客观需要。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说:“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提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脱离对“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考察就不可能理解和解读文化形态的任何一种特质[2]。中国门神的造型及应用方式衍变的根源及路径,与公共安全意识变迁有着内在的同构性与外显的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门神造型的每一次大的改变及普适性应用的文化行为,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而在精神层面和文化诉求上对“安全”的独特回应,包括作为公共安全意识独特载体——中国门神的衍化形式。
笔者以为,通过对影响中国传统门神造型衍变主要因素的剖析,并重点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视角探索门神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精髓,尤其是在当下审视公共安全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并诠释其对门神造型衍变和重构的意义,应是一种文化自觉。
二
从一定意义上讲,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的历史“徽号”,它必然具有四大基本的社会特征:(1)历史的传承性;(2)主题的时代性;(3)制度的阶级性;(4)发展的动态性。门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心理于一体的文化艺术形态。这意味着在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门神文化,既是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化形态——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存在——是对一种特定生产或生活方式的特殊诠释。因此,它是探寻、揭示、解读一个地区的文明发展史和某一特定民族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社会“视窗”。
(一)历史的传承性
“任何文化都是有根的,因此要了解一种文化就是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 [3]。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并因为中华民族的自觉、自醒与自强不息而发扬光大,因而审视其“历史传承性”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在要求。人们对“安全”的客观需求是门神文化留存至今的深层原因。其造型衍变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历时性与发展的叠加性使其成为兼具展现历史发展脉络与反映同时代背景印记的文化符号,具有独特的文化信码功能。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安全的需要处在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需要层次,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亚伯拉罕·马斯洛著作《人类激励理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43年。
纵观历史,“……有了阶级社会后,先是统治阶级门上画虎,随着宫殿建筑艺术的发展,统治者权力的增强,门上又出现了神荼郁垒及古代勇士,赖以保卫生命财产之安全” [4] 。自汉代,有王充在《论衡》中引《山海经》佚文汉·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佚文。
,“黄帝时代门户画神荼郁垒”,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神荼、郁垒为最早的司门之神,在汉画像砖石中可见其护宅避凶的实际生活应用;南北朝时期有宗懔撰《荆楚岁时记》也涉及民俗和门神;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开始出现以历史人物为门神,如秦叔宝、尉迟恭、关羽、岳飞、常遇春等。尤其在南宋时期,门神形象由神化到人化的衍变过程充分映射出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变迁中公共安全意识变迁的痕迹。原始巫性门神逐渐被代表“忠、孝、仁、义”的英雄人物所替代,客观的社会实存“是民众普遍的道德伦理及情感需求,创造、选择了这些形象化的题材和内容,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伦理情感的符号”[5]。这种“求神不如求人”的替代与其说是以“神”震慑鬼魅,不如说是从祖先崇拜的原始意识中以更加理性的方式直接满足和顺应了现实社会中人们更为实际的公共安全需求,并一直沿袭至今。endprint
在二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安全”问题,出现了大量以普通抗日军民为形象的“抗战门神”,门神形象有了从“求神不如求人”到“求人不如求己”的变化,足以说明门神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衍变”的根本原因——即当公共安全出现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定选取最为民众所接受,最深入人心,最能代表一个民族面对国家民族危难,最具有鲜明道德教化和情感内涵的形象为门神,这是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公共安全意识变迁的共性体现。表面看来是门神形象的改变,实则反映了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因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在精神层面和文化诉求上对“安全”的独特载体——门神进行“随时而变”的必然。因此“……门神画的功能涵义起了质的变化,即门神的身份已由守门看护、防范鬼魅转变为教育人们敬爱国家、反抗侵略,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团结意识……” [4]。
由史可见,历史的发展不断赋予门神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核。门神从“宫门”到“家门”再到“国门”而发展至今,其造型如同其词汇已逐渐成为一种从历史形态中抽离出的具有普适性与共时性同存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蕴含强烈的民族意识,具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共同性和价值观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寄托。其主要根源仍在于它承载着社会各个时期、各阶层民众对“安全”的共同期望。“文化有自己的历史,本身有历史的继承性,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体现在一般所说的‘民族精神上” [6]。门神在中国大地上历劫不衰,以强大的生命力步入信息时代,所依托的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
(二)主题的时代性
文化是人类文明之精华,它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和不断更新提供了养分,因而把握其“主题时代性”,是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需要。门神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形态,析其衍变是对历史纵向的梳理与解读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横向上比较社会中诸多因素的影响。
文化符号所象征的文化精神具有沟通民族成员的普适性和时代性,具有自我维护与统摄能力。门神自产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个民族“公共安全”系统的代表符号,是独特的社会组织化与安全保障系统化的历史文化遗产。虽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因“环境”的不同直接映射出人们对公共安全的解读有同有异,但任何时代背景下的主体意识系统的核心都是公共安全。
20世纪二战时期,面对日寇侵略,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不论是解放区或国统区均有骑马跨刀杀鬼子的“抗战门神”出现,门神在原有消灾辟邪的功能意义上具有了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体现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面,“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新中国门神画的时代主题。手持钢枪、托举钢炉、怀抱麦穗的工农兵形象成为那个时期的门神。这一时期的门神还有由男到女的衍变,传说中的穆桂英、花木兰和现实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性英雄人物也进入门神行列,体现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强烈时代气息;在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使传统门神完全绝迹,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阿庆嫂、严伟才等样板戏中高、大、全、红、光、亮的工农兵形象成为特定时期的门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弘扬和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步伐不断向前推进,随传统文化的回归,秦叔宝、尉迟恭等又站立在百姓的大门前,除辟邪之外,更是表现了为民祈福的愿望;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四川出版社大量印刷“敬爱的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大开国元勋形象的戎装骑马像被千家万户贴在门上成为民众的守护神,并在第6届全国美展上获政府金奖,体现出上下一心,拨乱反正,振兴中华的时代渴求;新时期的门神形象中有了科技工作者和航天英雄,传统门神也高举北京奥运火炬,信息时代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日渐畅达,外来文化中的超人、蝙蝠侠、机器人擎天柱、威震天等也“客走旺家门”,以洋为中用的姿态跻身当下中国门神行列。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有“门神”出现在民众的视野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总是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因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实现着需求与功能的转化,其造型始终体现着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门神之所以能够保留至今,正是特定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相互制约、互补整合的结果。所以,不论以怎样的方式或视角去理解、表达不同时代社会变迁或社会结构调整中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对门神造型的影响,门神文化的精神内涵都可以跨越意识形态和时空,在不同的时代表现着代谢和更迭。因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才是“公共安全”的本质所在。恩格斯说:从已有的历史和正在发展的过程得出确切结论。我们民族创造的门神文化,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还会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元素,为创造新的文化留下与时俱进的基础。
(三)制度的阶级性
文化是制度之基,研究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与门神造型的衍变关系则无法回避“制度的阶级性”问题。
从根本上讲,最初的造型行为是没有阶级性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历史领域活动中的人来支配,人是创造“门神”文化的主体。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其所体现的价值的阶级性和社会属性都是由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特定时空中人们的公共安全意识变迁的反映,凝聚着民族历史、时代特征和特定的制度基元。“从社会学视角理解制度文化往往借助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影响社会的精神力量,因而具有一元性,但作为主要反映精神生活的精神文化则是多元性的”[7]。如神荼、郁垒的最初应用是因统治者权力增强的安全需求。汉代盛行厚葬,墓室门上多见武士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安全需求;秦叔宝,尉迟恭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个人护卫等。沿袭至今,在门神的造型中仍可见封建制度的残留形式。因为文化堕距现象及文化的变迁虽然是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但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又滞后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迁,这就是“传统”形成的原因。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门神”作为一种历史遗留的艺术形式或文化符号,不同历史背景甚至相同历史背景下的人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对它(传统)的态度、应用、解读、评价等都有所不同。因为人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这是客观事实。而“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则是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也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 [9]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章第一条(1982年)。endprint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以不难理解在特定时空中的门神造型为何具有特定制度基元的痕迹。如20世纪50年代的“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人物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农兵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形象等都属于“无产阶级门神”。
进入信息时代,全球化为多元文化主义向跨文化主义嬗变提供了机遇,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可能,但跨文化主义潜在的基元——强势文化造成对不同民族文化特性的蜕变甚至消解的可能性也同时存在。对于一个民族,不是以人种来区分,而是以文化来界定。“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指向,它将为民族的延续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节选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年。
。因而任何一个面对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民族国家,都必须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检视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的安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文化就是保江山。门神造型的制度阶级性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普遍性和一元性的关系以及门神文化自身在时间历程中所显示出的特殊性和多元性的关系。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政治主张与文化战略思想。这从主流意识上确立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促进了门神造型的衍变。如河南省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指导思想,以朱仙镇年画产地为试点,选取历史上在开封任职又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人物,如包拯、范仲淹、寇准、杨继业、海瑞等作为门神创作的选题内容。这种“选取”,从方法学的角度看,一方面,如费孝通所说“任何事物的现代性都能从历史中找到根源”,因此根植民间和现实生活是创作与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遵循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基本要义,任何事物的历史价值,只有经过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得到升华,才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为今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提供精神财富等等。当下这种对门神等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的态度和应用方式仍然体现了特定时空中的制度基元,却表现得更为普适、开放、包容、和谐和充满自信。
门神造型衍变的这种制度痕迹最终会随历史的发展成为一种感官上物的形态而逐渐褪去特定时空中特定意识形态的意义。“当人类进入没有阶级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将随之消失,一些意识形态的形式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但那时还会有意识形态的存在,道德、哲学、艺术等形式还会存在下去,却是无可置疑的”[10]。
(四)发展的动态性
如前所述,门神作为公共安全意识的独特载体,其造型的衍变及普适性应用的文化行为,都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而在精神层面和文化诉求上对“安全”作出独特回应。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与门神造型的衍变二者之间的发生及互动关系则体现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动态发展的内在合力。
在全球化已作为一种国际性语境的塑造与实存的时代背景下,艺术作为人类传承文明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的艺术是完全封闭的或“能够”选择封闭。于是事物的发展具有了不同的社会参照(社会、政治、思想、观念、经济、文化、艺术等)。门神形态本就是特定“环境”的造化物,其文化特质虽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其风格与形式体系及应用方式等在衍变过程中则一脉相承地体现了基于历史、关注时代,同时以新的姿态回应时代的新诉求。
笔者认为,当下对中国门神文化的系列研究,既不是否定传统、脱离传统或者背弃传统,也不是抄袭传统或简单地基于传统来演绎“传统”,而是深植于传统的土壤中,寻觅、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现代意义;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门神文化的现代诠释,努力揭示和把握中国传统门神文化中具有规律性的要素……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基础。对传统文化的基元、表现形态和制作技法等作“现代诠释”的实质,是一种积极的扬弃,是使其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因此,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并与其他系统之间构成依附关系。对中国传统门神的现代诠释,是开放的“兼收并蓄”,并在多元形态的结合中尝试创新的过程。
“中国文化的现代变迁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中国文化的现代变迁将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体系”[11]。在当下,回归传统的门神文化符号在造型形态、应用空间、功能诠释、表现技术、使用方法等方面有了更加广泛的拓展。其造型衍变的多样性以及“功能”的多重性仍体现了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公共安全意识变迁的“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任何一个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民族性即是形式也是内容,时代性即是内容也是形式”[12]。如在现代设计中,门神一改以往威风凛凛、怒目圆瞪的守护家门的保安身份,将手中的鞭、锏、斧、钺等兵器换成了手机电话、奥运火炬、大礼包、聚宝盆等,笑眯眯的表情和脚下踩着健身运动滑板、腰上转着呼啦圈的模样深受民众欢迎;在各类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中门神也成为频繁应用的传统元素,如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的招贴设计、各类特色时尚的旅游纪念品中的Q版门神等;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虚拟社会成为现实社会的延伸,笔者作品“东西南北”将门神符号运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结合美术学的表现手法思考了当前网络安全的社会问题;在新时期的现代美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以门神为素材的原创美术作品,如笔者获国家文化部金奖的“德门积庆”、“民富国强满堂红”等作品,包括当下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门神年画的保护与推新等行为,不论在其造型衍变和应用方式上如何动态,都在需求的“本质”上体现着一个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普适性、群众参与的共建性及解读现行政策的回应性等。充分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热切期望和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构建和谐社会的心声。
从古至今,门神文化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门神”一词的诠释已不仅是单指一种造型艺术形态,作为民族精神的独特载体贯穿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应用范围的边界也在“随时延伸”,对其“功能”的界定与解读已经变得更加丰富。传统门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符号,其衍变还将不断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endprint
三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会出现特殊化,且呈现“特殊进化”与“多线进化”态势,必须承认,文化必须采取自己的环境所要求具备的形态[13]。因此,对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与门神造型的衍变研究,实质上梳理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在横向上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和纵向上递进并连续发展的系统过程。基于门神造型衍变的内核分析,其构建的是一个从特殊性中抽离出的普适性与共性特征,即对生命安全的渴求,反映着一定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轨迹的三维结构:以时间为轴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公共安全意识的变迁门神造型的衍变研究;以空间为基本范畴的门神文化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分析;以特定社会结构且跨越时空抽离了意识形态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意涵的解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14] 始终坚守对中国传统门神做现代性诠释的基本理路、基本取向、基本路径和基本方法,在传统延续中,揭示发展内在规律;在历史积淀中,寻找现实新的启迪;在现代诠释中,彰显主题的时代性;在现代演绎中,校正价值的阶级性;在技法创新中,丰富门神的艺术性。历史给人启示,更给人警示,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改变了世界,从原始的族群安全,到封建社会的对门户安全、生命安全、社会安定的需求,再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对生活富足和长治久安的渴求。可以说,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从未停止,还更大地扩展和延伸了安全的概念和范畴。
在当下社会背景中,深入研究传统门神现代诠释的相关论题需要进一步反思几个深层问题:(1)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交汇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与环境。(2)对传统门神作现代诠释的社会认同如何提高。(3)对传统门神现代诠释应如何市场化。中国门神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创造文化的历史,代表了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中华民族还将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化和书写着灿烂辉煌的历史篇章。参考文献:
[1]陈雄.构建和谐社会公共安全应急机制研究[D].湘潭:湖南师范大学,2009.
[2]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12.
[3]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259.
[4]王树村.中国民间门神艺术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84.5.
[5]唐家路.民间造物艺术的伦理观念[J].山东社会科学,2006(12):132.
[6]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0.
[7]罗玉成,罗万里,论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J].船山学刊,2003(4).
[8]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
[9]戚序.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J].理论学刊,2006(3):3.
[10]陆梅林.何为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论[J].文艺研究,1990(5):5.
[11]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75.
[12]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49.
[13]松原万龟雄.新进化主义[C]//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合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社,1988:179.
[14]费孝通.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R].“社会变迁与现代化”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稿,200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