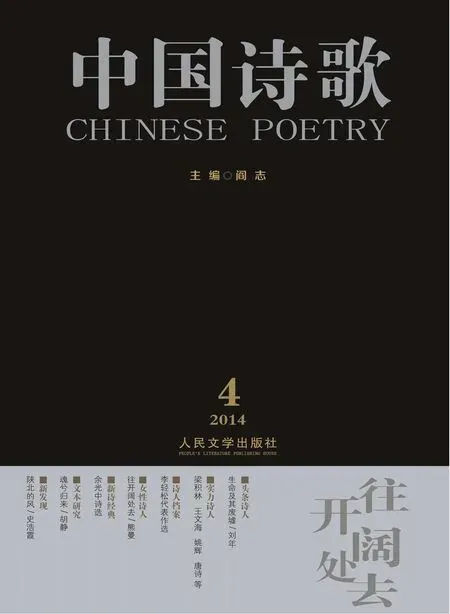诗学观点
□王婉/辑
诗学观点
□王婉/辑
●霍俊明认为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叙事诗学和戏剧性现实的双重影响下,更多的诗人以超强的“细节”和“叙述”能力,对身边的“事物”予以绘声绘色又煞有介事的抒写。这样写作范式的好处可能就是内心找到了客观或虚拟的物象予以对应,其缺陷则是导致了过于贴近原生景观和社会百态的放血和拟真化写作的泛滥。与此同时,这种黏稠的缺乏性情观照和超拔想象力提升的写作方式,正在成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汤养宗近年的诗歌则很少有“事物之诗”的冲动,恰恰相反,他在反方向中走向了智性探险意义上的“迷人深渊”。在他那些大量的自陈、内观、寓言质地又具有深层的与“身体”经验和“个人现实感”发生关联的诗歌话语方式,正在构成他整体诗人形象中最值得探究的部分。汤养宗无异于在“更高的悬崖那里”寻找一种与危险同在的语言方式、精神体操以及带有一定形而上意味的思想平衡术的操练。面对这种“中年智齿”般的智性写作,诗人选择拔掉还是让它继续发挥“特殊癖性”的命运?他希望看到的则是那个长着“第十一个手指”在悬崖边练习危险的倒立、翻腾术和平衡术的“不合常理”的人——如此触目惊心、唏嘘感怀,又有不可思议的僭越者一样的坦然、胆量和冒犯精神。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评2013年〈诗刊〉年度诗选》,《诗刊》2013年12月下半月刊)
●续小强认为写作诗歌的人并不全然可以用诗人的名号来称谓。“诗人”让我们浮想联翩,想起太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和诗歌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它们有可能(这些东西)再次让我们浮想联翩,想起更多的东西(置诗歌于死地的绝坏的隐喻),言语如此疯狂的连绵,让“诗歌”告别诗歌、诗人告别“诗人”。我们不是缺乏语言的想象,也不缺乏想象的语言,我们缺乏的,可能是想象的劳动——不仅想象,而且具体地劳动、扎实地生活,而且是富有想象地劳动、生活;让语言自然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参与精神小屋的建设,压抑其雕饰的欲望和四处游走漂流欲往天堂的企图,用我们的坚韧和耐心磨碎,成为甜蜜的烟丝,是的,这时候你便看到了老农锅里的火光,微弱、轻盈,但是,实在——在生活的温暖的大炕上的这幅情境,可能比花园里玫瑰更容易让他想起诗歌。写作诗歌的人无法确定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他“走路”的姿势那么难看,让造人的上帝都无法不惊奇。一个茫然的“拾垃圾者”,一个自信的盲者。
(《几段过去说过的话》,《名作欣赏》2013年12月号)
●车延高认为诗要有陌生感,诗最怕重复。诗人追求写作风格,就是想让自己成为自己。改动不了一个字,就是自恋。其实不要怕,写就要写出自己的旁门左道。你看另辟蹊径、卓尔不凡、别出心裁、独具匠心这些成语在明示什么?就是要我们从趋同的江湖与山寨中杀奔出来,更旗易帜,另立山头。
(《论诗》,《世界文学评论》2013年第17辑)
●干天全认为对于孕育万物的大自然,诗人和哲学家都会热爱,但两者的认识却是大不相同的。哲学家用逻辑和缜密的理性思维去思考大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依存关系与相互作用,而诗人却用直觉从大自然中获得自由的天性和创作的灵感,将大自然作为自己诗意栖居的精神寓所。《一滴雨和它的反光》这卷诗歌中看似有花草树、四时节令与日月星辰等诸多来自大自然的意象,但大多只是借助自然景物象征寓藏诗人各种情绪及生活感受,而不是对自然现象本身的描写,更不是去表达对自然的科学认识。诗人的自然观与人类的历史文化观、人生价值观、社会现实观是感性地融合在一起的,并以抒情而不是说理的方式,用象征暗示的语言去表达感悟的。
(《诗人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情怀——评〈一滴雨和它的反光〉(自然篇)》,《星星》2013年第12期)
●高平认为《离歌》顾名思义就是作者离离自己的歌,它与《离骚》词义相近,但内容大不相同。它没有怨尤,没有疑惑,没有追问,也没有屈原那样重大的心事和宏大的气魄。《离歌》是脱离虚幻的歌,永离童年的歌,离别父母的歌,离开乡土的歌。其中蕴含的不伤之哀,成为无声的歌,大音希声的歌。离离善于用坦诚的诉说表达深沉的感受,但她并不直说;她能用明朗的语言包裹含蓄的思想,每一首诗即使写到最后也不“卒章显其志”,点出所谓的主题,它们经常是戛然而止,形成无尾之尾,达到余音绕梁、余味无穷的效果。这真是一种本事,也是她的风格。
(《劝君听离歌——读离离的诗集〈离歌〉》,《飞天》2013年第12期)
●施勇猛认为所谓诗歌对于他,就是这样,他所经历过的,所能想到的,把它写出来,这样,人生的忧郁和孤独,就会忘记,他就会开心,就让所谓的诗歌帮他记着,或者忘了,就由它吧。在这个朋友、爱情都需要验证的年代,我们还有多少东西可以信任永久,可以忠贞不渝,可以无畏付出?活在这世上,生命是一种过渡,一次灿烂绚丽的绽放,又何必用什么来证明我们的存在。诗也如此,它无法证明什么。诗火热冰冷,孤独无情,诗是一种轨迹,心灵轨迹,一种证明心灵曾经存在的方法,仅此而已。正如他看见的一只飞虫,飞得缓慢的时候,我们都有杀了它的想法。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在人间往往被漠视。正如我们,在时间,在距离,在人心里,也许也飞得缓慢,飞得那样细微,细到无声,细到看不见自己在飞。我们就是这样,以为走在人间,其实已飞出人心。所谓的诗歌,是我们心灵世界的错误,是变异,是一切美好一切丑恶,一切我们想忘却忘不了的事。诗本身没有对错,错的是我们。我们相信永远,相信美好,相信堆砌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但就是忘了谁会相信我们,我们还能相信谁。
(《诗的外衣》,《福建文学》2013年第12期)
●汪余礼认为,“学人之诗”不限于传情,而是更多地关涉到人生经验、深沉思想、高级智慧的表达。如果把二十世纪中国一流学者的诗集中在一起,从中几乎可以看到一部隐性的、微型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这意味着“学人之诗”并非不入流的外行之作,而是需要以新的审美眼光、评论标准来看待的一种诗歌现象。
(《对“学人之诗”的深度透视》,《世界文学评论》2013年第17辑)
●郑成志认为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诗歌继续在“个人化写作”的道路上探索和分化。然而,当下的中国新诗尽管在“个人化写作”的道路上延续和深化,但是它并未真正走向“私人化”、走向自我的狭窄的空间,去浅唱低吟一己的欢乐和幸福或悲伤和不幸,而是在当下中国历史的宏大语境下,置身于中国现代性寻求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当下的中国诗人更多的是通过自我的意识、感觉和个体的经验,一方面试图重建诗歌与当下中国现实对话的平台,从而缝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争论出现的裂痕,另一方面诗人们又企望通过个体的感觉和经验,呈现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造成的个体与时代、自我与他者之间纠缠迎拒的复杂关系,从而彰显个人在宏大历史下被遮蔽的、被压抑的为意识形态所忽略的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诗人和诗歌对什么负责——对新世纪底层诗歌的一种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6期)
●王晓梦认为最理解生命的人,也许最善于在我们最真实的生活中挖掘那深厚而辽远的沉思。就如野川的这组诗,已是生命定格的蝴蝶标本,为树木修饰生命的啄木鸟,揉碎在风里的花,以及其他物象,都在生命的水墨里展开,时间之内,时间之外,人与自然,如水般流逝,如梦般虚幻。而生命、生存、生死也就在这样的点滴中被诗人升华为深度的哲思。而更深邃的感情世界里,诗人正在召唤我们一起去追寻“身体和灵魂畅通无阻”的终极意义:我们的一生/其实只是在回复,把失去的东西/一一擦亮,让它们闪烁/最初的光泽。
(《〈野川的诗〉点评》,《山东文学》2013年12月上半月刊)
●李瑛认为朱增泉用沉郁凝重的笔触,把地球面临的危机凝聚成对人类、对未来的思虑,他挖掘苦难的本源,他的忧患意识超越了种族、地理、国家、民族而成为对整个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共同的叩问。这不是表面化的、浅层次的抒情,而是形象的、有着深沉厚重的力量的。地球是一只“泪眼”,这形象给人以巨大的震撼,是对当今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概括,显示出了诗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应该说是个人的力量,就是诗人人格的力量。增泉同志的诗中,有很多带有这种哲理意味的警句,哲学的思辨已成为他表现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诗中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尽管诗歌创作是属于感情领域里的形象思维活动,但决不能摒除理性的思考。要知道,深刻的思想会带来深刻的感觉。正如庞德所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诗人在生活中,应更多和更敏锐地关注国家和人民中间的大事,使读者能从诗作中透视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透视出社会情绪,这样才能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从而有助于人们的心灵建设和社会进步。
(《以生命歌唱大美》,《解放军文艺》2013年第11期)
●朱霄华认为随着整体主义时代的终结和甚嚣尘上的现代主义对古典时代和大地的毁灭性颠覆,诗人何为?或者说“何为终极之诗?”——这个问题仍然难以在80后一代年轻诗人的书写中找到答案。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栖居于大地”的普世理想,究竟很难在人类荒芜的后院里落地生根。究其原因,人的存在的整体感的丧失是在人类被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集体诱入现代之后,一旦进入现代,人的主体性便即被抽离、缺席,显得支离破碎,身首异处,个体的人沦为工具时代的拥趸,“思想的疾病”俄尔转化成“身体的疾病”,所谓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此一时代,诗人当如何面对自己的写作?又如何经由写作来完成身体性的救赎?他以为,这几乎就是一个天问式的悖问。
(《零时代的身体叙事与身份书写》,《滇池》2014年第1期)
●朱春生认为好的诗歌,首先是一种纯粹。纯粹的感情,纯粹的意蕴,纯粹的思想。当然,所谓的纯粹,并不是单纯的为写诗而写诗,毕竟诗歌是如今四大文体之一,它也和小说、戏剧、散文一样,需要自身的写作技巧,甚至诗的写作技巧与小说、戏剧、散文都是相通的。如果有人可以游刃有余地在这四种文体中行走,相信他写出来的诗会比一般诗人的诗更胜一筹。其次,诗歌是一种自言自语的笔画。诗歌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感情,而每一个人都具有充沛的感情,从这个角度分析,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诗人了,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成了著名诗人,更不是所有诗人的著作都得到认可。所以,他强调了感情,却还是需要一种表述技巧。第三,诗歌是使人们向外界表述自己内心的一个媒介。诗人们写出了诗歌,其目的在于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一首好诗,总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一首好诗,总会使读者了解诗人的现状。但是,这个媒介总会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从绘画的角度分析,这就是留白。不同的人会涌现不同的情感。
(《2013:河北青年诗观》,《诗选刊》2013年第10期)
●胡弦认为乡村如此简单,但又是个情感的迷宫,让人无法从中走出来,这是情感记忆的力量所在。虽然现在的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某首诗来说,这种变化简直不值一提。不过,回忆或怀念,终究是站在今天的立场解释过去,其中,不自觉地会有戏剧化的成分,有时候,我们认为的那种记忆,甚至只是与记忆并排着的其他东西。诗人首先要从内心里说服自己,保证说出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要掂量这样一种事实:你突然明白过来,你不可能再回到那里,你在朝相反的方向走,那么,你和那些浮光掠影的书写者的区别在哪里?在这里最难的是在书写中做到自然。落日、山冈、村庄、流水……就像亲情一样自然。它们不需要启示、感悟,它们是无限的,不管怎样诠释,里面总包含着太多的未知。当诗歌中的亲人也已成为许多人的复合体时,写作像回忆某个梦境,并不自觉地对那梦境进行修补,这中间,想象力和某种存在已久的愿望在参与,克制的白描也会释放出梦魇般的力量,操控我们的感情。写作,一种真诚的回声重新寻找我们的听觉,并试图替我们这个糟糕的时代挽回一点声誉。
(《关于乡村记忆及写作》,《青年作家》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