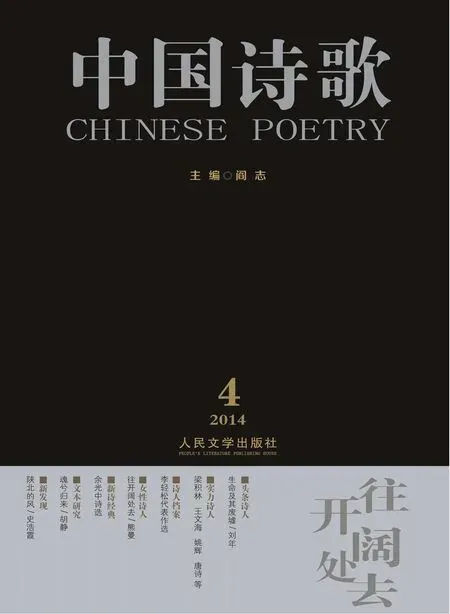余光中新诗导读
□桂延松 邹惟山
余光中新诗导读
□桂延松 邹惟山
作为当代中国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余光中以独立的两岸(大陆和台湾)地缘身份、独特的诗歌写作形式以及深刻的思想内容,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历史并没有预言一位诗人的诞生,却一再地证明了一位诗人的存在。当他的作品一发表,就拥有了众多的读者,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台湾本岛,还是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他的诗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台湾有许多一流的诗人,余光中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者之一。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南京,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动荡的岁月里度过的。抗战时期,他随母亲流寓到了四川重庆,在那里度过了艰辛而难忘的八年时光。抗战结束后,他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和厦门大学,1949年5月又去到了孤岛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余光中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赴美进修留学,获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高雄中山大学任教多年,在教学之余坚持写作,成就最高的是诗歌、散文、评论与翻译,可以说是左右开弓、上下齐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文学奇才。我们相信,余光中先生并不只是属于台湾,也并不只是属于海外,他与他的诗文属于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同时也属于整个世界。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余光中及其诗歌,才会有比较准确与科学的评价。的确,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其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整个诗坛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而后回归民族传统。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七十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这正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亦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八十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下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的浪子”。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余光中的诗歌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受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其诗歌艺术的发展轨迹虽然存在先西化后回归的倾向,却并不能说明他对中西文学的整体态度,只能说明他的诗歌艺术是多变的、丰富的与发展的,并且到了九十年代以至于近些年来,他也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
1
诗人首先还要是一位思想家,他要有自己观察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角度,并且有自己认识问题的路径与方法。正是因此,余光中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是多种多样和丰富复杂的,这正是一位大诗人所拥有的基本条件。他写诗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并且在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都从事过写作,人生的青年、中年与老年都与其诗路历程存在密切的关联,所以其诗歌题材相当广泛,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的、自然的、东方的、西方的、自我的、哲学的、宗教的,他都有所涉猎,并且总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深刻与精致。从总体上来说,其诗歌的独到的思想情感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一位诗人的身份所抒发的对中国大陆故土的怀念,具有一种深切的故国情怀。余光中本是出生于柔语声中多水桥的秀美江南,然而却降临于灾难深重、家国多难的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时刻。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浓烟还没散尽,日军的铁蹄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在东北肆虐,军阀割据,内战频繁,本有擎天大柱的中华民族摇摇欲坠。从9岁那年开始,余光中就只能咽下“国破山河碎”的苦涩,尝到了当“亡国奴”的痛苦滋味。自小开始的到处逃难的仓皇岁月及其苦难,深深烙印在余光中童年时代的记忆中。抗战一开始,诗人就随自己的母亲流寓于重庆,并在那里度过了中学时代。在这艰辛难忘的八年中,诗人把童真的记忆深锁在那一个山之国度里。抗战胜利,诗人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这一次的重返,谁知又很快成了又一次逃亡的开始。内战的硝烟弥漫,让读了一个半学期的诗人又逃至厦门,并且很快就来到了孤岛台湾。到了台湾以后,他身处那样一个小岛,正如诗人自己所说,那里“既非异国,亦非故土”(《忘川》)。回头看历史,在那样一场惨烈的政治争斗中,几百万人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大陆,而全家或者个人漂泊到了孤岛,必然产生一种寄生异地的无根者悲戚。一道浅浅的海峡,横亘在台湾与大陆中间,像一把无情的蓝刀,就这样把余光中的生命剖成了两半。有家难归、有乡难回,余光中将这种处境与痛楚化作了对大陆的山川风物、童年往事、亲人故土的深深眷恋。于是,他以一行行真切的文字,演绎着浓浓的乡愁,使人意动神摇,让许多读者也同他一起经历了大陆与台湾的分离,身心一直处于一种撕裂的痛苦之中。正是这种背井离乡的境遇,注定了诗人对大陆、亲人、故土的眷恋,由此对祖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理念的依恋,变得更加浓烈而持久。因此,在诗人余光中的内心深处,一直浸润着一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割舍的、深厚无比的“乡愁”情结。这种情感的郁结,实际上已经成为余光中几十年诗歌创作中萦绕不去的潜在心理动因,成为他乡愁诗创作深厚不竭的动力。《乡愁》就是余光中故国情结的生动体现,凝聚了余光中一生的感情体验和一个民族一个世纪的血泪沧桑。据说这首诗是他在厦门街的旧居面前,仅用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就一挥而就的。“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在《乡愁》中,邮票和船票是一种纽带,它们将母亲、新娘与“我”联结在一起,这时候的乡愁是带着思念和期待的;而坟墓和海峡却是一种残酷的现实存在,坟墓将母亲与“我”分隔开,海峡将台湾和大陆隔离开,这时候的乡愁是带着无限的痛苦和深深的无奈的。对于乡愁,诗人不仅仅看作一种对故乡的思念,而且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那故乡也不只是某种形而下的地理概念,乃是体现了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以及人生的一种永恒归宿。在诗人的身上,不仅仅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而且回荡着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之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身处那一座小岛,诗人的心却一直游弋在曾经生活过的巴山蜀水,以及少年时代眼里的杏花春雨江南。诗人多次用“母亲”和“妻子”意象来隐喻大陆和海岛。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说:“流亡到台湾的第二代作家,他们成长的主要岁月在台度过,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歧异,不管他们的本籍相隔多远,其内心同被一件历史事实所塑模:他们全与乡土脱了节,被逼离乡背井,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注定寄生异地的陌生环境。”(白先勇:《第六支手指》,台湾尔雅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对余光中而言,对中华民族的孺慕之情,对华夏山水的赤诚热爱,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对于过去生活的回顾追忆,是真正的宿命,是谁都无法更改的一种价值选择。同时,他将对大陆故土的思念与对母亲的思念相结合,赋予“母亲”以更深的情感内涵。在《当我死时》中有“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一句,余光中用“最母亲”三字来形容自己的祖国,这正是一位诗人的创造。把中国最具有母亲的性质、诗人和中国的关系如同母子、爱中国如同爱母亲等繁复意义,浓缩在一个当作形容词用的名词“母亲”身上,这既是一种血缘意义上的认可,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这是对母体文化的归依感的体现,集中体现了余光中乡愁诗的深层内涵。
二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怀。在余光中的许多诗作中,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那种认同,体现在诗人对历史文化中人、事、物的细致描写上。在《寻李白》一诗的副标题“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中,就已经表明了诗人对李白人格及其诗歌特点的根本认识,一个“寻”字就将诗人与李白的历史空间距离拉近了,诗人寻找的既是李白,也是李白诗中存在的那种盛唐气象。在这首诗中,诗人把李白的狂傲不逊、才华横溢写得淋漓尽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样的诗行,也许是现代诗中描写李白最有气势的诗句之一吧?此外,余光中诗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怀,往往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古与今的对话。在余光中诗中常能感受到古今对话的氛围,诗人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时空限制,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既是对古人的一种认同,也是对现在时空的一种感怀。在《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一诗中,诗人以第二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写与醉酒之后的李白同游,带着调侃的语气描写大诗人的车子如何驾驶、超速,却又时时穿插着文化的内涵,让人不禁赞叹诗人丰富的想象力。“高力士和议员们全都得罪光了/贺知章又不在,看谁来保你?”诗人还从李白的生平经历出发,对李白的人生行迹进行了一番调侃;“等《行路难》和《蜀道难》的官司/都打赢了之后,版税到手/再还我好了:也真是不公平”,“要不是王维一早去参加/辋川污染的座谈会/我们原该/搭他的老爷车回屏东去的”。在这里,诗人将古代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既显幽默,又内涵丰富,同时寄予着诗人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在《白玉苦瓜》一诗中,诗人以“苦瓜”象征丰富的文化传统,意蕴相当深厚。它象征艺术品,象征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传统,浓缩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苦难史,表达了对祖国文化、对祖国母亲深挚的爱,融合了深沉宏阔的历史感,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哲理情思。“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是全诗的精髓,是诗之魂。夏志清曾经指出:“他不断重温自己童年的回忆,不断憧憬在古典文学中得来有关祖国河山的壮丽,历史上的伟大,以保持自我的清醒与民族的意识。”(夏志清:《怀国与乡愁的延续》,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86页)虽然诗人在青年时代就离开了大陆,但他就像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心中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追忆着大陆,最让他不能忘怀的,就是祖国的人民、古老的山川、深厚的历史与精深的文化,因为他自己正是在这样一条长河里出来的,并且也始终处于这条长河之中。
三是对美好爱情的种种期许。在余光中的众多诗歌作品中,描写爱情的诗可谓独树一帜,它们清新中带着淡雅,饱含着美好的情感。余光中对于爱情有自己独到的理解:“真正的爱情予人上升的感觉……在爱情的表现上,恐怕东方古典式的含蓄远比西方浪漫式的坦陈要耐人寻味得多。”(余光中:《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谈谈中国现代诗的前途》,《余光中谈诗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10月,第87—99页) 在《等你,在雨中》一诗里,诗人将温暖的爱意串联在诗句里,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永恒,刹那,刹那,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等你,在刹那,在永恒”。诗人通过“等你”这个状态性的词语,用短短的诗行将爱意表露无遗。在《下次的约会》一诗中,诗人巧妙地编制了一个副标题:“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就将一对恋人离别时的感情集中深入地抒写了出来。“下次的约会在何处,在何处?/你说呢,你说,我依你/(你可相信轮回,你可相信?)/死亡的黑袖挡住,我看不清楚,可是/嗯,我听见了,我一定去”。正是在这样的诗句中,诗人展现出了东方爱情古典式的含蓄,对于下次约会的期许,也是对未来美好爱情的一种期待,即使有“死亡的黑袖挡住”,对爱情的追求还是会继续,这正是对个体生命真情的一种流露和感悟。在西方,爱情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没有杰出的爱情诗的诗人,往往不被看作是伟大的诗人,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意见,余光中也许对此深知,所以他在爱情诗写作上用力甚多,并且成效显著。
余光中的诗歌并不只是关注乡愁、文化与爱情三大主题,然而他比较集中地思考与探索与此相关的三个方面,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因此,我们看到了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表达乡愁、认识文化与表现真挚爱情的作品,形成了三个大的系列,并且成为他最杰出的一批诗篇。比如说《乡愁》、《乡愁四韵》、《民歌》就形成了乡愁系列。一位杰出的诗人在题材上还是要有自己的追求,不可今天写这、明天写那,不集中也许就不深入,没有讲究也许就没有特点。一位诗人如果过于随意地进行写作,没有自己的讲究与追求,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对诗歌艺术的不尊重。当然,余光中的诗歌是丰富而多样的,在题材与主题上也同样是如此。乡愁、文化与爱情只是我们根据其诗歌作品的总体情况而作的一种概括,然而这种概括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
2
余光中诗歌在艺术上有自己独到的追求,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许多诗中充满着一种少有的具象之美。诗人往往以意象呈现的方式,使得许多诗歌中充满着一种具象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不禁让人赞叹。余光中擅长锤炼动词,能以富于动态美感的语言,刻画事物动态之象。如《寻李白》一诗中的诗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吐”是一种经常性的动作,“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就在漫不经心之间,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效果,以此得见李白的才情。余光中除了善于捕捉静物的动感之外,也擅长表现活动中的事物,如《桂子山问月》中的诗句,“千株晚桂徐吐的清芬/沁入肺腑贪馋的深处/应是高贵的秋之魂魄/一缕缥缈,来附我凡身”,“徐吐”将桂花清幽而不浓腻的香气描写出来,以桂花散发香气的动作,引发了人们无限的遐想,而“沁入”、“附我凡身”这样的用词,又更深刻地写出了桂花对诗人内心深处的深刻影响,“沁”和“附”将月夜赏桂花的所有感觉都写了出来。“西顾荆州,唉,关羽已失守/东眺赤壁,坡公正夜游/听,大江浩荡隐隐在过境/正弹着三峡,鼓着洞庭”,诗人以这样的诗句写出了长江浩瀚的气势,“弹着”和“鼓着”两个动词的使用,让整首诗极具画面感和强大的震撼力。“徐吐”、“沁入”、“弹着”、“鼓着”等动词的运用都恰到好处,充满着弹力与动感,让桂子山的宁静和诗人内心的思想的跳动形成了强烈对比,让全诗充满着种种具象之美。
二是独特的语言结构。余光中诗歌的语言繁复善变,他一直力求“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红色的丹来。余光中认为诗歌的语言是要有弹性的、富有表现力的:“我理想中的新诗的语言,是以白话为骨干,以适度的欧化及文言句法为调剂的新的综合语言。只要配合得当,这种新语言是很有弹性的。”(余光中:《现代诗的节奏》,香港,文艺书屋,1975年,第55—56页)余光中有意识地引文入诗,其散文家气质使得诗歌创作具有散文的特点,具有了强大的表现力,“以文为诗”的探索既使其诗歌雅俗共赏,也为中国诗歌的语言表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在《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中,“刚才在店里你应该少喝几杯的/进口的威士忌不比鲁酒/太烈了,要怪那汪伦/摆什么阔呢,尽叫胡姬/一遍又一遍向杯里乱斟/你应该听医生的劝告,别听汪伦/肝硬化,昨天报上不是说/已升级为第七号杀手了么?/刚杀了一位武侠名家/你一直说要求仙,求侠/是昆仑太远了,就近向你的酒瓶/去寻找邋遢侠和糊涂仙吗?”诗人以如此散文化的语言写诗,使得这样的诗句幽默而不失韵味。同时,余光中十分注重语言的音乐性,在《〈白玉苦瓜〉后记》中,他认为诗人需要有一只敏感的耳朵,音调之高低,节奏之舒疾,句法之长短,语气之正反顺逆,必须常加试验,并且善为把握。在诗集《白玉苦瓜》中,和“歌”有关的作品将近十首,《乡愁四韵》便是音乐家戴洪轩要求余光中写的,在这里余光中将诗和音乐充分地结合起来,才创造出了这首杰出的诗歌。“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每一小节都是首句和尾句重复,于是让全诗产生了一种回环之美,适应了音乐演唱的习惯。诗人十分注重进入诗中的每一个词,研究它们的音质、音声以及在诗中可能形成的抑扬顿挫,产生一种呼应变化的音响效果。他偏向于用象声词,如《风铃》一诗,“我的心是七层塔檐上悬挂的风铃/叮咛叮咛咛”,音响感很强。“双声叠韵”也被他运用得十分精妙:“你立在风中,裙也翩翩,发也翩翩”(《下次的约会》)。诗人还从丰富多彩的日常口语中提炼升华诗语,因此,常常别有一种现代口语的美感光辉。
三是多样化的诗体形式。余光中确实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转益多师的创作态度,让他能很好地吸收东西方诗歌传统的精华,在处理不同的题材时,更是能够运用自如。其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软。在《〈莲的联想〉后记》一文中,诗人提倡古典与现代的结合,认为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弹性。在《莲的联想》一诗中,无论是文白的相互浮雕、单轨句法和双轨句法的对比,还是工整的分段和不规则的分行之间的变化,都说明了诗人的独特追求。感情甚至是浪漫的,却约束在古典的清远和均衡之中,它们之间也许是一种矛盾,却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在《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中,诗人成功地运用了“戏剧化独白”手法。黄维 在《诗中异品:戏剧化独白》一文中,认为“戏剧化独白是诗中异品”,而“戏剧化独白的特色,是冶诗与戏剧于一炉。既是诗,它具有诗的精炼经济;又是戏剧,它具有戏剧的故事性和生动真实”。古今虚实交融,现代感更加凸现,想象也更加丰富,除了把诗仙嗜酒豪迈写出来之外,还触及多种多样的社会问题。诗人用超现实的笔法,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这几年交通意外的统计/不下于安史之乱的伤亡”、“诗人的形象已经够坏了/批评家和警察同样不留情/身份证上,是可疑的‘无业’/别再提什么谪不谪仙”、“高力士和议员们全都得罪光了/贺知章又不在,看谁来保你?”“出版法哪像交通规则/天天这样严重地执行?/要不是王维一早去参加/辋川污染的座谈会/我们原该/搭他的老爷车回屏东去的”。诗人对于历史的批判、对于现实的讽刺和对于世道诗运的感慨,都包括在了这样的诗行中。他的诗以自由体为主,早年的长诗《天狼星》就是西方自由体诗的典范,而在六七十年代创作的系列作品,则比较讲究对偶与押韵,节与节、行与行之间的相对性存在,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式更加接近,有的就是古典绝句的扩大如《乡愁》,有的是古典律诗的化用如《民歌》,而《等你,在雨中》则是对宋词的一种景仰,长长短短的句式拼合起来,也具有一种古典的韵致,语言上与古典诗歌有同样的讲究。后期的《桂子山问月》在体式上是高度自由的,既不分节,也不押韵,然而却有深广的境界与深长的意味。
余光中的诗歌在艺术上形成自己的特点,与他对于诗意的讲究、语言的讲究、体式的讲究是有关系的。然而,他的诗在艺术上的追求绝不只是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因为他的个性与风格太独特,并且丰富多样、五彩缤纷,不是一篇短文能够概括得了的。
3
余光中是二十世纪中国少有的学者型的诗人之一,被文学史家尊称为台湾诗坛的“祭酒”。因此,我们对他诗歌作品的评论,再高似乎也不过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所有的诗作都是有其来历的。综观余光中诗歌创作的历程,由早期上承“新月派”的浪漫抒情,到后来先西化后回归民族传统,大量的诗作题材广泛,一再地说明了他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从中国到国际,复从国际返回民族文化的大陆;从现实而历史文化,从“联想”、“梦”到“年代”、“地理”等等,无所不包的诗歌丰富性。其艺术手段从传统(中国的、西方的)而现代,又从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而到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他的诗作无不作了范围广阔的尝试。如果我们用“博大精深”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余光中的诗歌,一点也不会过分,因为他对于古今中外的诗歌、文学与文化都有广泛的涉猎,并且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将所有外在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的东西,从而成就了余光中诗歌的个性与风采。
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有着不容抹煞的传承性。对于余光中而言,传统渗透在其血液中,但朴素的感情代替不了语言的自觉。对诗歌传统文化的甄别、取舍和融化,是一个复杂细致的过程,任何轻率浮躁的态度,都不可能深入这一过程。余光中在几十年的艺术探索中,注重并善于汲取古典诗词的艺术特长,保持诗的艺术内涵和审美形式的民族特色。其历久不衰的“乡愁诗”,更是母语和本土文化的情结的直接体现。现代母语情结,是现代语言之子眷念和追认母语的记录。难能可贵的是,余光中能够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叉点上:一方面珍惜母体的诗和文化的历史,另一方面又站在现代的高度进行重新审视;一方面能够面向世界,接受人类现代意识和现代科学艺术,另一方面又立足本土,不断激活母语和文化语境;一方面以宽宏的眼光,接纳和吸取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另一方面又与中国诗歌传统艺术相融汇,创造出新的既现代又有民族审美特征的汉语诗歌;一方面顺应世界进步诗学和文化潮流,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传统诗艺引向新生和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余光中的诗与他的散文、文学评论一样,是一种多样化与丰富性的存在,这正是他与许多当代中国诗人的区别所在。有的诗人只接受北方民歌,有的诗人只接受西方现代,有的诗人只接受古典诗词,而余光中与他前辈诗人望舒先生一样,能够在多种多样的文学传统中,勇于进取,独树一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位杰出诗人的产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是有他的时代、环境、文化以及个人的原因。正是两岸分离的地理、人文环境和余光中独特的成长背景、人生经历,塑造了余光中诗歌的内在品格。在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诗人又接通了通往西方文化艺术的途径,使得其诗融汇古今、贯通中外。“乡愁”诗奏响了他诗歌的主旋律,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诗人借用了中国古代诗词传统的联想、象征手法,但在构思、意象、节奏变化上,明显地受西方诗歌及音乐的影响,显得丰富多彩。如果没有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流浪生活,如果没有孤处小岛的两岸分离,如果没有古典文学的根基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流行,如果没有美国的求学与台港两地的教学生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开始的世界各地的讲学与交流,也许他的诗是另一种模样、另一种风韵。自我、时代与文化,古典、现代与中国,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让他成为了我们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可以和二十世纪早期的艾青、戴望舒,后期的舒婷等相提并论,并且还有过人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余光中的大部分著名诗作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正好是中国大陆的诗歌处于退潮期,他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种缺失。当然,还有洛夫、纪弦、罗门、钟鼎文等台湾诗人也和他一样,起到了这种弥补缺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