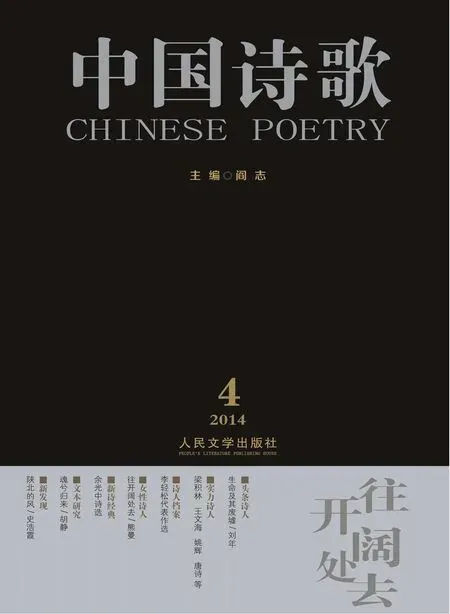李轻松代表作选
悬 瞳
如果我能够追想 这一次的知遇
像冬日的月儿一样薄而脆弱
像冬日的月儿一样白而易碎
那么我呼吸的风已袅袅飞散
这印花的被子与我的皮肤这么相称
一种恋旧的结 类似一条藤蔓
你环绕的双手一样缠紧我 并在我心的
背面。在灵魂最阴暗的一隅
翻检我陈年的旧物
这时你宽衣的声音簌簌响起
一声喘息都能使我瘫软。请望定我!
让我看看你瞳仁里闪亮的火苗
看看火苗中游移的阴影。请望定我!
这比水还清白的身体
最初怎样给你?如果你要——
现在怎样给你?只要你要。
在你墙上的壁画中看到死鱼的眼睛
一种空洞。一种悬浮的洞——
无着且无落。以及被打碎的陶片
如此尖锐。流血的快感
你用身体作炭
在燃烧的火与仇视中
把女人焚毁的同时先把自己焚毁
这本身充满了意义
你最初的情人,最后的母亲
都必将是我。在这临时的天堂中穿行
像穿行在你的指缝和牢房中
无法呼救。一个因爱而被囚的女兽
类似于谁?你此生再也不会遭遇!
樱桃!樱桃!
我是这样地用尽了自己
——题记
不仅是一种假设,不仅开花
你荒凉的生存 是叶子 又是人
这些树上的樱花 使我隐讳
一个整体或一团火焰的心灵
是黑色 黑色的眼睛与觉醒
一如我肤色的智慧与脆弱
一个盲诗人的歌咏:是大师,又是面具
什么与五月如此相关?樱桃!
这五月万物的金箔
它落下,比红还紫
比紫还深 比白色更不安
金箔的五月的鲜花 樱桃之外
这质感的嘴唇与果肉
这充足的雨水与乳汁
我是这样地用尽了自己
一个果实丰富我一生
现在你低下头
仿佛不曾存在 不曾是我
在落英中的堕落
你是大师,又是面具
我是无数樱桃仁中的一个
谁比我更芬芳?羸弱?
这首诗中提到一朵花
不过是一枚首饰,一个金箔
五月万物的金箔
它落下,比白还浅
比灰还灰……
碎 心
把这层卑劣的外衣撕掉,亲爱的!
在我还没有心碎之前
让我的爱情触摸到你的嘴唇
这是我一贯的姿势。在一个人面前
废墟一样虚无;在一个形容里
春天一样昏厥;在一个声音里
你是吹向我生命中的血
多么迷幻啊!一棵树裹在风里
与一个人裹在身体里一样
被什么疯狂地摇动、与占有
直到每个枝丫都爆出骨朵
直到我昏迷。像你见过的某个死者
她离弃了肉体的精神,依然在飞
这是什么地方?我在与谁相爱?
我自身中最堕落的部分
为什么瞬间站在了高处?
我一身仇视的欲望,为什么
美到了极致,或极致以外?
这个冬天,我丢弃了书籍与文字
这个冬天,我所能做的
就是想你或爱你
许多年来,我无言的躯体
被生活的外衣包裹得过分平静
一只猛兽,它混迹于恭良的羔羊之中
它噬血的本性,在炭火的底层醒着
没有谁没有什么能够把它催眠
我过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什么?
我的笑颜,被有毒的灯盏混淆
一些岁月的桃子皲裂、破溃
直至血汁四溅。我不能爱
我腐烂得快要死掉!
不能哭,就像一个濒危的人
被内心的野兽舔净了泪水
血中的白骨,以及骨头中的精髓
就这样,我坐在冬天里最后的日子里
把我曾经破碎的诗歌拿来
与我曾经破碎的心放在一起
让你看到:一种爱与死。
宿命的女人与鹿
这幽闭而蜷曲的河蚌,我将对谁展开?
双手解开河面的微风
我裸露到什么程度,才能了解
我自己的珍珠,是不是沙石
因为缺少刀痕,我取不出肉体里的针芒
那腐烂的气味飘走了羊的腥膻
让我看到纯粹的疼痛,不知沉迷在哪儿。
也许,我只有一条缝隙可以通过
刀或者精气的海:“剪开还是淹没”
我还在不在,是不是一个人?
这被生育铰碎的身体,曾经空着
像离开海水的鱼,空有一身鱼皮
我惊悸的手不敢露出
有一滴水落在胎儿的身上,我体内的胎儿
紧裹在秘密的囊里,像苞蕾中的苞蕾
眼睛里的眼睛。她惊吓的蕊一动不动
我被什么取回,放在胎心的上方
聆听我骨骼深处的撕裂声
从此我将是另一个人,一块碎骨
蜂针里的蜜或毒,以及
羊皮里的羊
还有我孕育的生命,与我酷似的
一个婴儿或奇迹
她内心充满我的空洞与针芒
像我一样辗转,钟声穿过
更爱自己的红颜与血水
这一只怀孕的母鹿,有没有怜悯
一位年老的族长祷告:
给她象牙,用朱鹭的羽毛遮住
她以不反抗来顺从灭绝
一个女人或一只母鹿的一生
是猎人使她们倒下
血光中有什么离开母亲的尸体
大地的精神和天空远逝
这是一个女人或一只鹿的宿命
陌生人之恋
陌生人,我只爱你,爱你冷漠的眼神
爱你的拒绝。我和你,隔着不仅是两棵树的距离
肉体的距离。还有左边的盆花,右边的水壶
陌生人,此刻我只爱你。爱你脸上的疤痕
好像找到了世界的出口。据说台风就要来袭
风力十二级,我从未如此地渴望过暴力
霸权。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快感
鱼和水分居。我与世界分居
今晚我们谈到了需要,就像谈到食物和水
香气弥漫起来……陌生人,而我与你彼此无关
与天气、道德、世界无关。我只信任我的触觉
像从巴黎的鳞爪中分辨出手
是黄昏使我患病,天色一晚
我就急于表白。暴露自己的虚弱
用越来越悲观的口吻说起
第一次死于疯狂,第二次死于忧郁
第三次死于怀疑
陌生人,我爱你的紧闭,你抚摸的深度
我从来不曾到达。我们失掉身份
便打开了所有的穴位
只剩下水分发声。爱情退到了后面
那些陌生的事物,学会了观望
闪烁。并用自身的韵律歌唱
锈是可以传染的
我说过,我爱那些被遮蔽的部分
那张满是锈迹的脸,有些失传
我越来越擅于生锈
就像擅于生育。从腐蚀中透析出铁
从铁中炼成钢。
金属、黄金和白银构成了今日行情
我的身体症候。暖涡气流一路北上
而西伯利亚寒流也已袭来
我被夹在中间,冷暖自知。
一些雀斑像旧时光。需要重新锻打
我和我新鲜的女儿,需要重新出生。
我被锈死的灯,低下头
在胸口之间寻找首都
一种亡国的气息。
锈的萎靡气息。它是一个君王
洞庭花犹在隔岸
腐烂却在内心。我们最后的晚餐。
指甲花做的花瓣饭。一道蛋花
还有西芹百合这样的尤物
都被锈腐蚀。
在头发上涂榆树油
那时我还擅长奔跑
膝盖上留有的伤疤像个月牙
我已成为前朝岁月的遗民
用做爱来还原爱,用牺牲来还原生
众仙降临
一声古朴的唱腔,仿佛穿越了时空
万物都屏住了呼吸。疾走的亡灵停下
你们只是一个转身。便是广大的世界
在一片树叶上,一声叹息里
或在水波里、在荷尖、在时光的消失里
你们是歌舞而来还是云雾而来?
快让我用仪式之美再次相邀吧!
我不用花草相迎,更不用香火
也不必跪拜。便已是心醉神迷
你们的恩泽遍布。我也恍惚在飞
对每一个生灵都怀有敬畏
做仙也有做人的性格,我已了然
形而上做仙,形而下做人
中间的部分无师自通,或有灵有犀
神通广大啊!我预先打开了身体
才能打通精神。接受未知的部分
我要鼓乐加冕,认那棵老榆树为亲
她不美,有点老,但却迷人
让石头也开花。快把那些妖魔驱散吧!
所有的冤魂都有了救
我披挂满头,歌唱这不幸中的万幸
左边的事物
左边的事物都是明亮的
先是我左手的指甲,排列着太阳的光谱
我在风中一亮,便有了激进的翅膀
我的左耳蜗擅于分辨杂音
八方的尘埃与人民,都深积于此
悲悯的大地啊还能挽救谁?
我的左乳灌满了乳汁,喂养后代和狼
我的骨髓和血都被吸干
只剩下岁月的空囊,补丁或者伤口
我左边的嘴唇是柔软的,不施口红
更能亲吻疼痛和冤情
一些红唇的伪爱,一些君子的奸情
我的左腿患有风湿,却选择了弱者的道路
左边的雨都是倾斜的
能安慰辽阔的世界和良心
疮 疤
我替世界产下:婴孩、腥气、灾祸的美
产下这美丽的冻疮。需要用雪来医治
我常在夜半掌灯,被旧疾惊醒
一半是感染 一半是愈合
而一服药总是煎了又熬
一个最小的细菌被逼成大病
逼成千古的冤情。我被自己的影子扶着
随时都要被风吹走。没有温度的手
一边摘花一边摘刺
摘下鬓边的那朵浮云
一声道白里的唱与念
都莫名地沾染了伤痕的气质
不说也罢,一些疮疤也有它的良心
月亮地
有月亮的夜晚是银质的。我私藏多年
山川和水都镶了边儿,有一丝杂音
是那些喝露水的动物歇在草间
像一些潜伏者,在暗处发光
我阴郁的部分都被照亮了
用一厘米皮肤相遇,用数厘米目光躲闪
我备下了前世的酒和桂花
还有寂寞的长袖。吟诵她的人都已作古
却被她一再地传说。在诗与酒里活着
豪放是婉约的另一种文本
都难免要涕下,要卧在岸边
最后都被月亮埋下,声名与诗名
月下的植物是属阴的。我也是其中之一
尘埃里的匍匐者,末日里的赶路人
都趁着月在西厢,断了最后的退路
谁还爱我饱受摧残的脸啊?
一个小仙且飞且停
脸色白过嫦娥。而我已落下
倒吸了口凉气。幸亏我还有体温
对世俗带着不舍的眼神
和一层层被包裹的茧
不免要呈现我的刀功和茶道
淡酒一两壶,一些话悠悠道出
这一地的月光,和酒后的小令
看起来都回到了天上人间
打铁的人
一个打铁的人,就是一首诗的核心所在。
这个人沉默、面部不清、须发丛生,
他的铁散落在民间,又深藏杀机。
这个人必须有一副硬骨头。
必须在铁屑飞溅时,裸露那一身的肌肉
一个在汗珠里现身的人
必有着生铁的味道、淬火的味道
那一道白烟升起,他就是个欲生欲死的人
一个崇拜“铁”的人,比钢更有韧性
更不易折断。一块铁在手上被反复掂量
像掂量这一生。无论是鸿毛之轻或泰山之重
都要经他亲手打造。而那些闪光的部分
是亮在眼前,还是怀在体内
如何呈现永远是他的品格所致
一个打铁的人,持锤如同执剑
要的就是那个力道。轻敲还是重击
他惯于用韵律定论。他对于敌手也会报上名来
藏起那锋芒、柔情和对铁的敬意
只有他的须发、皮肤、目光都是利刃。
这与持刀不同,与蒙面也不同
在精神的层面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个打铁的人,饱含着一块铁的天性。
他与铁互为知己,彼此守候又共同锻造
“铁”的生死便带一种玄妙。
如同他触摸到了,血的甜腥、水的沸点、冷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