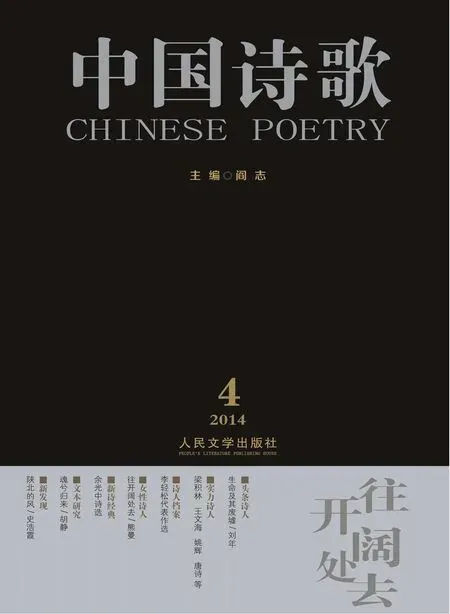魂兮归来
——马新朝长诗《幻河》中的传统文化反思
■胡静
魂兮归来
——马新朝长诗《幻河》中的传统文化反思
■胡静
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黄河因而被中国人赋予了母亲河的神圣意义。这条桀骜、凶险、雄伟、壮丽的河流不仅养育着中国人,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理结构,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马新朝长达十多万字的诗作《幻河》中,他以雄浑、劲健的抒情风格和凝练、朴素的话语方式,表述了他心目中对黄河、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厚的感情与深沉的反思。
马新朝抒写黄河的冲动始于1987年。这一年,时任《时代青年》杂志社记者的马新朝跟随着中国第一支黄河漂流队完成了对黄河的全程探险漂流。经过4个月生与死的考验,探险队终于完成漂流的壮举,但七条年轻的生命为黄河而殇。这场争夺中国江河首漂权的斗争落下帷幕,却由此引发了二十多年来反思中西文化差异的思想潮流。1988年,一部影响深远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播出,更是将以黄河为标志的中华文明与以海洋为标志的西方文明的差异凸显,并开启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批判性思考的思潮。《幻河》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所创作出来的,作为黄河首漂的亲历者,马新朝对黄河的凶险与壮丽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这一切都成为他最终提笔创作《幻河》的动因。这首诗酝酿于1987年之后,自1995年进入创作阶段,于2002年创作完成并出版。
从创作风格角度来看,《幻河》无疑应归入司空图所称的“雄浑”一品。司空图以“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四十八个字来形容“雄浑”诗风所表达的诗歌境界。他认为,雄浑诗风的形成,究其根本,是诗人内在精神气质的外在显现。而诗人内在精神气质的强健则源于诗人与自然之道的融合,即通过回到自然以养成浑成深厚之气。通过气运外物,诗人得以超越世间万象而进入形象内蕴的意旨。
从这一视角看马新朝的《幻河》,无疑会让人耳目一新。长诗洋洋洒洒十多万字,读来一气呵成,充盈着一股浑厚深沉的气韵,充分显示出作者内在精神气质的强健有力。这正是司空图所说的“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在这股劲健的气韵之下,诗人以个体对黄河的观照落笔,以一种民间的姿态,平实的视角,从黄河的源头“十二座雪峰”到黄河的入海口“渤海湾”,顺着黄河流水的走向审视着一条河流对中华文明的塑造。诗人以气运笔,以意象呈现的形式展现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史发展图景。诗中的意象都带有历史的厚重感,而意象的呈现是随着黄河的走向和历史的发展而次第出现的,这无形中证明了中华民族与黄河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这正是《幻河》这首诗的基本立足点,即对黄河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中华民族之根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走向的反思。
《幻河》开首即以“我”与黄河的同生同构来描写个体心目中的黄河,也是描写作为中国人的自己:“我是一条大水复杂而精细的结构/体内水声四起阴阳互补西风万里/我在河源上站立成黑漆漆的村庄/黑漆漆的屋顶鸡鸣狗叫沐浴着你的圣光/鹰翅走兽紫色的太阳骨镞西风/浇铸着我的姓氏原初的背景峨岩的信条/黑白相间的细节”。
这无疑是诗人幻想中的黄河,但又不仅仅是一条幻想中的河流。诗人的目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巡回,诗中的意象也在反复的咏叹中勾勒出黄河与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它超越于历朝历代此起彼伏的政治的纷争,包含着诗人对黄河带有哲理性的思索。黄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正是在约古宗列曲宁静的流水中,古老的中华民族开始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在这里,尘世的故事开始启程,走向繁华,也走向纷争。“这是泪水与血的源头是所有马匹和速度出发的地方/万物的初始孕育着我内心的节奏词语灯火”。
黄河以它万里奔流入海的身姿向着东方而行,伴着流水的奔涌而繁衍生息的人们按照流水的准则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这是自然的规律,有着永恒的节奏。“我歌唱这琴弦万里的河流流水在暗处敲响/节拍一种不可违背的预约和力量”。在黄河的哺育下成长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按照流水的节奏和自然的规律成长的中国人,自降临到这个尘世的一瞬间,已经被赋予了黄河的全部内容,注定了一生的命运。“在我见到你之前你已经拼写好了我的名字/填写好了我的种族籍贯和命运”。
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的一条清澈的河流,在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之后,成为了一条混杂着大量泥沙的黄河,这似乎注定中华民族在经过原始文明的童年之后,要经受太多的苦难,经受血与泪的挣扎,才能走向现代文明。然而,被这条黄河所塑造的中国人的性格与气质,与这条黄河一样是难以改变的。不同于《河殇》中对中华文明的激烈的批判与否定,《幻河》中的“我”更多体会出轮回的意义、沧桑的意义,一切对黄河的批判都必须与黄河的苦难并行才有意义,一切对华夏文明的诟病也必须首先与文明的传承相关才显得厚重。由此,在二十年之后,马新朝对中华文明的反思也开始进入内在肌理的层面。“在黑暗之树上摘取光明的人……”“听到了你的召唤”。
黄土高原改变了黄河的颜色,也改变了黄河的性格,黄河开始波涛汹涌,也开始经常性地泛滥成灾。“猿鹤惊心悲皓月,鱼龙得意舞高秋。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黄遵宪诗)。黄河所造成的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黄河的狂暴也驯服了它统治下的子民。在这里,黄河既是“专横的暴君”,也是“伟大的施舍者”。奔流在黄土高原的这条河流,依然浩浩荡荡地奔向东方,它所哺育的人们在它的狂暴之下依然谨慎本分地生活,无论是改道、泛滥、干旱还是日复一日生长的云梯,都没有改变黄河流域人们对母亲河的虔诚的崇拜与敬仰,他们忍受苦难,是因为黄河给了他们生命;他们承受痛苦,是因为他们对于黄河有着深沉的爱。时光荏苒,他们卑微的生命融入了世界的印迹,而遥远的七十二座山峰上的冰雪的圣迹,也终于渐行渐远。“像钟声之上的戏楼像白日残留在戏楼旗杆上的记忆”,“散发着废墟的气息和旱烟味/沉入了黄土”,“黄土关闭了孩子们全部的星辰砍断了那个传送神谕的人/通向流水的路关闭了一个人内心最后的月光”。
就像桀骜、凶险的黄河终于也要奔向大海一样,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无论路途上有多少坎坷和曲折,无论遭受多少误解与伤害,从传统走向现代依然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那从遥远的蔚蓝色的海洋上传递过来的潮水的气息,足以激发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而所有的阵痛与煎熬,都是迎接新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历程。这里诗人用“陌生人”代表来自海洋文明的探路者,“陌生人头戴海洋蓝色的光环目光湿润/他使用异乡的表情身体里水声四起/他带来了远方的信息和流水上的琴弦”。
从黄河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土地走向大海,对于世世代代依赖着土地而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世纪的挑战。代表着海洋之子的“陌生人”,已经深入到了黄土的村庄,叩响了黄土中的门楣。“陌生人在村庄里敲遍所有的黄土层柴门和拴马桩/敲遍了戏楼高塔祭坛和阴阳的两面/却敲不破一个梦敲不破一片黄土”。
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过于怯懦,只是在黄河的暴虐下他们已经习惯与黄土为伴:
黄土在他们的体内行走游动堆积锈蚀
使他们更像黄土
经受着凝固的时间凝固的风暴蚁嘴上的黑暗
在自己的骨头里安顿下来
然而,在陌生人看来,这“在黄土里走了一千年的村庄/陷入了更深的混沌/在村庄里走了一千年的你们/仍在原处”。这停滞的一千年正是因为失去了流水的气息,失去了流水的节奏,而来自蔚蓝色的海洋的陌生人,代表着一种开放的、新型的思维方式,这与黄河源流处的清澈是一样警醒灵魂的水的圣灵。古老的约古宗列曲的清澈养育了中华文明,是黄土遮蔽了我们的双眼,阻挡了我们探寻世界的勇气与智慧。如今我们要回归流水的清澈,走向更广阔的水域。“陌生人”说道:“我水汽茫茫的身子琴声四起的身子/被香草护卫被紫藻雨燕护卫/我是流水的使者/我不可阻挡我一触即溃”。
然而,“乌鸦的碎片已经在黄土里骚动/白骨已经从白骨出发”,“黄土的大军/黄土的马队/在黄土里呜呜作响”,传统的力量窒息了新生的力量。这里“黄土”代表着阻碍、窒息“流水的使者”的落后的势力,它用黄土围困了“陌生人”,黄土在“他的体内漫延迅速淹没了他的头颅/那蓝色的光环在黄土里像闪电一样/噼啪作响冒着青烟”。
这是一场流水与黄土的战争,交战的主题是改变与守旧。第一个回合,“黄土”成功了,“黄土高原又恢复了门板上的宁静/村头在陌生人曾经站立的地方/长出一棵高大的树枝繁叶茂/在村庄的西风中发出流水般的响声”。
然而,在黄土的围困中挣扎的,不仅是一个被埋葬了的海洋之子,还有每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黄土的灵魂。而灵魂的困窘却放开了欲望的枷锁,那一扇一扇没有被精神之手敲开的门,却逐一被欲望的手打开了。“黄金把黄土的面容拉入流水/把风暴拉入流水/陪伴人们的渔火从黄昏到天明/一千个梦从圣殿里依次升起/一千个梦握在黄金的手中”。
这是中华文明的“阿喀琉斯之踵”吗?这是俄狄浦斯不可逃避的宿命吗?诗人悲叹被黄土围困的中华文明,悲叹被黄金迷失的中华文明之魂。“黄金把一个季节推向另一个季节黄金是另一种/黄土比枯草更轻比万里的高原更深厚”。当被黄土蒙蔽的人们陷入黄金的迷障之中时,“我”追随着河流,遇到了比黄土更高的“幻景”,遇到了“那个鲜血满面的人”——这里显然是指遭受深重苦难的中华文明之魂,在苦难中崛起的力量终于到了爆发的时刻,这种爆发必然地采取了暴力的形式。“以暴力的形式把黄土中的一些喊声/引出把我的生命揉成一个颤音/这从天而降的大火圣殿之火/又一次找到我瞬间的轰炸/使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荒凉与破败”。
这时黄河文明在阵痛中第一次承认了内心的荒凉与破败,在革命的腥风血雨中惊醒的中国人开始怀着深厚、沉重的感情回望老去的黄河,像看待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咏叹必然要远去的传统文化。“河啊你从斜坡上走下来迟缓地走下来/在平原上展开土黄色的经卷你已经老了”。而时光像雨丝风片一样顺时而来,不可阻挡,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也时不我待。只是,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说自己已然准备好了世界的挑战,于是“年迈的父亲”为“我”递来了“太阳的酒盏”,“花朵在我体内打开的力量/使城中的开门声响成一片”。
纵使中华文化已经放弃了老去的传统和陈旧的习俗,当西方文明裹挟着炮弹和资本而来时,有谁能否认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侵蚀不是一场黄河的决堤呢?当西方文明如肆虐的洪水弥漫到中华大地的每一块贫瘠的土地,并以圣灵的名义剥夺去卑微的人们生存的意义时,有谁会说这一场文明的碰撞不是一场战争呢?何况,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碰撞从来都是伴随着国土的流失、主权的践踏和经济上的操纵。在这个历程中,诗人的描述包含着沉痛与压抑:“你的阴影踏过盛典在台房与台房之间巡视/暗中已经把我的名字记下我的躯体血肉灵魂/成为你的道路写满了黑色的咒语”。
但是,正如黄河的九曲十八弯中隐含着中国人灵魂深处顽强的生命力一样,中华文化的根远在圣灵栖息的巴颜喀拉山雪峰,那里不是尘世的兵锋和血雨所能到达的地方。每当黄河的波涛声被喧嚣的时代和世俗的欲望所遮掩时,就会有空灵的声音响起,就像英国诗人丁尼生在《越过沙洲》一诗中所吟唱的“一个呼唤我的清越声音”。它呼唤着中华民族的“魂兮归来”,这声音越过所有离乱的风尘,深入响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隐隐约约我听到有人在黑暗中唤我”,“洪水滔滔洪水滚过我的肢体滚过我的呼吸”。而洪水所到之处,仍然使沉寂千年的古城崩塌,使迷失于欲望的人们衰亡,这一场命定的毁灭与救赎,对于古老的中华文化而言,福兮祸兮?人们只看到:“人影晃动/面容模糊的背尸人在历史的走廊里洪水的走廊里/来回穿梭他们把这些古今的/朽亡葬在何处”。
如果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一场必然来临的潮汛,如果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屈辱与抗争是一场无处逃离的洪灾,那么所有的灾难过去,等待着我们的仍然是在废墟上重建民族自尊的勇气与责任,而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所赋予“我”的最原始的力量。“在广远的大地上我独自收拾着/落英鸟羽紫箫文书收拾着祭器与血迹”,“我已经经历了西风中/全部的泪水经历了黄土中最深的黑暗/经历了河流的洪水和干枯”。
文化传统的断裂所造成的心灵的饥渴让现代社会的人们陷入欲望的深渊,也使整个社会迷失价值的坐标。重建文化传统犹如干旱的人们寻找水源一样急切:“寻找水源的人们被水源流放/大地上聚集着寻找水源的人”,“我们翻过一个又一个陡坡人流如潮/水源在远方传递着消息远方浮动着黄昏的脊背/用血液的速度用水瓮的速度/被流水的波光引导”。
当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已经被摧毁时,自尊心便像麦田里凸起的野草,顽强地显露出来。上一个世纪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落败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来临时期待着用一场新的碰撞来证明自己的成功。然而重建中华文化的传统不仅仅像在一场一场文明的碰撞中夺得胜利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用心灵守候,静候圣灵的重新降临:“我”在“风沙漫卷的回廊里”“静候”,在“无水无波的渡口上”“静候”。
文化传统的重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对重建文化传统的基本立场却应该是早就确定好了的。黄河一刻不息地奔流向大海,如果离开海的怀抱,抛弃大海的胸怀,中华文化不可能一朝立足于世界。因此,怀抱黄河的浪涛与大海的无限和蔚蓝,应该是中华文化得以长久繁衍下去的永恒的立场。
渤海湾的风吹来它怀抱着大海的无限和蔚蓝
它怀抱着空无一人的河床传递着最陌生的词语和呼吸
渤海湾的风吹来
这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的气息,它必将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