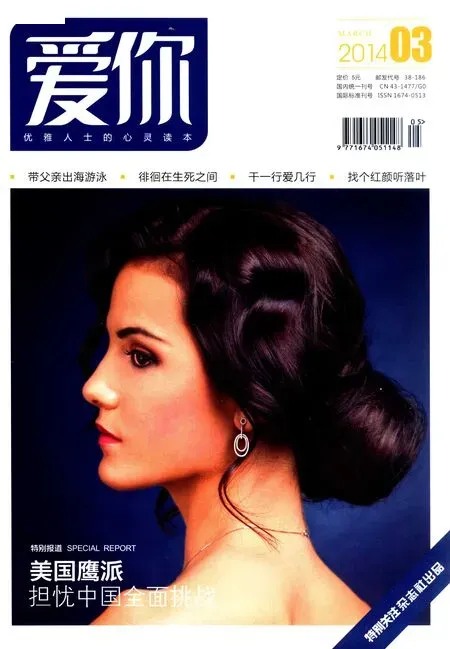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 王艺涵
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 王艺涵
严师出高徒
尽管在国内时我有两年多的媒体从业经历,可等到了美国,却不得不从一名实习生干起——在《每日南城报》做校对。三个月后,我在社会新闻部当实习记者,开始动手写稿。在这里,我遇到了资深编辑劳伦女士。
一天上午,我接到一桩采访任务,要写一篇芝加哥当地美国中产家庭每月消费与支出的调查分析。
三天后,我把打印得工整、漂亮的稿子交给了劳伦女士。半小时后,劳伦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重写一遍!注意,每段应由主题句开始。”
当天临下班前,她收下了我的修改稿,示意我先回去。两天以后,待劳伦把文章交还给我时,稿子已被红笔一道道划掉许多,旁边增加了一行行字。劳伦一边交还稿子给我,一边拿两本工具书给我,说:“王,遇上不会拼的新词,没弄懂的知识,请记得查字典。”
我那篇稿子被她反复用红笔认真修改过好几次,包括语法、逻辑、修辞,甚至连拼写、标点符号都改好了,才获通过。
“记住,你可以做得更好!”这是她和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十个月熬过去,我的文字越写越顺。一年后,我实习期满拿到了传播学硕士学位。
脱颖而出
结束实习生涯,我谋到一份薪水不错的报社工作。
有一天,报社人力资源部主任大卫·查普曼要求所有新员工用两个小时写一篇福利院见闻记。他的要求是:要让从没去过福利院的人身临其境。
三天以后,查普曼把我的稿件往桌子上一放,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拿起反盖着的稿子,一个红笔写的“A+”跃入我眼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天下班后,查普曼特别找我喝了两杯,使我更加受宠若惊。
“王。”查普曼说,“我在人力资源部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为一篇新人的文稿打A+,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我摇头,一脸茫然。
查普曼继续说:“这说明,在教过你的老师里,必有一位杰出的老师,他磨练了你观察与写作的能力,你应该向这位老师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还可以做得更好
2012年3月,我进了《芝加哥论坛报》,忙得不可开交。我负责市民丧事告示,就是刊登者提供逝者基本资料,由我编写讣告和悼词。我力求做到文字简洁,语调平静,有时夹点小幽默;该煽情时煽情,情到深处,哀婉感人令人唏嘘泪下。半年过去,我成为报社里出勤最多的讣告、悼词撰稿人。
忙忙碌碌中,我几乎把劳伦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原来她的父亲去世了,想在论坛报上刊登讣告。我心里一惊,事不宜迟,我立即驱车前往劳伦的家。
我鼓起勇气按响了门铃,前来开门的劳伦和九个月前判若两人:脸色苍白,悲伤过度。
她神态疲顿地坐在沙发上,拿出了她父亲的生平资料。原来,劳伦的父亲也是位记者,曾供职《纽约时报》,上世纪60年代,还曾获得一项普利策奖。劳伦说:“孩子,我知道你干得不错,我父亲的讣告和悼词就由你来撰写。这一次,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我突然结巴起来,嗫嚅地告诉她,我当初还曾抱怨过她,还讲到了报考论坛报的经过,然后说:“所以,我一直想来看您,向您说声谢谢,可工作太忙,一直没能来,真对不起。”
劳伦愣了一下,眼圈有点红了。她拿出了几大本她父亲当记者时的稿子簿,按草稿、修改稿、最后登出的定稿的顺序装订。最初的草稿主题含混、结构散乱,文字枯燥无味;修改稿上夹杂着很多红墨水改动的文字是她父亲自己或编辑动笔修改的,就像是蘸着作者的血来写成;最后的定稿,文字畅达娴熟,如清澈的流水。
临出门时,劳伦清了清嗓子,对我说:“王,你还可以做得更好。相信我!”
我点头,握着她的手,目光有些湿润。(摘自《华人时刊》2013年第10期 图/周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