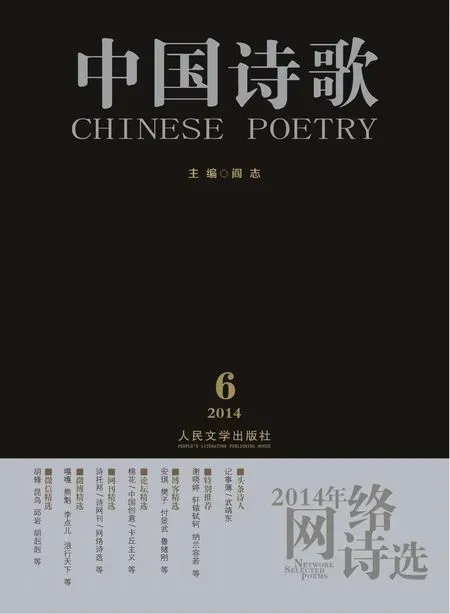羽毛〔外一首〕
2014-11-15 00:41羌人六
中国诗歌 2014年6期
◎羌人六
羽毛〔外一首〕
◎羌人六
十月,穿过被鸡屎和落叶碾得蓬头垢面的庭院,
被秋阳锯出老相的核桃树,忧郁地闪到一旁
它数着自己不断剥落的羽毛,
慢慢誊出天空,
慢慢誊出死亡跟生活的本来面目。
这些羽毛,更像留在记忆里的疤。
父亲去世后的很多夜晚,
疤就在我的血液里借宿。它们将我苦成一个男人。
核桃树,它的果实是雷管。它的高度是导火索。
飞蛾扑火的父亲,是落地的核桃。
这一刻,核桃树剥落的羽毛,
更像是它亲手写下的欠条,
但它遮遮掩掩,像要提醒什么——
众多的隐喻后面,死神戴着面具,
昼夜不息。
到此一游——悼东荡子
素未谋面的诗人,
头戴似曾相识的王冠,怀揣似曾相识的死,
穿过茫茫夜色和苦白了月亮的那种孤单,
从遥远的外省
款款而来,他来得恰到好处——
逮住了大山里一场政治篮球的尾巴,逮住了
满桌狼藉的荤菜、诳语和“夜郎”二字独有的狐臭。
球场上这些慢吞吞的小鱼,形同虚设;
永远比进攻少半拍的防守,形同虚设;
捉襟见肘的得分,形同虚设。
生与死,输和赢
刚好与我被塑胶场地磨烂的脚板,不谋而合。
死,我们养在身体里的小鱼和共鸣,疯狂又虚无。
昨夜,你的噩耗像条小鱼,在这个国家
大大小小的城市上空,游来游去;
在那些同时暗下来的草木和石头中间
走动,翻山越岭。
隔着命运的扶手,我命令带风的词语为你送行,
但它们统统弱爆了,
像球场上那些形同虚设、
慢吞吞,巴不得被对手活剥的小鱼。
突如其来的噩耗和远离,身形臃肿不堪,
只是我们都难以消化。
猜你喜欢
农民致富之友(2020年26期)2020-09-12
小资CHIC!ELEGANCE(2019年33期)2019-11-22
作文·初中版(2019年9期)2019-09-15
阅读与作文(小学高年级版)(2018年9期)2018-10-25
小猕猴学习画刊(2018年5期)2018-06-12
环球时报(2018-04-12)2018-04-12
足球周刊(2017年22期)2018-04-03
新农村(2018年35期)2018-04-02
作文周刊(中考版)(2016年41期)2017-06-01
网球俱乐部(2009年1期)2009-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