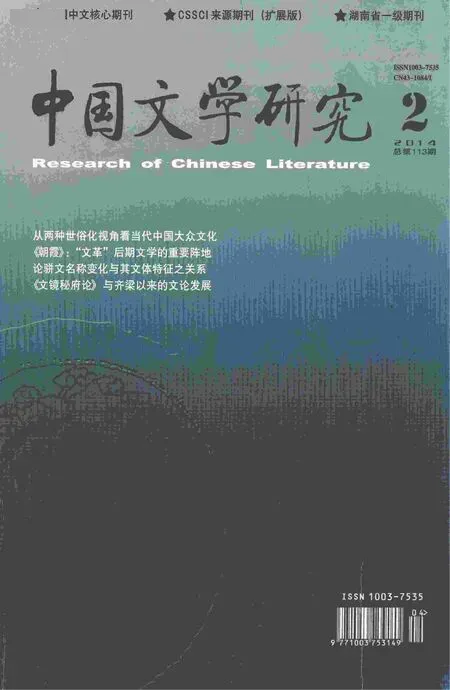鲁迅小说中人物话语的戏剧艺术审美效果
孙淑芳
(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综观鲁迅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叙述、描写固然存在,但叙述和分析性的描写已经不是主要的手法,特别是人物话语,基本上采用戏剧式直接展示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是,《起死》这一历史小说是采用话剧的剧本样式来创作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话语往往有一种摆脱了叙述主体的影响而“自行其是”的幻象,仿佛是对象自身越过了话语主体的中介而“直接”同我们见面,因而具有一种客观性、生动性。人物的话语也明显地体现出戏剧话语的特点——不仅显示人物的性格,更具有很直观的动作性。具体表现在人物“自然”对话的动作性和个人独白的动作性两个方面。这两种富有动作性的人物话语,不仅指向人物的生存状态,更指向人物的精神状态。这正是鲁迅小说具有深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鲁迅小说中也不乏人物外部动作(形体动作)的叙述和描写,但动作幅度大的、具有戏剧性的外部动作倒是很少。由此可见,鲁迅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人物的精神层面,正像夏志清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记得,作家鲁迅的主要愿望,是做一个精神上的医生来为国服务。”
一、人物“自然”对话的戏剧审美效果
瓦莱特认为,根据柏拉图的观点,小说是一种混合体裁,“《奥德赛》一直被视做最早的叙事文学作品——口头的或书面的——之一。……《奥德赛》一方面包含对物体、人物(肖像)和事件(或者是叙事)的描述,这些描述要求施动者(讲述者或者作者)的存在;另一方面含有对人物话语的直接描绘(模仿)。小说得到‘混合体裁’的称号正是由于其对戏剧体裁的对话体的模仿。”瓦莱特的这种看法也意在表明小说与戏剧艺术之间存在着渗融的关系,主要侧重说明小说中对人物话语的直接模仿其实是借鉴了戏剧体裁中的对话体样式,可以说在人物话语的展现方式上,“直接模仿”使小说与戏剧艺术之间具有了一定的“共同语”。
根据瓦莱特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更多地采用了戏剧的形式,让人物自己表达,直接使用“自然”对话。在鲁迅的小说中,绝大多数篇章里都存在这样的对话。且不说《起死》这一剧本形式的小说,就《长明灯》而言,整篇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段就在于对话,《药》、《风波》、《肥皂》、《离婚》、《高老夫子》、《孤独者》、《奔月》、《非攻》等小说的叙事里都插入了大篇幅的人物对话。而这些人物都操着符合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特征的语言。鲁迅正是运用对话来客观地展现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通过默示的方式提供各种观点正面冲突的场景。“从福楼拜开始,作者似乎不再作为陈述者介入作品了:他让位于故事,让人物和故事说话。”对于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只有客体和观察到的经验最重要。他们拒绝对某个价值体系发表立场,只是满足于公正地再现事实:可以说论说的重要性和叙述成反比。”鲁迅小说直接模仿人物话语的特点,正契合了现实主义的叙事行为,与戏剧基本上运用对话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类同。
鲁迅小说中的对话,不只是向观众交代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叙述已经发展了的情节,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强烈“动作性”,直观地呈现了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谭霈生认为:“‘对话’本身就意味着双方的交往。但真正具有戏剧性的对话,应该是两颗心灵的交往及相互影响,对话的结果必须使双方的关系有所变化、有所发展,因而成为剧情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小说在叙事中追求动作性的做法可能来源于童年看戏的体验与记忆。鲁迅“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社戏》中也回忆了儿时看戏的情景:厌倦那只是依依呀呀地唱的老旦,喜欢奇异的扮演和打斗的场面。鲁迅少儿时期,家乡绍兴经常上演他所衷爱的“目连戏”。“目连戏”集戏曲、舞蹈、杂技、武术于一身,将“唱、做、念、打”融为一体,外部动作幅度相当大。儿时的体验与记忆潜意识地影响了鲁迅小说中塑造人物技巧的戏剧化选择。只不过鲁迅是在借鉴以平等深入的精神对话为宗旨的西方戏剧和具有现代性的西方小说的基础上,将中国戏曲重故事重人物外部行动的惯性转为重人物内在的心理冲突。因此鲁迅小说中的对话并不注重推动情节的发展而重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众所周知,戏剧基本上是以人物对话对冲突的再现。正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戏剧性不在于对话,而在于对话者彼此的生动的动作。”鲁迅小说中对话的动作性就体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上,冲突既有外部冲突也有内部冲突,其中外部冲突典型地体现在意志冲突上。意志冲突是戏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动作性最强烈的。“意志”本来一直就是心理学上的概念,指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常以语言或行动表现出来。根据谭霈生的“性格冲突”说,意志是性格构成的一种因素,因此鲁迅小说中的冲突及其结果除了意志之外,还有性格中的其他复杂因素在起作用,从而使塑造的人物形象和反映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几个对话片段,为了便于考察,下面所列举的对话均省略了其中夹杂的少量的叙述、描写、论说的语言和对话的引导词。也就是说只凭借人物自身的语言,而不依靠其他说明、暗示的语言来透视对话的动作性。
“吃人的事,对么?”
“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对么?”
“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狂人日记》
以上是狂人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对话,对话的动作性极强,在对话中所体现出来的既有外部冲突,又有内部冲突。冲突既包含着意志上的冲突,也存在着性格上其他因素的冲突。就外部冲突而言,狂人与年轻人之间构成极端对立的矛盾关系,其内质是两种自觉意志——反抗吃人的行为和维护吃人的惯例的对立,而且两人的意志强度可谓是旗鼓相当。狂人从四千年来吃人的社会中觉醒,认识到“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因此毫无惧色、“勇气百倍”地质问年轻人,呈现出直言无忌的性格。而身为吃人一伙,“喜欢吃人”的年轻人则墨守陈规,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个吃人的社会。这样就构成了狂人与年轻人这两股客观的敌对力量之间的对抗。当两种对立的意志正面交锋,在狂人步步逼问的情境中,这种对抗终于演变为直接的冲突,表现在意志行动上的冲突就是语言上的交战。从内部冲突来看,年轻人的主体心灵中同样存在着矛盾,承受着灵魂分裂的煎熬。“有”与“没有”,“对”与“不对”言语的前后矛盾正可谓是年轻人内心深处冲突的表征。面对狂人的拷问,年轻人由否认到尴尬、力图转移话题再到语无伦次直至凶相毕露,态度蛮横强硬、针锋相对,这期间他的心理一直处于挣扎与冲突之中。尽管年轻人认同“从来如此”的吃人老例,但也知道不宜明说,特别是直面具有异质思想的狂人。因此年轻人的心理一方面坚守吃人的传统,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遮人耳目,呈现出矛盾对立的状态,于是在与狂人的对话中左躲右闪,含糊吞吐,恰似在吃人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凶狠、狡猾和怯弱正是年轻人灵魂中冲突的两种性格力量。在《狂人日记》的这段对话中,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交错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从而使对话极具动作性,对话的结果使狂人与年轻人的关系由抵触发展到正面冲突。在“人吃我,我吃人”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狂人与年轻人的意志冲突其实已经被赋予了社会属性,所以他们之间对话的戏剧性(动作性)也就有了某种明显的社会批判的力量。
关于意志冲突的另一典型例子体现在《长明灯》中。阔亭们与“疯子”在庙前的对话主要是外部冲突,矛盾对立的双方是“疯子”和吉光屯的民众(主要是阔亭和方头),他们之间的冲突就鲜明地体现在意志冲突上。双方自觉意志都无比坚定:“疯子”执意要熄灭梁武帝点起的长明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他要“自己去熄,此刻去熄!”他不理不畏那些人对他的威逼劝诱,推不开庙门就想出放火的办法,一心要熄灭长明灯。阔亭和方头则坚决保卫长明灯,他们认为保住了长明灯就是守护住了吉光屯,灯在人在,灯灭人亡,为了阻止“疯子”熄灭长明灯,他们软硬兼施。处于对抗而又十分强烈的这两种意志使矛盾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并迅速发展到危机的顶点,“我放火!”表明了“疯子”熄灯的决心,也似晴天霹雳让吉光屯的人们感到末日的来临,由此双方关系也发展到一个十分紧张的阶段,从而使对话场景随之推进到接下来的四爷客厅的紧急议事。《长明灯》中的这段对话的动作强度甚于上面《狂人日记》里的。
在以上两个对话片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矛盾对立的双方是个人和众数,这里指的是持某一种思想的人数的众寡。他们之间对话的动作性都是十分强烈的,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势单而减弱冲突,相反,冲突都是愈演愈烈。正像易卜生《人民公敌》里斯多克芒医生所认识到的:“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对话的动作性是鲁迅刻意采取的最能直观而又强烈地体现出个体人物与传统文化、守旧势力不屈斗争的语言运用上的重要手段。
“你回来了?”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也许有罢,——我想。”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祝福》
《祝福》中的这段对话也蕴含着丰富的动作,不过这段对话不存在外部的对立和冲突,而重在人物内心的冲突,也就是人与自我的冲突,呈现出一种个体人格本身的分裂和矛盾。“我”与祥林嫂之间没有矛盾关系,也就不存在对立和冲突,相反“我”倒是很同情祥林嫂。但是在对话中这两个人物各自的内心世界却掀起了惊涛巨澜。“我”本来是想布施与她的,却不料她问出人死后灵魂有无的问题,在这个鬼神依旧占统治地位的鲁镇,祥林嫂大胆质疑鬼神存在的思想先是令“我”感到十分恐惧,然后就是自我内在的冲突和斗争,不知是该说“有”还是“没有”。本着同情的心理,“我”想说鬼魂的存在来减轻时日不多的祥林嫂的苦恼,但面对追根问底、已对鬼神持怀疑态度的祥林嫂“我”又觉得先前的回答站不住脚,不能给祥林嫂以合理的解释,所以不免胆怯又想推翻先前的回答。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我”只能用一些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话语,还是吞吞吐吐的。标点符号(问号、破折号、省略号)和词汇(感叹词“啊”“唉”)以及问句语法的使用都更有效地体现了“我”当时内心世界强烈的冲突和斗争。问句的使用既是对祥林嫂问话的震悚也是自我灵魂的拷问。最终“我”以“说不清”力图掩饰内心所有的犹虑和矛盾。在对话中,祥林嫂始终处于发问的主动地位,但她的内心世界同样受到来自外部语言的巨大的冲击力。与“我”开始对话前,祥林嫂对鬼神的信念已经动摇,但还是不确定,想通过“我”加以明确,可以说她对“我”这个见多识广的读书人抱有完全的信任。然而“我”似是而非的回答却使祥林嫂陷于难以摆脱的内心困扰之中。她希望魂灵的存在能使她和日思夜想的“宝儿”相见,又希望魂灵不存在以免被两个“男人”锯开。
史雷格尔认为,戏剧性对话和非戏剧性对话的界限正在于对话本身是否具有动作性。在他看来:“如果剧中人物彼此间尽管表现了思想和感情,但是互不影响对话的一方,而双方的心情自始至终没有变化,那么,即使对话的内容值得注意,也引不起戏剧的兴趣。”而对话的动作性指的正是人物在对话中“以各人的见解、情操、情感相互影响,断然决定他们的相互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对话中,“我”与祥林嫂不仅存在着主体自身灵魂的冲突,而且个人的内心冲突表现在语言上,一方对另一方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双方的心情可以说是产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从自觉站住等着祥林嫂来讨钱到带着不安的心情急匆匆地逃离,祥林嫂则从满心的期待到最后选择了死亡。当然我们不能将祥林嫂的死完全归于与“我”的对话,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我”的对话就是导致祥林嫂恐惧而又绝望地走向末路的“最后一根稻草”。由此可见,“我”与祥林嫂之间对话的动作性十分强烈,对话的结果使“我”与祥林嫂之间的关系由主动遇合到被迫逃离。
关于对话的动作性体现,谭霈生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具体体现冲突的对话才有动作性,心灵的交往也可以是意愿一致时内心情感的交流,但同样相互具有影响力,能够导致双方的心情以及相互关系发展变化。鲁迅小说中的有些对话的动作性就并非体现在冲突上,而是人物之间意愿趋同时的内心情感交流与相互间的影响。《孔乙己》中掌柜与酒客的对话,《药》中华老栓店里茶客谈论夏瑜,《风波》中土场上围绕七斤辫子的问题展开的议论,《肥皂》中四铭与道翁、薇翁议拟征文题目,《长明灯》中吉光屯茶馆里、四爷客厅上众人商议对付“疯子”的办法,《弟兄》中公益局办公室里办事员谈论弟兄之间的关系,《离婚》中航船上谈论爱姑离婚的事情等场景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不仅没有冲突反而起到了沁染思想、普泛情感、激发共识的作用,特别是凝聚传统思想、坚定传统观念的作用。群众精神上的保守、愚昧、麻木、冷漠、自私、残酷、不觉悟的集体性格,对待别人的命运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像瘟疫一样在人们中间蔓延着并不断地被强化,包括孩子。封建传统势力也在猥琐而卑劣的共同商讨中力图维系、稳固封建传统意识形态。
鲁迅以对人生、人性内在矛盾和人物之间心灵交往的深刻洞察赋予小说前所未有的现实性与现代性。他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充当小说家主体理念的傀儡,而以其自在的生命状态进行“对话”,“对话”的客观性亦使人物深度精神内容得以释放,从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深刻性与现实性的精神“对话”。可以说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真正体现出西方戏剧以平等深入的精神对话为旨归的中心理念。而鲁迅小说中这种人物对话所富有的动作性使人物的内心活动获得了戏剧式表现的直观、客观、生动的艺术效果。
二、个人独白——人物内心话语表达的戏剧审美效果
在鲁迅小说中,独白被作为展现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实现“心理分析”的有效方式之一,呈现出戏剧特性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内心独白,无假设听众;另一种是戏剧式独白,有假想听众,它们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为“自由直接引语”(“原本”记录人物话语,但通常不带引号也不带引导句,或者仅省略其中一项)和“直接引语”(使用引号“原本”记录人物话语,保留其各种语言特征,通常带引导句)。这两种人物内心话语均为第一人称,时态为现在时,具有戏剧艺术表达的直观性。正像英国当代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所说的:“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
现代小说摆脱传统小说束缚的途径之一,就是把话语模仿推向极限,除去叙述主体的最后标记,常常运用自由直接引语,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展示这一戏剧化手法,让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直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鲁迅小说中,用自由直接引语这种极端形式表达内心话语的非常明显的篇目有《狂人日记》、《伤逝》等,小说摆脱了一切叙述模式,叙述者不起任何作用,整篇当中除了插入的少部分直接引语,大部分都是最戏剧式的自由直接引语,它们将狂人、涓生等人物的意识直接展示给读者。当然鲁迅在小说中也运用直接引语来表达人物的内心话语,如《幸福的家庭》里的人物内在的直接话语就加以引号。这种表达方式同样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将主人公的内心幻想像一个个流动的画面一样直接呈现给读者。鲁迅小说中大篇幅运用戏剧式独白的有《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其中《头发的故事》通篇基本上是N先生一个人的独白。鲁迅小说中的戏剧式独白是将个体的内心世界直接展示给读者,并构设了独白的对象,成为个人内心话语迸发的触发力量。就独白的对象而言,《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都是“我”,“我”就是假想的听众。
不论从戏剧演出的直观性上还是从戏剧的观演关系上来看,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独白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戏剧的艺术特性,然而更具戏剧艺术特性的是其所包含的内心动作。在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独白被发挥到了极致,一篇小说甚至就是由一个人的独白所构成,长篇独白之所以在鲁迅小说中能够获得成功,其关键就在于独白所具有的动作性。戏剧中的独白是展示人物内心动作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情节的组成部分。鲁迅小说的长篇独白同样蕴含着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动作,从而成为长篇独白的主要原动力,使长篇独白能够衍生成小说的整个情节或参与小说情节的重要构成。鲁迅小说长篇独白的动作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与他者的意志冲突和性格冲突;人物内在的情感律动;人物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和内心与外界的互动。
在《狂人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犯病的”的狂人,以狂人的眼睛观察、评价世界必定是非正常的,非正常的“个人”自然会在思想言行上与周围的人或事物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相背离,呈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发人之所未敢发,行人之所未敢行,这正是鲁迅渴求出现的启蒙者形象。因此狂人独白的动作性就体现在精神(意志和性格)上与众人的严重对立。狂人所独具的个体精神特征:洞察力、判断力、怀疑性、反叛性、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反思意识,与“吃人的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征:伪善狡猾、色厉内荏、是非不辨、愚昧守旧构成的截然反差,势必促成狂人与“吃人的人”之间决绝的冲突,而这冲突就成为狂人内心独白的强大内驱力。狂人的内心独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其所包蕴的激切的内心的动作足以让人心惊胆战,《狂人日记》因此而成为鲁迅小说中向封建社会笔伐的第一声“呐喊”。
《头发的故事》这篇小说几乎是N先生一个人内心独白的迸射,堪称“独白体”。鲁迅根据小说既有的特定的题材,紧紧抓住了N先生的个性,将其内在的情感律动作为他长篇独白的深层原动力。统观全篇,N先生的感情波澜从激愤到沉痛,从沉痛到得意,从得意到诘责,就是在“得意”这个感情层次里仍然存在着情感的起伏:苦闷——悲哀——孤独——得意。尽管情感上有波澜,但N先生的每一种情感无疑都是十分强烈的,至始至终贯穿着愤世嫉俗、忧虑时事的精神。这是鲁迅经过精心构思所选择的颇具动感又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情感。正是这内在的情感律动使N先生长篇独白的情节得以自然形成,情感的逻辑性演变不断推动着独白向前发展。另外这篇小说长篇独白的动作性还体现在人物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上:为革命而献身的故人本该值得纪念,“我”却不堪纪念而忘却了纪念;出去留学剪掉了辫子,回到中国又买了一条假辫子带上;自己废了假辫子穿西装,然而又在笑骂声中不得已换成了大衫;留学时气愤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本多博士用手杖说话的行为,而自己现在中国竟也无意识地这样做了;自己内心里赞成剪辫子,嘴上却不支持学生剪辫子;希冀革新,却又对积垢深厚、发展缓滞的中国失望而悲愤。这些如此深刻的内心矛盾所不可避免而产生的尖锐的内心冲突,推动着人物独白的戏剧性展开,成为长篇独白的又一原动力。《伤逝》中内心独白的动作性表现类似,“我”(涓生)对子君感情的发展变化、“我”与子君灵魂的隔膜以及“我”自身思想的内部矛盾冲突成为独白的内在动力。鲁迅不愧为“精神分析学家”,他对人物心理变化的规律与节奏的把握是如此的准确而熟练,整个心理过程如波浪一样高低起伏。《在酒楼上》、《孤独者》中人物的戏剧式独白都是由与“我”这个独白对象的对话引发开来的。在戏剧中,作为言语动作的“独白”,本身就是人物心理动作的一部分。这两篇小说独白的动作性同样也体现在人物内在的情感律动和人物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上,特别是后者。独白展示出了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及今昔完全两样的心态,或是敷衍模糊或是颓废报复,曾经是战士形象的“他们”在“变脸”转型的过程中该是怎样的无奈、伤痛、悲愤与失望啊,而伴随这个过程的就是内心激烈而惨痛的斗争。
与《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里人物独白的动作性表现不同,《幸福的家庭》中“作家”内心独白的动作性主要体现在其心理幻想与现实状况的互动上。“当内心活动是在外部动作的刺激下引起反应,由平静和谐走向矛盾冲突,并趋于紧张激烈而需要加以外现时,也才具有真正的戏剧性。”“《幸福的家庭》中‘作家’的创作心理始终受制于他自己所处的不幸家庭的状况,心理的每一变化、‘灵感’的每一次获得总是受到自己家庭的种种‘不幸’的启发,这样,他的思维和心理变化便形成了某种规律性的定势:幻想与情绪的爆发点总是对现状的某种不自觉的反拨。”创作构想中对不断干扰进来的现实情形的置之不理或“纠正”和美化,充分说明了“作家”运思时内心潜在的矛盾冲突。最终“作家”挣脱矛盾,走出幻想,回到现实。也就是说,“作家”的内心独白是一种戏剧性的动态的展示,它总是受到外界的触发而得以继续开展,当开展不下去的时候,也就是内心理想与外界现实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促使“作家”不得不有所选择和行动,表现出来就是放弃幻想,干预现实。
通过直接内心独白和戏剧性独白,鲁迅将小说中人物的独白直接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与戏剧将独白直接诉诸于观众听觉的效果是类似的,同样做到了直观与生动,它们都直接触摸到人物心灵的深处,动作性十分强烈,从而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除此之外,鲁迅小说还有一种戏剧式展现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静止,如果说前两种独白相当于戏剧中的有声独白:把人物内心的活动具体地告诉观众,那么静止也就相当于戏剧中的无声独白:通过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联想获得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谭霈生认为:小说家对人物心理活动进行分析、描写的方式在剧本中没有用武之地,戏剧有它自己的方式。方式之一是剧本“舞台提示”中所说的“沉默”,或曰“停顿”。在这时,人物没有台词,没有明显的形体动作,只是静止不动。停顿是否具有戏剧性,正是取决于人物在这一瞬间心理活动的内容。“停顿”也正是一系列因果相承的动作中的一个环节。“停顿”是无声的独白。预示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变化,预示着将要有一系列新的动作。在鲁迅小说中,人物的静止动作是颇多的,下面举出部分例子以供参考: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药》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药》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故乡》
“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故乡》
“‘阿呀!’吴妈愣了一息”。——《阿Q正传》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祝福》
“他的笔立刻停滞了;他仰了头,两眼瞪着房顶”。——《幸福的家庭》
“他惘然的坐着,仿佛有些醉了。”——《幸福的家庭》
“学程看了他几眼,没有动。”——《肥皂》
“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长明灯》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示众》
“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孤独者》
“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孤独者》
“他连喝了两口酒,默默地想着”。——《孤独者》
“他想着,默默地喝酒,吃完了一个熏鱼头。”——《孤独者》
“他沉默了,指间夹着烟卷,低了头,想着。”——《孤独者》
“她又沉默了一会,说……”——《伤逝》
“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伤逝》
“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伤逝》
现在我们从以上举例中挑选几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透视这些静止动作背后的内心独白。我们首先来分析《祝福》中关于祥林嫂的一处静止动作:“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在祥林嫂已经把阿毛的故事讲到别人都听得纯熟的时候,她再刚一开头,便立即被听众厌烦地用戏谑的模拟口吻生硬地打断。当她渴望用这个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爱子阿毛深深的忏悔和无尽的思念时,别人却无情地剥夺了她的这一话语权,她连倾诉的人、倾诉的机会都没有了。当她雕塑似的“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那些对她几乎“深恶痛绝”的人们时,她的内心犹如五雷轰顶,悲凉而绝望。祥林嫂的这一静止动作正是其内心受到强烈撞击所必然发生的,它预示着祥林嫂必将会有新的变化和动作。在接下来的环节中祥林嫂的性格变得更加麻木呆滞,她对周围的人已经丧失了讲述的欲望,“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因此可以说祥林嫂此时的静止动作,是具有戏剧性的。在《孤独者》中人物的静止动作是比较多的,其中“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这一静止动作发生在魏连殳祖母大殓的时候,大殓已经完毕,可魏连殳却还一动不动地坐着、沉思着,这一静止动作不知道保持了多久。然而魏连殳的内心却不是静止的,他此时内心进行的言语过程是复杂而丰富的,他的脑海里回放着关于祖母的记忆,用自己孤独的心品味着祖母孤独的一生,共鸣的情感使他的内心犹如波涛汹涌。魏连殳的这一静止动作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长时间的沉默必定会带来情感火山式的喷发,而“在沉默中爆发”的情感才最有力量。所以此处沉默的动作性是非常强烈的,它是鲁迅所设置的魏连殳在祖母大殓时所有出人意料动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应哭孝的魏连殳却长时间沉默,这是出乎众人意料的;然而酝蓄已久的沉默突然转为惨痛的大哭,更是“老例上所没有的”,但却是人物内心动作发展的必然结果。魏连殳的这一静止动作同时也预示着其孤独、愤世性格的进一步发展,对祖母的重新认识、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以及与周围人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吊唁的众人从对他的沉默“惊奇,不满,想走散”到他大哭时“手足无措,集体前去劝止”,而且没有劝止住。《伤逝》中子君的沉默同样蕴含着丰富而剧烈的内心动作,直接指向子君未来的命运。“优秀剧作中的‘停顿’是富有戏剧性的,这正是因为在这个静止不动的瞬间,寄寓着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内容,它甚至比让人物用冗长的台词把内心隐秘和盘托出具有更大的艺术效果。”就“戏剧动作”的真正含义来说,内心动作比外部的形体动作更丰富、更重要。鲁迅小说在塑造人物手段上即善于借鉴戏剧审美特点,颇具戏剧的艺术效果。“在表现某种戏剧性情势时,不是运用某种慷慨激昂的陈述,而是运用某种恰如其分的沉默。”
正像谭霈生所认识的那样:“小说和戏剧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人物动作的叙述、描写,后者是对动作的直观再现。小说和戏剧对外部动作的不同表现方式,更明显地表明了这种区别。”其实这种直观的再现就是对人物动作的直接模仿。“在戏剧艺术中,模仿手段达到了自己的高峰。”而鲁迅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现除了“言语模仿”还有“对真实思想活动的模仿”,从而使小说在借鉴戏剧优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具有了一定的直观性、客观性、生动性。最重要的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和独白并非是静止的展现,而是体现出了戏剧艺术的本质特性——动作性,从这一点来说,鲁迅小说与戏剧艺术对于人物内心的表现在艺术的效果上是一致的。毋庸置疑,小说叙事的语言属性决定了本文所论述的鲁迅小说人物话语的戏剧审美效果,也只是相对于其他艺术手段而言的一种艺术效果。但就是这种效果使鲁迅小说突破了古典小说在人物话语方面重叙述、重议论、重分析性描写的艺术规范,在叙事中具有一种动态的美感,使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得以生动鲜活地展现。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法)贝尔纳·瓦莱特著,陈艳译.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鲁迅.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M〕//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汪流.艺术特征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6〕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
〔7〕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英)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9〕施旭升.戏剧艺术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10〕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1〕(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