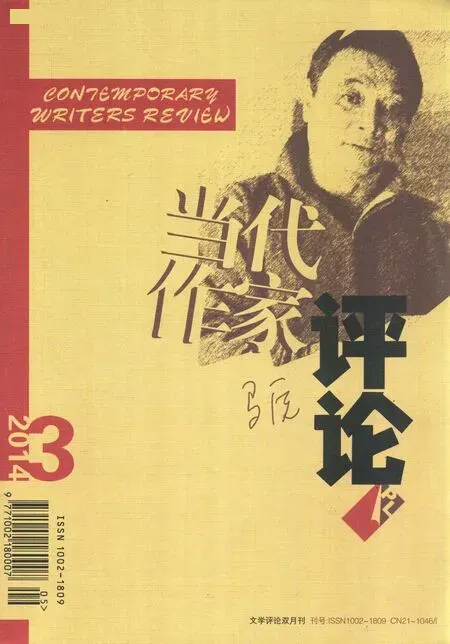《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毕飞宇的三重叙事
汪 政
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几次三番地强调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来说尤其厉害。他曾经以哥德、达·芬奇、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为例子,把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一一对照,说出了许多惊人的秘密。如果这位医生的话是对的,那么,了解一位作家,或者将他的作品读透的好方法之一就是去翻看他的童年,不管是大事小事,都会意味深长。
所以,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首先的意义是精神分析学的,是创作学的,肯定会被那些搞传记批评的评论家抓住不放,深挖不止。事实上,我们确实从毕飞宇的往事中看到了他作品的许多原型,虚构的生活与实体的生活在这儿得到了草蛇灰线样的印证。故乡与童年是那么的强大,不管毕飞宇小说的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总是系在苏中的那块洼地上。我们不难从飞宇的回忆中寻找到他小说的蛛丝马迹。《写字》中在操场上以地作纸的男孩显然有着作者童年的影子,而蛐蛐这种小昆虫让作者那么着迷,以至作者后来直接用它作为小说的篇名,《枸杞子》中的手电也可能就是作家童年的家电,这一日常用品对作家的启蒙竟然涉及到了物理学中的光学和电学两大学科……如果不是故乡特殊的地理地貌,那一望无际的大水,也许少年毕飞宇对空间的想象不会那么深刻和强烈,直到成年后还会以《地球上的王家庄》的方式顽强地挣扎出来。毫无疑问,从现今的小说叙事中可以看出,毕飞宇的知识是丰富驳杂的,但乡土系列始终是他知识谱系中的强项,他说如果没有少年时代的经验和父辈的传授,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会写出像《平原》、《玉米》这样的作品。
在江苏作家中,毕飞宇是有理论兴趣的一位,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理论兴趣与他的写作联系在一起,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对自己作品的自我阐释,二是对自己创作的回顾与反思。应该说这两方面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都有所体现。看过这部带有自传意味的作品就会明白,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不仅是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性格、气质的形成,是不自觉的状态下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审美趣味的生发。某一天毕飞宇曾经对着就要落山的太阳给儿子讲解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小家伙的眼里闪起了泪光,他说他‘最不喜欢’,每天一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力气’。”毕飞宇为儿子的“少年愁滋味”,特别是这种滋味与夕阳在儿子心里产生的同构关系感到“骄傲”,因为“我的儿子拥有非凡的感受能力,也许还有非凡的审美能力”。他显然在儿子身上看到了他的童年,他的诸多感受力与生命体验不就开始于童年吗?毕飞宇至今还记得故乡破败的草房子——
每一座废弃的草房子都是地狱。它们没有屋顶,只有残败的土基墙。残垣断壁是可怕的,它们和家的衰败、生命的死亡紧密相连。本来应该是堂屋或卧房的,却蓬生蒿长了,那些植物像疯了一样,神经了,格外的茂密,格外的健壮。这茂密和健壮是阴森的,那是老鼠、蛇、黄鼠狼出没的地方,也是传说中的鬼、狐狸精和赤脚大仙出没的地方。色彩诡异的蝴蝶在杂草的中间翻飞,风打着旋涡,那是极不吉祥的。在我看来,蒲松龄的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的一件事,蒲老先生一定见过太多的狐宅和太多的断壁,哪一条断壁的拐弯处没有它自己的狐狸呢?在乱世,意外的死亡是常有的,悲愤的死亡是常有的,那么多的亡魂不可能安稳,所以狐狸的尾巴会无端地妖冶,那是冤魂的摇曳。
这里的回述当然带有今天的远观,但一个少年对死亡的体验,以及恐惧、灵异、毁灭、孤独等等最初的感受和想象确实都来自于那阴风四起、草木疯长的废置老屋。所以,生活对人的意义和影响从来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可以具体分析的。这不但因为生活总是具体的,而且,即使同样的生活,它也因人的不同而不同,还有,由于人的变化,它的意义可能还会被重新或不断被发现。就毕飞宇来说,《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所记叙的那一段生活对于他的意义直到他对文学产生了自觉的认识的那一天才被发现,因为“回过头来看,我愿意把那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看作我的文学课堂”。对这一文学课堂的学习内容,毕飞宇认为有这样几个关键,“对‘虚拟’的信任与虔诚”,“语言与‘虚拟’的关系”,“‘虚拟’与想象的关系”,“想象与语言的关系”,“什么是生活的真”,“价值观”。所有这些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它几乎是一个作家文学观念的全部,而这些,毕飞宇竟然在他的童年就获得了,起码奠定了其发生的基础。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这部有趣的关于作者往日的纪实性作品看成作家的成长叙事,同时又可以看作一部教育叙事。不过,这么看首先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教育。教育其实是很宽泛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狭隘的唯一的学校教育。如果按照这种狭隘的理解,那么毕飞宇这部作品中的许多叙述都称不上是知识,起码不是有用的知识,遑论教育?但教育就是在我们不以为是教育的地方发生了,而且,它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可能远远大于学校,重于老师,多于书本。可以断言,我们的一些家长会从毕飞宇的这部书中获得许多的启示,并由此调整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针。事实上,毕飞宇在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对家庭在其成长中的作用确实有许多的回忆与追认。他的记叙不由得让人想到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洛扎诺夫的观点,“家庭是真正的学校”。洛扎诺夫对当时的学校伤透了心,他认为孩子在学校里固然可以“学到精确的知识,会获得实用的技能或其他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是非精神性的,并不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而如果一个人不能确立做人的根本,那么知识与技能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倘若“所造之物仍未获得人的正确形象,在这个机制中,所形成的个人没有生命力,形象模糊、扭曲,虽然所掌握的知识是准确的、广博的,所掌握的技能是实用的,但也不会大展鸿图。受教育者身上没有形成一个重要的核心,以使这些技能得到有益的应用或至少得到保留,或使精确的知识再加以扩展并得到有效的使用。”换句话说,也就是德育首位。但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学校常常让人失望。洛扎诺夫当然没有看到,毕飞宇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在那时的学校,既学不到知识技能,而精神上的学习可以说是负性的。洛扎诺夫的解决方案是将“德育”这一块划给家庭:“只有家庭,也唯有家庭才能培养儿童最重要的文化品质,教给儿童最高尚、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规律的、宗教性的且富有诗意的东西。他不无绝对地认为:“个人正是通过家庭、而后才是通过社会同整个人类溶为一体并感悟生与死的奥秘。”他这样比较家庭与学校:“家庭唯一能给孩子的是使之健康成长,使之有信仰,使之处事认真,这就是给孩子工具,工具如同给旅行者一根手杖一样。如果家庭能做到这一切,就让学校给孩子其他次要的知识吧。”其实,这样的变通在任何社会和国家大概都是如此。当一个家庭对学校失望时,只能将教育的责任自己承担起来,这在国家与社会产生动荡或者价值失范的时候尤其如此。毕飞宇在作品中多次写到他的家庭,他的奶奶、父母和姐姐,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祖母对他的爱,体会到他的母亲对他的体面与尊严的教育。如何穿衣在母亲那儿都是大事,因为这事关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教养,孩子从小不能“一点学好的样子都没有”。做人完全可以从如何穿一双鞋开始。如何交友当然是大事,在母亲那里,这项复杂微妙的人际工程是从日常生活着手的,她只要暗示自己的孩子多与哪些小朋友玩儿就可以了。毕飞宇在作品中写到一个人,他叫黄俊祥。他是毕飞宇父亲的学生,学习成绩特别是语文成绩非常优秀,作文尤其得到毕飞宇父亲的赏识,但是这样的学生在当时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如果走不了“后门”是很难进入高级阶段学习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普及义务教育,初高级教育只有被推荐才能进入。而不幸的是黄俊祥不可能被推荐,他只能求助于爱他的老师,但毕飞宇的父亲虽然万般努力,却终于无功而返。毕飞宇在几十年后再次想到这个父亲当年的学生,他想到的显然不仅是黄同学的不幸,不仅是当年教育的落后与不公,更有一个落泊的乡村老师的情怀、人格,记住了黄俊祥实际上是记住了父亲对儿子善的影响。这样的事情与细节在作品中比比皆是,许多场景看上去并不是在写教育、写成长,但它们都与成长相关。还要提到洛扎诺夫的观点,他认为孩子的意志品质、行为习惯是“养成”的,而不是教成的,更不是用言语教育出来的。与学校教育不同,家庭是孩子生活的地方,享受快乐与亲情的地方,是他适性与游戏的地方,在家里,应该让孩子感到自由,在学校重视“类”的教育的情况下,家庭应该给孩子提供个性的保护伞。孩子的个性不是习得的,是慢慢长成的。对这样一个至今未解的颇为神秘的人才学难题,洛扎诺夫归之于上帝,至于家庭,就只管营造这样的温床:“家庭以无声无息的温柔关系和延绵不断的印象掘松和准备好了土壤,虽然没能制造种子,但种子会悄然而来的。怎么来的?来自哪里?这是上帝的秘密,是培养所有杰出人才的秘密。”毕飞宇这样描写和“定义”他的父亲,“他身上有恐怖的、令人窒息的学究气,凡是他没有弄明白的问题,他可以不吃、不睡,成仙了一样。”毕飞宇的父亲是一位语文老师,“文革”使人文学科成了高危领域,于是他的父亲来了个“华丽的转身”,教起了物理。因为同样的道理,他的父亲对毕飞宇喜欢文学持反对态度。叙述毕飞宇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影响包括他父亲的语文出身,这种语文出身使他的儿子显露出了文字的早慧,早早地就在作文比赛中获奖。这种影响又在父亲的反对中,这种反对成为一种反作用力,使得毕飞宇更执著于文学。因为反对也是一种强化,“父亲无意间不停地强化什么,孩子最后就真的成了什么”。这种影响更在于毕飞宇“身上的偏执很像父亲”,“也喜欢空想,我也可以没日没夜地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们都是死心眼。我们还有外人所不能了解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都骄傲。”
可以看出,家庭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毕飞宇的少年生活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种延展。由家庭,他开始走进村庄,慢慢地小心地拓展着他的生活半径,这样的拓展如同中国画中的积墨法一样不断渲染出一种氛围,这样的氛围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一个孩子基本的人生意识,他的好奇,他的怀疑,他对生活的兴趣,他对劳动的理解和参与……这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必须遵循的精神。不妨拓开去说一说,《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给我们展示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都不是洛扎诺夫所说的学校的知识,与我们现今的知识体系更是有隔代之感。那些乡村的经验是知识吗?它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有用的吗?也许因为我与毕飞宇是同代人,所以阅读他对逝去的乡村生活的描写觉得特别亲切。这样的感觉除了有相似的经验外,代际间的身份认同也是原因之一。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一个人的生命内容的形成,他的生命年轮与精神标识。因为从知识学的角度说,一个人的生命具体说来就是他的习得,他的经验,这也同时就是他的知识。而说到底,一个人的知识不是抽象的,更不都是他从教科书上获得的学问,它总是与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相连,价值、风尚、技术、物质与趣味,既是空间的,更是时间的,既是可以说明的,更有无从说明的。所以,人与人的不同就是知识的不同。我曾就这个问题验证过一位也在阅读这本书的“八○后”,我问她你如何看待毕飞宇的童年,他的童年经验?你的童年又是什么?让你回忆,你会说些什么?她想了想说“猫和老鼠”、“小龙人”、“小虎队”、“超级玛丽”、“新白娘子传奇”、“流星花园和 F4”……这些就是她的年轮和生命教材,只有通过它们,她才能将她的那段人生完整地串连起来。她特别遗憾地说起她的父亲在某一个年份没有允许她看《新白娘子传奇》,这让她的人生少了一个节点,现在同学们回忆往事到这一年,她只能无话可说并且因此受到了同学们的奚落。她不无夸张地说她的这一段人生是无法弥补的空白!这就是一位“八○后”的童年,可能多少带有个体性与偶然性,但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可以由此对一代人进行猜想的。其实,这一代人的生活并不完全是电视与游戏和那些由虚拟与符号构成的世界,但他们的代际身份定位迫使他们对其作了选择性的遗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有一代人的成长资源,也有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从这些视角看去,我们与他们的差别实在太大。不管我是不是抽象了他们,我还是倾向地认为我们的童年更丰富。这不仅是因为学校教育占去了他们太多的时间,也不仅仅是因为升学的压力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正在从他们脚下将大地抽去。一个人的童年,一个人的成长最好要与日常生活相关,尽可能完整地参与到日常生活中去。一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看法不能仅仅来源于书本,而是要形成或验证于他与自然的关系,与生活的互动。他要与天空、大地、河流、乡土植物,与人们生存不可分离的动物们建立友谊,与四时节令、油米酱醋挂上钩。人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带着质感与气味,甚至是肌肤相亲,用句俗话说就是接地气的。少地气的生活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也许,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不会看出来,但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如何让孩子们拥有全面、健康、自由和自然化的生活,是一个问题。
话再说回来,当我们感念我们童年生活与大地肌肤相亲的同时,那个时代的严酷,它对我们的伤害又让我们不寒而栗。因此,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是当毕飞宇开始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他该如何书写这一面?如何在纪实的层面开启他的“文革”叙事?讨论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倒过来读,从第七章“几个人”读起,比如陈德荣。陈德荣是少年毕飞宇的朋友,但是,这对本来非常要好的朋友却因某一天陈德荣“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某一天已经是一九七六年的十一月了,从中国的政治日历来说已经是“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陈德荣却因为被老师批评为“搞‘四人帮’”而干了件他以为是“‘四人帮’该干的事”,在公社的门口写上了“反动标语”,陈德荣成了“现行反革命”。陈德荣被开除了,但开除了的陈德荣却不许离开学校,而要供“中堡中学大批判小组”批判。毕飞宇荣幸地成为大批判组的成员,他要参与到批判好朋友的“十大罪状”中去。分配给少年毕飞宇的具体任务是《陈德荣是一个惯偷》。毕飞宇怎么写这篇“大批判稿”呢?“简单地说,栽赃。我所写的东西里头没有一样是真的,大批判小组里头的‘十大罪状’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栽赃。很奇怪,我们都清晰地知道我们在栽赃,但是在那样一个特别的语境里,栽着栽着,不知道自己在栽赃了”,他“唯一担心的是我的栽赃‘不够’:‘不深刻’,‘不全面’”。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这一篇的语言风格稍稍有些特别,毕飞宇尽量多地使用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语汇,尽量完整地再现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因为,“我想说的是,十二岁的孩子也可以很迷狂,十二岁的孩子也可以很邪恶——我当年就是这样的。只要‘上面’需要,什么都做得出来,什么都敢。”他仔细地回忆自己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的表现,他的所得,他的兴奋。毕飞宇特别在意自己的感受,一是“我清晰地感受过我在邪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二是“随着陈德荣的被‘定性’,我一阵轻松,突然意识到我依旧是一个‘好人’,这个‘好’在迅速地扩张、膨胀,都接近‘英雄’了。我在刹那之间就建立起了巨大而又可靠的道德优势”。没有哪个少年没有做过荒唐事,没有哪个少年的荒唐事不能原谅,但毕飞宇没有。在等待了几十年之后,毕飞宇开始了对自己这一荒唐举动的反省和批判,这样的反省与批判甚至有些过度,他说:“无论如何,一九七六年,我十二岁,那是我人生中最丑陋的一年。”陈德荣虽然原谅了当年的小同学,但毕飞宇却没有也无法原谅自己,因为今天的反思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反思,是一个有了许多丰富的社会与人生阅历的人的反思,是一个对中国传统、中国现当代史、人性等等有了认识后的反思,是一个作家的反思。这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少年对朋友的道歉。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一方面当然可以认定事件的荒谬,可以庆幸这样的事件在毕飞宇其后的生活中没有重复,但是另一方面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发生在那个岁月那些少年身上的必然性,更应意识到它可能重复的必然性。“那样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做了,不,我不会这样说。这样说是很不负责任的。我愿意相信,那样的事情我依然有可能再做,因为胆怯,因为虚荣,因为贪婪,因为嫉妒,因为自信,因为不可思议的‘一个闪念’,都有可能,只要外部提供充足的条件。”这是一个章节,但已经足够说明毕飞宇纪实层面的“文革”叙述策略,他在意的是那场运动背后的力量,乃至无意识的力量;在意的是那场运动与人内心的关系,与人性的关系;在意的是那场运动的影响,它不死的幽灵和与人心的默契以及不可预期的合谋。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的阴影不仅笼罩了毕飞宇此前的岁月,而且还将继续投射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难怪毕飞宇要将这一章放在最后作为全书的休止符。
问题是,这是毕飞宇对自己的批判,他的自言自语,还是与《平原》、《玉米》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文体的特定题材的创作,抑或是他对孩子们回忆他童年的故事?如果是前两者,这部作品可能是另一副样子。但毕飞宇这次是为今天的孩子写的,他“希望孩子们能够阅读这本书,毕竟,这是书写童年和少年的”。“我多么希望我的书能得到这样的评价:你给孩子们送来了一样好礼物。”他必须选择,节制,他不能让今天的孩子来为他背负这罪恶的包袱。他“不希望自己写一本泪汪汪的书。我不是个那年纪的人了,退一步说,我在心理上也不习惯那样。所以,留给作者、也就是我自己的,其实只有克制。”而且,不仅仅是自我的克制,毕飞宇还要面对人们的认识惯性,因为对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来说,“文革”,早已被抽空、定性和概念化为“贫穷”、“苦难”、“罪恶”、“残酷”、“苍白”的一段历史。如果你试图以另一种风格去叙述可能会遭受质疑甚至严厉的批判,将冒着美化“文革”的巨大风险。而事实上,美好、诗意与善良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不管在哪种环境中,孩子们都要成长,也都在成长,都有他们天真的童年。因此,毕飞宇如果试图写出他的童年,写出他童年眼中心里的世界,他首先要从成年中抽身,将成年后所感受和接受的对那段历史的通行说法放到一边,或者小心地区别开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到过去,将旧时光重新来过。一旦如此,一旦忠实于自己的童年,你就会发现,天真、幼稚、懵懂无知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会将严酷、罪恶与苦难,将成人阴险、复杂的世界摒除在外,孩子们会享受到令成长惊讶的欢乐。毕飞宇这样辨析道:“作为一个出生于一九六四年的中国人,一个倒霉蛋的后代,在他年近半百并回首往事的时候,苦难感已经成了他的逻辑性感受,这是一种‘长大’的感受,也是一种‘长大’的判断。但是,在他的童年与少年,因为没有比较,因为天性烂漫,他不可能去‘感受’苦难。他欢天喜地的。真的,欢天喜地。”也正因毕飞宇这样的策略,如今的孩子们才能看到他们前辈们真实的童年,而且竟然发现,他们的长辈们确实生长于一个疯狂的时代,一段贫困的岁月,但是,他们也逃脱了现在孩子们面临的困境与压力,享受到了如今孩子们可能也永远享受不到的自由和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的“文革”叙事应该有两个维度,既有成年后对那个年代的反思和批判,又有避开既成观念对苦难时代诗意的打捞。
本来还想对《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叙事风格做些具体的描述,恰巧在写作本文时看到了对它的批评性意见,其中之一是它的议论。“各种各样的言论随时从行文中跳出来,打断进行中的叙事,终止流动中的情感,并把一切可能引向宽广深邃的东西阻挡在外,让作品显得局促而散碎。”尽管是对它的批评,但不能不说是抓住了它的特点的,甚至是抓住了毕飞宇作品的特点。不仅是这样的纪实性作品,就是那些虚构性作品,毕飞宇同样表现出议论风生的特点。议论,已经成为毕飞宇的风格性标志。因此,与对他的批评不同,我以为,要从毕飞宇的叙事风格、叙事策略,乃至话语方式上去理解这一特点。一旦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议论就不仅是与说明、记叙和抒情一样的内容与方法,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是一种“腔调”,离了它,就没有了文学的毕飞宇,毕飞宇就不可能进行文学发声,所以,议论在毕飞宇的文学世界中是具有本体论的地位的。议论,在毕飞宇的作品中既是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的语言板块,但更多的是与其他话语渗透、交叉、纠缠在一起不可析出的。随便从书中节录一段:
锡匠很特殊,有点像吉卜赛人。他们居无定所,通常在船上。他们在我们村的大头上一停就是一两个月,有时候,他们一两年都不来一次。他们永远是神秘的客人,除了做生意,他们不上岸。他们是孤独的,为了对付自己的孤独,他们喜欢搭伴,两家,三家,四家,但不会更多了。他们没有名字,他们的名字一律都是“锡匠”。
这是叙述还是议论?应该两者都有,它既有事实的呈现,人物的行动,但又有对事实和人物的思考、评价。正因为这样的特点,我将毕飞宇的叙事统称为“分析性叙事”。所谓分析性叙事就是在叙述时加进了叙事人的观察、思考和评价。这样的叙述语言不是客观的呈现,它的功能与信息不止于叙述事情的进程,描写事物的形貌,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融入了叙事人或作品中人的感受、体验与观点。如果仔细分析,这种融入一般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带有主观色彩的语言去叙述客观的事物,二是以镶嵌的方式将评论与分析语植入叙述当中,三是将叙述语与作品中的人物语言结合起来,甚至干脆以人物语言替代叙述语言,四是在叙述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进入补充,进一步对叙述对象进入评价。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我只想从性质与功能上对这一风格做些强调,即这样的风格与作品的叙述策略非常契合。它不但突显了作品的话语特征,而且深度地介入到作品的进程,促进了话语的增殖、繁衍,而话语的增殖与繁衍则给故事与人物关系提供了丰富性与可能性,抻大了作品宽度和厚度,而在本质上,它体现了毕飞宇的世界观和毕飞宇与对象的关系,是毕飞宇对世界的力的介入。对毕飞宇而言,世界,只有在他的思考中才能存在,才能呈现。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改定于龙凤花园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基层创作生态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3JDA0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重建与新世纪乡村文学新变》(项目编号:13BZW13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苏地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1ZWB00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规划基金《新世纪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YJA75102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