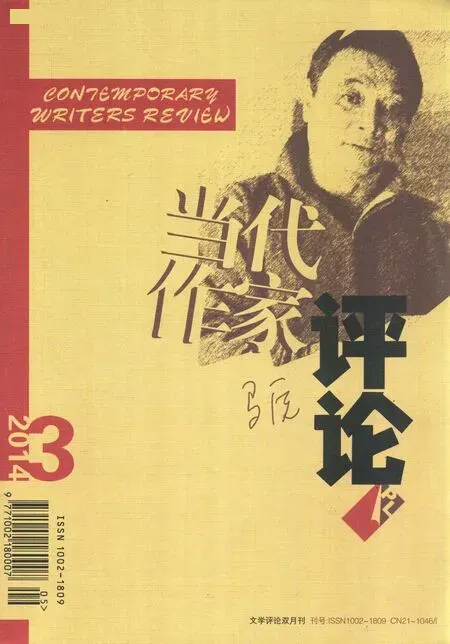马原《纠缠》和《荒唐》读札
张光芒
一、一场“重新开始”的战斗
读罢马原新作《纠缠》和《荒唐》,英国思想家阿伦·布洛克那一句话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他说人类解放自身的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显然,作家写小说也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的对象就是作家置身其中的生活,而战斗的成败取决于小说是否抓住了生活,取决于作家审美主体是否克服了生活的挑战。二十年前,马原不会纠缠于生活本身,而只会借其先锋意识纠缠于叙事的圈套。但二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与人性嬗递,使生活本身变成了一种重重叠叠难以名状的圈套,它让任何基于先锋姿态的形而上的求索或者灵魂的高蹈都难以下手。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连他在场的生活都捉摸不透,何谈个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如果一个小说家只能在历史题材中寻找灵感以回避当下的问题,或者只能徘徊于现实的表象世界而不触及生活的本质,又有多少审美创造性可言?的确如人们注意到的,最近两年,生活“倒逼”作家采取“正面强攻”的姿态,重新调整文学与当下的关系。一批八十年代成名的重要作家,如贾平凹、余华等,自觉地承担起重新定义小说与重新定义世界的双重使命。
在这一潮流中,重返文坛的马原“重新开始的战斗”意识可以说既突出又独特。与余华《第七天》极言生活之荒诞不同,马原笔下的荒唐更多悲喜剧相交织的意味;与贾平凹《带灯》尖锐的批判性不同,马原的小说似乎不急于从生活中超脱出来,其叙事立场和叙事伦理更多地纠缠于对生活真相的展示之中。马原的重新开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近年流行的底层写作或者官场叙事不同,他是回归自身深有体验、最为熟悉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生活领域,这样也同时有利于与上至官场下至底层的生活相交集纠缠。其二,与呼声相对较高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者象征性写作不同,《纠缠》和《荒唐》的叙事回归原始的讲故事方式,这样也便于调动笔墨以最大程度地聚焦于生活真相的揭示;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叙述者卸下了对于世界的先验观念和对于人生的价值设定,一切都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纠缠中展开和流露,有关善与恶、美与丑的纠缠也不复是先入为主的或者想当然的道德判断,而是更多地交给人物去感受体验,更多地带有伦理探索的色彩。
缘于这样的写作意识,《纠缠》与《荒唐》展现出来的审美世界,对于作家主体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进行时”,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敞开了的生活,而对于生活本身来说,则表现为深入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之中的人生形态。在我看来,无论是“纠缠”,还是“荒唐”,这两个意象均非单向度地指涉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而包含了对于社会与人生、人性与存在的综合性的反映。
二、人心的纠缠与生存的真相
当归来的马原将审美的光圈聚焦于以姚明与姚亮、黄棠与洪锦江为核心的中产阶层家庭及其生活时,这个选择本身便透露出作家与众不同的个性旨趣与创作动因。这两个家庭既有官员、教授、老板、高级经理人、富二代、官二代等这样常常被媒体妖魔化的人物形象,也有违法飙车、跨国投资、超生移民等诸如此类遭人痛骂的社会元素。惟其如此,当下写作中凡是涉及到这一阶层的生活描写往往处于两种极端。一种以欣赏的姿态描写成功人士的成功伦理,表现中产阶级趣味与中产阶级景观;另一种则持批判性的立场,对这一阶层进行简单化的想象与以偏概全的道德抨击。前者以“八○后”作家的都市写作居多,后者则每每出自以民间立场自居的作家之手。甚至在有些作家看来,对于当下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功能惟有“底层叙事”堪以担当,因此常常以弱势群体为关注重心,但有时候因为生活体验的不足,难免陷入为底层代言的身份尴尬之中。
其实这些倾向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偏见。正如西方现代社会理论所认为的,作为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向上下两极分化的阶级,中产阶级是促进社会发展,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功能的社会主体力量。马原的小说告诉我们,如何定义中产阶层这一概念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样一个阶层或者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整体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也是包含了各种复杂情状的一个大群体,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当下生活许多典型性的和本质性的层面,更非简单化的或者妖魔化的想象可以概括。
于是,我们看到,从中产阶层的生活本身出发构成了马原新作进入生活肌理从而揭示生存真相的唯一路径。《纠缠》一开始就让大学教授姚亮遇到了两个“特别特别闹心”的麻烦。一个是大麻烦,来自前妻的电话,话题事关他在上海的那套大房子的权益归属。另一个是小麻烦,已经鳏居三年的八十七岁的老父亲仙逝,需要赶赴深圳奔丧并处理父亲遗嘱、遗产问题。大麻烦难以解决,只能先全力以赴去面对这个小麻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这只能算得上是个小麻烦,却依然让姚亮与姐姐姚明陷入了接踵而至、无穷无止的纠缠之中。
应该说,《纠缠》绝无意于通过一些离奇的情节以制造矛盾冲突。这两个麻烦是任何一个有一定地位和财富积累的中年人都有可能面对的问题。这两个麻烦,一方面涉及到人与物、人与财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涉及到人与社会、人与体制的关系问题,而这两个层面又都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展现出来。与过去无财产时代或私有化水平较低的时代迥异,商品经济之下,金钱欲望的膨胀、物质的发达、制度的延展与细化,这些方面在给人带来满足的同时也反过来形成禁锢人们的枷锁。小说结尾处,就在姚家姐弟历经重重困苦,感觉总算可以完成父亲遗愿的时候,突然又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她带了全套的身份证明,自称是他们的母亲褚克勤的女儿,是褚克勤参加革命之前在老家生的女儿。看来,一场新的麻烦又不得不接着上演了。这一情节设计强化了这样一种让人深陷牢笼的无奈之感。一个知名度颇高的教授不得不深陷这种毫无意义的牢笼中无法自拔,而姚明这位拥有万贯家私在商界如鱼得水的女强人,竟也因此中风失忆,差点儿葬送了性命。
有种看不见的秩序一直存在着,严密地禁锢着你。但看得见的秩序却似乎一直在变,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了秩序。《荒唐》中就写到了“国五条”的出台竟然在机关引发了包括离婚潮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连锁反应。在另一处,静棋说道:“我早看透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在卖。”不是卖这个就是卖那个,不是买进来就是卖出去。而所谓白领,不过就是“帮公司卖货品,帮自己卖萌邀宠”。静棋之所以做底薪只有一千五百元的售楼小姐,唯一的动力便是将“自己一次性卖掉”,即寻找机会在高档楼盘里钓到金龟婿。作家借小说人物之口慨叹曰:“我真想找一桩不必去卖的事情,可是找来找去发现根本就没这样的事情。”
三、荒唐的逻辑与人性的畸变
如果仅仅是描写出物与物化制度对于人的束缚,那也只是批判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揭示的那种“冷冰冰的社会机器”,尚不足以透射当下中国生存真相的人心文化层面。《纠缠》也好,《荒唐》也罢,进一步揭示出的是人心异化与人性畸变的纠缠。物与欲望对人的异化及其所带来的人性的畸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文化潜流,它潜在地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社会潮流所向。姚亮与儿子姚良相之间本来有着父子情深的前提基础,姚亮与前妻范柏之间本无必要恶语相向,是房产证上的名字激发了物欲,异化了人伦情感。
细读《纠缠》你会发现,一条条荒唐的逻辑线清晰地展现在面前。姚明的父亲姚清涧立遗嘱,在他死后属于他与先他而去的老伴的全部遗产捐献给他的母校。但因他在生前不愿接受老伴已死的事实未及时申报,结果在死后被社保中心告上了法庭,指控的罪名是隐匿死亡事实,以冒名领取养老金来达到恶意侵吞国家财产的罪恶目的。因父亲已死,第一继承人便成为被告。姚明、姚亮二人,不抱私心,一心只想及时将遗产变现然后全部捐赠以完成父亲遗愿,却遇到了重重的波折和阻挠。拟接受数百万捐赠的檀溪小学校长覃湘,在法定程序尚未走到他的时候,便急不可耐地去找姚明抢夺遗产处置权。正是这位不速之客的嘴脸,强烈刺激了姚明,使她突发脑溢血。小说逼真地描写了她的心理感受:姚明忽然间觉得全身的骨头缝都在疼,忽然一切都崩塌了。父亲的美好意愿,她和姚亮对父亲的全力支持,许久以来她为此付出的全部热情和努力,忽然都崩塌了。
《荒唐》的故事伊始,洪锦江便遭遇碰瓷并引起了一场连锁反应。碰瓷的麻烦也正源于权欲带来的人性之堕落。官场之险恶无非是人心之异化的表现形式。尤其重要的是,《荒唐》进一步揭示出生存状态背后荒唐的生存逻辑,以及这种荒唐逻辑诞生的必然性。作为一名较为清廉自律的官员,洪锦江始终小心翼翼,但仍然遭到污蔑毁害,在遭设计被碰瓷后,有人要通过网络致他于死地。他本来坚信“我不怕谁查,身正不怕影子斜”,然而在现实面前,他终于认识到,网络微博这个可怕的东西,有无风起浪无事生非之奇效,它“会让身正不怕影子斜这样的民间智慧也相形见绌”。问题是面对这样的难题困境,他竟然束手无策;反倒是在他看来不成器、不上进的十七岁儿子洪开元信心十足。他迅速地利用网络和各种手段调查对方的违法证据,救父亲于危难。对此,黄棠看得非常明白:“别说他是个坏人,他即使不是坏人,为官这么多年,要查出他违纪枉法的事情,肯定也一查一个准你信不信?”让人听来不禁齿冷。这种奇特的逻辑一旦成为规律和常态,那就表明这个世界的运转系统出了问题。
在飙车案事发面临监禁之刑罚的关口,洪开元依然不按常规出牌,以攻为守,设计以滥用职权的罪名反告交警大队,最终逃脱了惩罚,让人不得不佩服他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本事。如果说前者还算是以恶抗恶,那么后者只能说视法律如儿戏,但是只要抓住了社会运行的逻辑,再荒唐的事情也会成为现实。而只要荒唐的逻辑大行其道,人性的畸变必会像决堤的河水样疯狂泛滥,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和凝固荒唐的现实逻辑。
四、当代人的自我救赎
在更多的时候,揭示生存的真相总是比试图通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更为重要。当年鲁迅之所以秉承“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思想,盖因在当时整个知识界并不能看清楚国民性的真面目,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不啻是一种妄谈,此时,对于病状与病根的诊断不仅是基础性的工作,更是时代性的大课题。对于小说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来说,尤其如此。当马原的小说在人心的纠缠与人性的荒唐这样不同的层面发现问题的症结的时候,叙述者其实已经为人们预示了疗救的方向,那就是无我之爱的灌注、打通人心沟通的路径以及恢复人性的尊严。
马原审视现实的笔触虽然不无冷峻之气,但与此同时他并未忘记以善意和温暖的眼光去打量中产阶层身上所葆有的那些爱与美的元素,触摸人心最柔软的部分。《纠缠》中,姚亮与姚良相父子俩长期的对立情绪,儿子对父亲多年的冷暴力,最终得以解决,正是源于父亲对于儿子深藏不露的爱,也源于儿子既发现了父爱的无私,也发现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荒唐》中,罹患脑瘫达一年之久的黄棠竟突然痊愈苏醒,亦源于丈夫的无我之爱。这正是康德哲学意义上对爱的信仰,是一种为爱而爱的形而上境界。
《纠缠》中,姚明与姚亮在处理遗产的过程中,自称是他们同胞大哥的吴姚的出现一度引起重重波折,深有意味的是,僵局的打破归功于突发脑溢血后一直神志不清的姚明。也许,当人类卸下所有的物欲,面临生死的终极关口时,才是最富有人性也最具有人心力量的时刻。当姚明重新站了起来,我们发现,爱、信任、沟通与人性的恢复,不仅是对抗一切禁锢的最坚定的力量源泉,也正是现代人自我救赎之途。
(本文获韩国外国语大学二○一四研究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