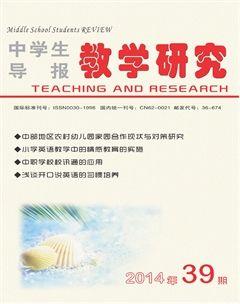论卞之琳早期诗歌对北平的独特情愫
程娜娜
摘 要:卞之琳早期诗歌多写故都北平城郊内外,呈现出与35年后“知性”诗风不同的审美趣味,体现了京派文人独特的文风与情怀,也显示了都市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卞之琳;诗歌;北平
谈到卞之琳,很自然会联想起他的成名作《断章》,充满哲思、“知性”的诗风是读者对其的普遍印象。实际上,诗人前期关于北平的书写占据了其诗歌创作的很大一部分,与其35年后成熟、复杂的诗歌相比,可谓“冷淡盖真挚,玩笑出心酸”,体现了诗人独特的才华与北平情愫。
卞之琳晚年回顾中,将其战前诗分为三个阶段,即:(1)1930~1932年;(2)1933~1935年;(3)1937年。第一阶段是在北大读书时,其诗多写故都风物。第二阶段是游踪逐渐流动、风格趋向变化的“上下交结、前后过渡”时期。第三阶段则是1937年春天在江南的几个月,继续了前一时期的转变。[1]江弱水在他的研究著述《卞之琳诗艺研究》里將卞之琳1930~1934年的诗歌归为前期创作,指出自1935年起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开始由早期的情景的写实转向观念的象征。笔者在这里主要参照江弱水先生的划分法,重点分析卞之琳1930~1934年有关北平书写的代表性诗歌。
纵观卞之琳1930~1934年的诗歌,笔者认为其对北平的独特情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浓郁的北方地域色彩
这一期间的卞之琳为中国新诗史增添了许多具有北平人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一个闲人》里刻画了一个街头路边手叉在背后的闲人,“轧轧的轧轧的磨着,磨着……唉!不知磨过了多少时光?”[2];《一个和尚》里勾勒了一个懒洋洋的和尚,“一天的钟儿撞过了又一天”“一声一声的,催眠了山和水”[3];《酸梅汤》里描写了一个生意惨淡的人力车夫调侃同命相怜的卖酸梅汤老头的场景,将一个安于现状、穷作乐的北平小市民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过节》里自我独白性的语句“账条吗,别在桌子上笑我,反正也经不起一把烈火,管他!到后院去看月亮。”[4]更是将一个乐天派的北平人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诗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也是近乎相同的,“无望、无告、无聊、无奈”[5]。外界的战乱、故都的衰败似乎影响不了他们,他们依然在麻木、愚钝中过着平常往复的市井生活。《胡琴》里一个青年在冷静的街头拉着寂寞的胡琴小调;《酸梅汤》里生意惨淡的老头,一句话不讲,倒像生谁的气;《西长安街》里的黄衣兵低声无语,却思念故土。少言、无言似乎成了这些小人物共有的特征,昏昏欲睡的萎靡状态似乎成了他们逃离现状的一种方式,无疑具有讽刺意味。
此外,除了对人性的挖掘与玩味,诗人还十分注重对30年代北平底层小人物生活现状的考察,体现了诗人关怀人生、体恤民众的情怀。且看《苦雨》[6]:
茶馆老王懒得不开门;
小周躲在屋檐下等候,
隔了空洋车一排檐溜。
一把伞拖来了一个老人:
“早啊,今天还想卖烧饼?”
“卖不了什么也得走走。”
诗人由近及远,将北平街头的一角描写得真实入微,再现了北平底层民众的坎坷生活境遇。“茶馆老王懒得不开门;小周躲在屋檐下等候,”一个“懒”字,一个“躲”字,形成强烈的心理反差,讽刺了有钱人的奢骄,流露了对贫苦百姓艰辛境遇的怜悯之情;“一把伞拖来了一个老人”的“拖”字,很生动地暗示了老人身体的瘦弱,下文戏剧性的回应“卖不了也得走走”则道出了人间无尽的心酸与无奈。
卞氏的另一首诗《几个人》则更全面地描绘了北平市井的众生相,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常态:贩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在吆喝中吃了满口的尘灰,提鸟笼的小市民在悠闲地望着天上的白鸽,卖萝卜的挑着一担萝卜在菜场上空挥着手里的小刀,矮叫花子蹲在街角痴眼看着自己倒映在阳光下的影子。有些人生来挨饿受冻,有些人却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正如诗中所写的“有些人捧一碗饭叹气,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一切都是这么静悄悄而又死气沉沉的在北平上演着,诗人笔下的北平市井是灰蒙蒙的、了无声息的,是寂静的又是冰冷的,全诗借一个沉思着的年轻人的视角将北平市井的众生相冷冰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禁令人唏嘘长叹。
可以说,卞之琳前期创作的诗歌是30年代北平的缩影,多写北平街头小人物、描绘市井百态,注重选取具有北平特色的吃食和景物入诗,如酸梅汤、冰糖葫芦、长安街等,偏好“秋天”、“夕阳”、“黄昏”等清冷意象,整体创作呈现低沉、荒凉的色彩,文字朴实无华且蕴藉深厚,体现了诗人对北平复杂而又独特的情愫,呈现出与后期创作风格迥异的审美特色。
(二)复杂、深厚的情感
卞之琳对北平的独特情愫不仅表现在其诗歌蕴含的浓郁的北方地域色彩,更体现在其对北平的复杂、深厚的情感。这种独特的情感我们可以通过品读他充满戏谑意味、耐人寻味的长诗《西长安街》来理解。
第一部分作于1932年9月。诗人一开始就写了三种影子,枯树的影子、老人的影子、手杖的影子,并用“斜斜的”“淡淡的”来修饰,营造了一种时光的恍惚感,带有一种秋的悲凉、凄清的气息。接下来,笔锋一转,写到晚照、红墙、墙外的蓝天、北方的蓝天,选取一些具有北方特色的景物,把人带入一种静穆、闲适的美景之中,流露了诗人对北平固有风韵的留恋与追忆。这里,诗人用“长”写了很多景物,“影子、红墙、蓝天、道路、冬天”,体现了诗人对古都风韵的追忆。
第二部分写于1933年5月,诗人以一种激昂的情绪进入一种幻想中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威武、霸气的场面,流露出诗人对皇城昔日辉煌的回忆。接着,幻想跌入现实,眼前是一派荒芜、改朝换代的时代:“黄衣兵站在一个大门前,他们像墓碑直立在那里,不作声,不谈话,还思念乡土,东北天底下的乡土?一定的”[7]。前半句“墓碑”一词极其讽刺了黄衣兵沦为亡国奴的可悲姿态,暗讽了士兵的麻木,后半句则以滑稽可笑的语言“不作声、不谈话”将其讽刺力度进一步强化。
接下来,诗人采用“家园的井旁、家鸡、彷徨”等清冷的意象以及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语,描绘了北平在经受“九一八”事变后衰败荒凉的景象。“哪儿是暂时的住家呢。”一句借用王独清《我从CAFE中出来》中的诗句“向哪一处走去,才是我的暂时的住家……”进一步表达了士兵孤独、彷徨的心境。“什么?枪声!打哪来的?土枪声!自家底,不怕不怕!……”[8]与上文形成对应,嘲讽了士兵的胆小、懦弱。“蟋蟀”这一古典意象的引用,营造了一种愁苦凄清的气氛,与用“褪色”一词形容的“青纱帐”这样具有北方特色的景物对应,暗含了北平在遭受迁都、战乱后死一般沉寂的世界。“明天再想吧,这时候只好不作声,不谈话。低下头来”[9]再次与上文呼应,暗讽了士兵的悲哀、愚昧、得过且过、缺乏危机的心态。大敌当前,士兵们想的不是起身抗争,而是明天再想眼前的无奈处境,无不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在诗歌快接近结尾时,诗人将长街上略過的汽车与昔日的大旗对比,表达了对昔日北平皇城的吊唁与追忆,“红门”正对着“朝阳”,如今只能怅然望着秋阳了,给人一种悲凉、凄清的气氛。
细细分析这首《西长安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卞之琳对北平独特、复杂的情感:既有对北平古韵的赏玩与怀念,又有对昔日皇权威严的北平的追忆、凭吊,还有对北平民众在大敌当前时的麻木、愚昧、得过且过的心态的讽刺。
再看他1934年作的另一首长诗《春城》,则是用嬉笑怒骂的语调表达了对北平复杂的情感。全诗采用“众生喧哗”的多声部发音以及戏剧性独白,揭示“边城”状态下京城没落的同时,又嘲讽了乐天派的北平人“穷作乐”的愚昧精神状态。
昔日在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映衬下的京城,如今在“垃圾堆”里消靡、沉沦。京城没有了似马德里蔚蓝的天,而是终日风沙肆虐,为此,民众的抱怨甚嚣尘上。这肆虐的风沙卷起了千年历史的尘埃,似马、似狼、似虎,满街跑,满街滚,满街号,往街头窗口与屋角狂啸。
接着,诗歌由北平的狂沙纷飞写到北平人在战乱下的怡然自得、无所事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似乎没有给这个古城带来多大的危机感,且看民众打哈哈的语调:
“好家伙!真吓坏了我,倒不是
一枚炸弹——哈哈哈哈!
“真舒服,春梦做得够香了不是?
拉不到人就在车蹬上歇午觉,
幸亏瓦片倒还有眼睛。”
鸟矢儿也有眼睛——哈哈哈哈”[10]
……
日本飞机投下炸弹似乎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一瞬间的吓坏后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笑了之。底层的车夫在拉不到人的情况下躺在车蹬上睡起香甜甜的午觉,国家的安危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在得过且过的日子里度过死气沉沉缺乏斗志的每一天。纵使是充满新生与希望的小孩子也和老头子一样,“想起了当年事”。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陈腔滥调响彻北平的街头巷尾,车夫们在调侃打趣儿里埋怨着北平的尘灰漫天,他们在自我安慰中惶惶度日,正如诗歌结尾写道的那样:
蓝天白鸽,渺无飞机,
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
决不忍向琉璃瓦下蛋也……[11]
就这样,日子能过一天是一天吧,暗含了当时北平城人们普遍的精神麻木与堕落。
反观卞之琳1930年—1934年创作的有关北平的诗歌,我们看到了北平都市文化的变迁给青年时期北上求学的卞之琳带来的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让我们感受到了卞之琳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京派文人固有的情怀,体现了他别样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情愫,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 卞之琳:《雕虫纪历1930~1958》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7页
[2] 卞之琳:《三秋草》,姜诗元编选,华夏出版社,第6页
[3] 卞之琳:《三秋草》,姜诗元编选,华夏出版社,第7页
[4] 卞之琳:《三秋草》,姜诗元编选,华夏出版社,第34页
[5] 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第20页
[6] 卞之琳:《三秋草》,姜诗元编选,华夏出版社,第35页
[7] [8][9]卞之琳:《三秋草》,姜诗元编选,华夏出版社,第31页
[10] 卞之琳:《三秋草》,姜诗元编选,华夏出版社,第58页
[11] 卞之琳:《三秋草》,姜诗元编选,华夏出版社,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