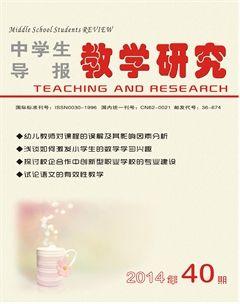论在生物学教学中开展伦理教育的可能
薛庆祥
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和深入,生物学研究已经逐渐具备了伦理学的视野。由此观之,中学生物学教学也应当具备这种视野,在进行传统生物学教学的过程中开展伦理学教育。从学理和现实两个方面来看,在生物学教育中开展伦理教育都具备了某种可能。
从学理的方面来看,在生物学教育中开展伦理教育已经具备了如下的可能:
一是科学哲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拓展了生物学研究和教学的内容、丰富了生物学研究和教学的方法。科学哲学虽然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但是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一般认为是自1883年出版的赫尔的《自然哲学研究序论》开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科学哲学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同时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且出现了历史主义的转向。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独特的贡献,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科学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马克思科学哲学的总体特点是反对实证主义,坚持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在科学哲学问题上,马克思坚持整体论的科学划界标准;承认科学有其独特的方法;赞成科学实在论,相信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承认社会科学也有规律。”①因此,中学生物学教学也应当相应地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拓展和丰富需要一定的限度,不能脱离教学大纲的要求和中高考的要求,否则就背离了中学生物学教学的规律。换句话说,中学生物学的研究应当在围绕教学大纲和中高考的要求之下,适当地兼顾科学哲学发展的新动向,采用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文史等学科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
二是伦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为科学哲学的前进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持。科学哲学的发展使得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产生了“联姻”式的关系,人文学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哲学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从加强中学生道德角度来看,并不是与科学哲学有关的所有人文学科都适合在生物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而伦理学则具有“先天”的优势,并且在科学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过,不同时代的伦理学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今天要提倡的伦理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十分强调人类生活的道德实践的意义,由此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必然是强调人类生活的道德实践的意义,而生物学教学也应当相应地强调相同的意义。
从现实的方面来看,在生物学教育中开展伦理教育已经具备了如下的可能:
一是生物学本身面临的伦理问题,使得生物学研究和教学者不得不思考相关伦理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哲学的出现和发展是与科学面临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生物学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克隆技术,对于伦理关系的研究恐怕不会像今天这样深入;如果没有战争中对于生化武器的使用及其严重的危害,恐怕也难以形成当前伦理和法律层面的种种共识和禁令。这一切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新的变化,DNA相關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把“双刃剑”,其在医学上的重大意义以及可能的危害和挑战,更是促使生物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思考相关的伦理问题,并且用伦理规范等来约束和调整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教学者绝对不能对这一切熟视无睹,而必须在中学生物学的教学过程中,在教授学生知识的过程中,及时将生物学发展所面临的现实的伦理问题引介给学生,并且帮助学生树立与社会主义伦理观相一致的科学的生物伦理观,进而为学生深入和独自学习、研究生物学提供一把能够解决伦理问题的钥匙。
二是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并且逐渐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使得生物学也融入了这种发展趋势之中。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了包括生物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理性的繁荣,消费社会的出现更加神话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异化”。在这个过程中,生物学及其衍生品无疑充当了商品的角色,成为人们“异化”的原因之一。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批判和对于工具理性、消费社会等的反思,人的价值得到了再一次的彰显,其直接目的在于企图以此来消解“异化”,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对于“异化”的反击并没有滑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而是走进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的发展道路。因此,生物学研究和教学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至少也应当在生物学教学的过程中,结合中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进度和对于传统文化的掌握程度,适时地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从生物伦理的角度开展对于“异化”的讨论和批判。
以上两个方面四种可能,不但从理论上证明了开展伦理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也从实践上指明了开展伦理教育的路径、方法和渠道。这对于丰富生物学教学、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的互动和融合、加强中学生伦理道德教育,以及帮助中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解:
①魏洪钟:《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及其当代意义》,《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