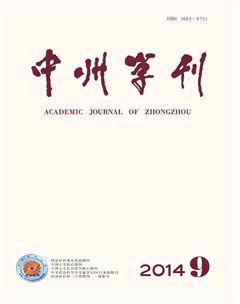血气重建:文艺家的自我救赎之途
李占伟
摘要:由于当下文化中工具理性、欲望主义、消费主义、道德无痛主义的大行其道,我们的文化事业中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深层次看,“三俗”文艺的泛滥,还在于我们时代的人和文化出现了深层危机,并根本遗忘了古典教诲中的“血气”。血气使人义愤、英勇无畏、充满正义之感、满怀悲悯之心。血气对于文艺家来说,便是文艺家的批判性、担当性、崇高性。恢复与重建文艺家的血气是抵制“三俗”文艺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文化危机;三俗;血气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9-0020-04
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的文艺创作在数量上翻倍地剧增,但文艺界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的氛围。“软骨病”“无病呻吟”“无节制叙事”成为批评家们的惯用语汇;“文化危机”“文学终结”“文学已死”成为文艺理论家们的口头禅;“庸俗、低俗、媚俗”成为学人时常挂在口头上的词汇。那么,导致文艺“三俗”泛滥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可资救赎的途径呢?
一、“三俗”文艺泛滥的深层原因
从哲学层面看,导致“三俗”文艺泛滥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
1.工具理性的强势僭越
启蒙理性、科技理性发展的逻辑必然就是工具理性的出现。然而,本来为人类所利用的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工具”,却潜移默化地僭越为了人类存在的目的。尤其是伴随着“电子媒介”的兴盛、“读图时代”的到来、“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开启,文艺、文化的存在样态变得越来越花样繁多,也越来越难以把捉。不可否认,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文艺、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也给文化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民主”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们的自由多了,自由精神却没了;自我选择多了,主体性却死了;个人主义实现了,个性却消弭了。”①人们在传媒工具面前,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庸俗化、简单化,文化事业有变成抓取人眼球的媚俗事业的危险。
2.欲望主义的甚嚣尘上
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巨变,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随着西方“反理性”思潮、解构主义思想、“身体”哲学、女权主义等理论的传入与影响,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对人类的统治也逐渐从物质领域扩展到了精神领域。“‘身体写作、‘美女写作、‘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人体摄影、‘人体绘画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术语、新词汇尽管各有侧重及其所指,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涉入一个共同的领域和话题,即欲望的书写、叙事、表现。”②诚然,对“身体”的发现、对潜意识欲望的挖掘可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更为复杂的人性,使艺术形象更为丰富和立体,使艺术空间更加丰满和充盈。然而,当欲望成了文化的主题,欲望化、感官化与商品化互相勾结之时,文化精神则沦陷为娱乐精神,文化理想则变成欲望之身,文化叙事则变成欲望叙事,低俗、庸俗也就不足为怪了。
3.消费主义的高调统治
法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鲍德里亚曾用“白色社会”来形容世界范围内消费逻辑的高调统治。所谓“白色社会”便是没有情感、没用温度、没有理想的社会。当商品成为人们新的宠儿、消费成为人们新的信仰,金钱自然就变成人们生存的终极目的。在众声喧哗、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文化出现“商品化”“利益化”倾向,变成无节制被消费的对象,也就难以避免。消费逻辑统治的必然逻辑结果便是,越来越多的文艺产品在产生之初便为着利益而来、为着金钱而来。这样的思考怎能不带来彻头彻尾的“媚俗”?又怎会有情感,怎会有温度和理想呢?
4.无痛伦理的大行其道
时至今日,人们的伦理在经历了德性伦理、宗法伦理(西方叫宗教伦理)、责任伦理之后,进入了个人无痛伦理时代。所谓个人无痛伦理,是指个体化的、多元化的、相对化的、包容化的、自由化的伦理。现如今,人们丧失了德性伦理,丧失了宗法伦理时代的道德休戚与共感,同时也抛弃了责任伦理时代的集体荣誉感,而进入了一种“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个体伦理无痛感。人们不需要向上帝负责,更不需要向集体负责,只需要对自己个体的“幸福”负责,完善自我幸福就是最大的“善”。在这种伦理原则的指导下,文化艺术中开始出现极端的自我倾向,“自恋式”的写作、“无节制”叙事、“虚假性”纯粹等不一而足。一些文艺作品没有了崇高,没有了远大抱负,没有了休戚与共,没有了人文关怀。
实际上,文化领域所出现的危机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紧密相关。相较于过去的所有时代,现代人创造了最为丰富的物质,生产出了最为高端的商品,生活因为这些东西似乎愈发安逸与快乐了。但快乐并不等同于幸福,现代人似乎并未因为上述成果的取得而更加幸福。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们因为欲望的张狂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伟大的抱负;因为物质的享乐而越来越没有英雄气概;因为价值上的虚无与真空而越来越没有道德上的休戚与共感;因为自私自利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担当感和责任心。“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③施特劳斯说:“根据经验或常识,每个社会都因其崇尚某种东西而获得各自的特征……每个人也因其崇尚某种东西而成为他自身。”④当前文化的“三俗”化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同形同构,都是因为缺乏伟大、崇高、勇气、担当。而“伟大、崇高、勇气、担当”正是古希腊哲学概念“血气”(thymos)一词的原初之义。换言之,正是由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化看轻或根本遗忘了“血气”,才导致现在的庸俗不堪。
二、文艺家血气重建
在西方,“血气”(thymos)作为哲学概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血气和欲望三个部分,其中,理性掌管人灵魂的高级部分,欲望掌管人灵魂的低级部分,而血气则掌管人灵魂中道德义愤、勇气、正义、公民友爱等精神。道德义愤是血气在人身体上的生理表现;勇气则是血气在精神层面的表达;捍卫正义是血气的本质内容;公民友爱则是血气的必然结果。而现代人要么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过于看重;要么则是对人的欲望过于高扬,却根本忽略了血气中那些可资抵抗庸俗、低俗、媚俗的义愤、勇气、正义和友爱。
文艺作品由文艺家所创作,文艺家的人文素养、道德涵养、哲学修养对文艺水平的高低具有决定性作用。若要抵制文艺的“三俗”,先要抵制文艺家的“三俗”;如要抵制文艺家的“三俗”,则应首先重建在许多文艺家身上已经消失的血气。从文学史上看,伟大的文学家都是血气充盈、超凡脱“俗”的。从屈原、陶渊明、杜甫、白居易到苏轼、辛弃疾、陆游,哪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诗人不曾发出忧国忧民的呼声?西方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等等,无一不是在为人的生命、尊严、美好情感、自由等精神奔走呐喊。而这些恰是文艺家血气的集中表达,也是文艺家避免堕入“三俗”的不二法门。但遗憾的是,这些精神在当代一些文艺家身上越来越难以找到,他们要么患上了对威权卑躬屈膝的“软骨病”;要么变成了自我书写的“自恋狂”;要么皈依了“商品拜物教”。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抵制“三俗”文艺,必须重振文艺家之精神,重建文艺家之血气。
血气精神中的道德义愤、勇气、正义、公民友爱之于文艺家的特征,我们可以用“担当性”“批判性”“崇高性”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没有担当性,文艺难以避免陷入自我叙事的低俗;没有批判性,文艺难以避免取悦大众的媚俗;没有崇高性,文艺也自然难以避免缺乏神圣之感的庸俗。
1.血气本性所带来的公民关爱表现为文艺家的担当性
关心民众疾苦,主动承担人民苦难,举凡有血气之人便会如此,好的作家更是血气充盈。“兴、观、群、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体现了古代文人的血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体现了现代文人对民众苦难的关怀与担当。作家张炜坚信:“体现文学本质的也许始终有这几个词,这就是:‘批判、‘底层、‘纯粹……是这些品质决定了它的挑战性,并因此而维持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⑤然而,中国当下的一些文艺家恰恰缺乏这种古典的文艺担当,因此其作品也大多是一种自恋式的叙事、无节制的狂欢,要么躲进自我臆造的私人空间里无病呻吟,要么露骨地描绘自己的私生活,要么夸张地刻画上层生活的奢华,要么平庸地在文学艺术中嫁接新闻事件。私生活、奢华生活、新闻花边生活,恰是低俗文艺描绘与刻画的基本内容,对这些内容的关注与描写也正是文艺家血气担当丧失的典型表现。故而,文艺要进行“低俗”疗伤的话,重建文艺家的血气担当应是必选之良药。
2.血气中的义愤表现为文艺家的批判性
司马迁在评价《诗经》时,认为其“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著书”遂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显说。这里的“发愤”便是指借助文学艺术抒发作者心中之义愤。义愤何来?不过是因遭遇不公、世事不平而在心里郁结的愤懑之情。奥地利作家卡夫卡通过其怪诞奇异的人物形象及故事的描写,深刻批判了西方现代性造成的人们之间冷漠如冰的人际关系;鲁迅通过其“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典型形象,深入批判了当时制度对人造成的异化以及国民的劣根性。这种批判是作家的良知使然,是作家的血气本性使然,一旦丧失,文学的真实性、深刻性将无从谈起。然而,目前中国的文艺似乎进入了一个批判殆无、媚俗成灾的时代:文艺圈的互相吹捧、媒体圈的兴风作浪、出版界的推波助澜,共同打造了中国文艺一个又一个的“媚俗”神话。对于如此媚俗的文艺圈,是时候给它增加一些古典“血气批判”的成分了。
3.血气中的勇气与正义表现为文艺家的崇高性
血气使人勇敢无畏,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对生命的不惜不是主动放弃生命,而是血气使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着“值得以死相趋”的高尚之存在,这种高尚之存在可能是自由、正义,也可能是最本真的人性,但超越生命的高尚绝然存在。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高级形态,更应当认可崇高、追求崇高,并时刻唤起人们心目中的崇高之感。可以说,文学崇高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浩然正气的体现,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站在全人类立场思考和写作的姿态表征,实际上也更是作者灵魂血气中的正义和勇气之心的精神表达。然而,文学艺术的血气崇高,在这个“庸俗”时代里也几乎被消磨殆尽。文艺不再是神圣不可亵渎的纯洁殿堂,相当一部分文艺家信奉“商品拜物教”,认为不管作品多么庸俗,只要能攫取经济资本,抑或是名誉资本,就是“好”作品。故而,深沉的作品越来越少,浮躁的作品越来越多;沉静的作品越来越少,喧嚣的作品越来越多;直抵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声色犬马的作品越来越多。故而,恢复与重建文艺家的血气崇高,对于抵制文艺庸俗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见,重新恢复与肯定人类灵魂当中的血气,使人血气充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拯救现代人精神的萎顿与颓靡;而血气之于文艺家、之于文学艺术的担当性、批判性、崇高性,对于抵制文艺“三俗”具有重要作用。
三、任重而道远的救赎之途
正如前文所论,血气的消弭殆尽、“三俗”的泛滥成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故而,文艺家血气重建的自我救赎之途也必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作为文艺创作主体的文艺家如何找回并长期葆有血气之担当性、批判性、崇高性,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文艺家应不断完善其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家无不是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这种独立精神,并不是要求文艺家“躲进小楼成一统”,也不是鼓励文艺家进行自恋式的叙事,而是要其磨炼一种敢于向威权说不、向世俗说不,敢于说真话、实话的勇气与坚持。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先生,曾用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海力布”来形容作为文艺家的这种独立精神。海力布能听懂鸟兽的话语,但不能泄露他所听到的,不然就要变成石头。他为了拯救村民,将山洪即将暴发的消息告诉了乡亲,他也因此变成了石头。“一个有着海力布般的无私精神,一个用自己的睿智洞察了人类面临着巨大困境的人,是不能不创作的;这个‘唯一的报信人,是不能闭住嘴的。”⑥莫言诚恳地践行了这种精神,其作品中有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反思(如《蛙》),有对土地改革“一刀切”的强烈质疑(如《生死疲劳》),也有对官僚腐败作风的戏谑调侃(如《酒国》),更有对政府不作为的直言鞭挞(如《天堂蒜薹之歌》)。这与当下一些文艺家要么卑躬屈膝地臣服权贵,要么无所节制地攫取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当下文艺家要不断完善其独立精神,唯有人格独立、精神独立,才能不需要用作品取悦谁、讨好谁,才能使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而免于媚俗。
2.文艺家应不断加深其人文关怀的深度
文学艺术是属“人”的,是指向人、服务人的,故而任何文艺家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必然都有对“人”的关注。文艺家关切与关怀“人”的层面不同,直接决定了其文艺作品的水平高低。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生存需求由低到高排列了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带有“三俗”倾向的“文艺家”基本关注的是人的动物性层面的生理、安全需求,故而其作品充斥着色情、暴力、凶杀等内容;带有“通俗”特质的文艺家则多半关注的是人的基本情感需求,故而其作品带有明显的娱乐性、休闲性等特征;而具有“脱俗”(高雅)特质的文艺家关注的则是人的自我实现、尊重等高级别需求,故而其作品包蕴着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幸福、自由等的深沉思考。所以,文艺家唯有不断加深其人文关怀的深度,不断加强其对“人”思考与关切的力度,才能使其作品有自觉的担当性而免于低俗。
3.文艺家应不断提升其哲学思想的高度
哲学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属“人”的,但其与一般人文学科关注人的角度和方法不同。首先,哲学视阈下的人是大写的“人”,也即是说,哲学关怀的是普世的“人”,而非某一个人、某一群人,它自然具有一种“全人类”的视角,希冀探索出全人类共同幸福的规律。伟大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孔子、庄子等莫不如此。其次,哲学对人的关心是终极性的、彼岸性的,而能够给世俗之人提供彼岸之思的还有另外两样东西——宗教与文学艺术。诚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每一位艺术家都成为哲学家,但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应当具备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问题的视角。让我们来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便知一二。1915年在颁奖给罗曼·罗兰时,瑞典学院对其这样评价:“赞扬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的理想主义和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⑦1950年颁奖给罗素是“表彰他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自由思想的多样而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⑧。1964年颁奖给萨特是“由于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充满自由的精神和对真理的探索,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⑨。这些伟大作家的共同特质,便是具有普世关怀的哲学高度。另外,因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三者在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彼岸之思上具有相通之处,文艺家应当不断提升其作品的神圣性、纯洁性。即是,文艺家应当把文学艺术奉为自己的崇高宗教,不忍亵渎。故而,文艺家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哲学关怀高度,以文艺为信仰,才能使其作品葆有神圣的崇高性而免于庸俗。
其实,面对“三俗”文艺,作为文化参与者、文艺接受者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们爱自己胜过爱文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幻想、窥视欲、追富梦等感官需求,我们主动地去阅读和消费“三俗”文艺,为其提供了滋长的土壤与市场。沉迷于此的人们,是不是也应当重新找回自己弄丢了的血气,而变得有道德义愤、正义之感、关爱之心呢?
注释
①张光芒:《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昆仑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②李鲁平:《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解》,《文艺报》2005年12月22日。③[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页。④刘小枫主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2》,彭磊、丁耘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7页。⑤转引自杨守森:《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精神》,《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⑥莫言:《莫言演讲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3页。⑦⑧⑨毛信德、蒋跃:《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7、383、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