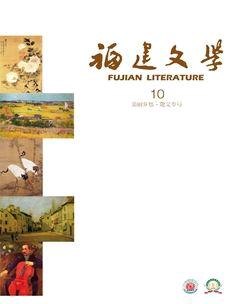年轮
张强
1
更多的时候,我游弋在麦田碧绿的海洋里,那阵吹斜了一只花斑鹊的风,掀起一股不算狂躁的波浪,我随波浪起伏,瞬间被推出去很远。
浪头尽处,浮出一只金黄的狐狸,它回头看我一眼,转瞬就消失在坟堆里了。我知道那是它的家,它和我的先人住在一起,是先人的邻居。
那些五彩的蝴蝶像浪花迸溅的粉末,它们斑斑点点漂浮着,像斑斓的梦境笼罩着麦田,在这个梦里,我究竟是什么呢?我会偶尔这么想。
我遇到的小蛇柔软地躺在田埂上,友好、和善;我遇到的麻雀并不聒噪,沉默、内敛;我遇到的鹌鹑还穿着去年的旧衣裳,我很诧异,已经是春天了,它怎么不脱下那件旧外套,阳光下暖暖地晒晒身子。
我就这样漫无边际地走,耳边风声飒飒,麦苗的体香盛大而磅礴,野花的清香细小而婉约。我喜欢这样漂浮在海洋里,孤独而渺小;我喜欢让一阵阵的波浪拍打我,缠绕我,亲昵我;我喜欢麦苗轻柔的唇,它们在我耳边布下窃窃私语。
有时候我会在田埂坐下来,彻底沉潜进麦地深处,我似乎碰触到大地的心跳和脉搏,我听到它的一阵心跳里埋藏着溪水的荡漾,裹挟着鸡鸣犬吠牛哞、铁桶的声音、劈柴的声音、打磨农具的声音、花儿凋谢的声音、啄木鸟梆梆梆啄着树木老关节的声音……
我知道那都是村庄发出的声音,此时村庄就在我的后面,离我只有三里地远。
我知道我是村庄的孩子,但我的梦在麦田,我希望永远漂浮在麦田里,像个水手,一个十岁的水手。
2
我从来都不相信灵魂。尽管大人们常说,大年夜不要往黑地方走,免得撞上回家过年的先人,那是大不敬;尽管有人说喜旺的娘死后第三天,有人在她家菜园看到过她忙碌的影子。
但我相信人死后会变成一只鸟。
腊月天寒,夕阳早早地收敛了光芒,昏黄的天幕下,乌鸦贴着村庄的头顶盘旋。在乌鸦还没归巢之前,哪棵树上落的乌鸦最多,这家往往就会倒霉,所以凛冽的风声里,常常能听到“啾啾”“啾啾”赶乌鸦的声音。
麻子大爷从来不相信这些,所以他家的老槐树上,总是落满了乌鸦,黑压压一片,总共三十八只,嘎嘎嘎唱着黑色的挽歌。
有人说麻子大爷的大限到了,乌鸦来给他搭桥,接他到另一个世界去。
麻子大爷的大限真的到了,他死之后,我发现他家树上的乌鸦变成了三十九只,所以我确信,麻子大爷变成了一只乌鸦,就是常常从树上俯冲下来,落在他家锅台的那只。
我还确信,罗锅大娘死后变成了一只猫头鹰,拴柱娘变成了一只斑鸠,高个子的狗胜变成了一只长腿的苍鹭,落水而死的小琴变成了一只花喜鹊,牛二家不满月就夭折的孩子变成了一只灰山雀……
村庄的人是不忍离开村庄的,不忍离开村庄的人只有死后变成一只鸟,才能继续守护着村庄,守护着心中不灭的灯盏。
我死后会变成一只什么鸟呢?
这个问题在我十一岁的脑海里荡来漾去,常常搅扰得我无法安眠。
3
我不知道村庄上空为什么要有这样浓重的阴霾,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或许是南来的风堆积起了十二吨雪花,正等着天空支起筛子,筛下时光结晶的碎屑。
这时候的村庄静得出奇,鸡不叫,狗不咬,雀鸟也不焦躁,或许它们都有了预感,一场大雪就要来了,它们都在竭力保持镇定,不至于村庄被铺天盖地的白淹没的时候,发出慌乱的尖叫。
我也在竭力保持镇定。
从木格子窗棂望出去,那只喜鹊还蹲在那个树枝上,我说不清它蹲在那里多长时间了,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把它看成这棵树上结的一枚果子,被寒风一遍遍抚摸,渐渐抚摸成了黑灰色。
我不能像那只喜鹊一样,对眼前的一切熟视无睹,我胸中的压抑,需要一种宣泄和释放。
我熟悉村庄的每条小道,就像我前面的那只羊,即使没有放羊的人牵着,也能独自找到家门。我从村庄的东面走到西边,我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走,或许是因为窗外的风景太单调了,那只喜鹊始终一动不动,或许是我真的希望能在村庄里碰到谁。
走到村庄尽头的时候我又原路返回,我还是没有碰到她,虽然我有些失落,但转念一想,真要碰到她的话我会多么窘迫,脸红得说不出话,这会多么尴尬。就像那次,她微笑着叫出我的名字,我的心扑通一跳,撒腿跑出了很远很远。
天依旧昏黄着,我想象着雪落的情景:雪花纷纷扬扬,像灰白的翎羽弥漫村庄上空,我撑着一把伞与她擦肩而过,我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互相回头看了两眼,一朵雪在她头发上,倏然开出了这个冬天少有的灿烂。
十二岁那年,我只记住了一场大雪的前端,其他关于村庄的记忆,都淹没在那场大雪中。
4
村庄里老木匠年纪最大,知道的故事也最多,我称老木匠是神仙。
老木匠说,乌鸦才是村庄的神仙。
在村庄,乌鸦站得最高,站得最高的乌鸦看得最远。
它看到每个十五的晚上,月亮不辞辛劳从村口的井里汲水,把村庄苍老的身体洇湿;它看到炊烟的尾巴有时比东南风短,而西北风,常常大把大把往村庄的伤口上撒盐。
乌鸦的记性也好,乌鸦记得村庄里每座老屋的年岁,记得棺木里先人的姓字,哪具棺木是柏木或橡木,哪具棺木埋在了哪座向阳的山冈。它记得村庄里曾经有位落魄的秀才,多看了两眼地主家的二小姐,却耽误了一世功名。它记得哪一年的雪大,压塌了几间茅屋;哪一年的霜早,打蔫了几亩地的虫声。
在村庄,乌鸦就是一部史书,它活在时间里,把往事一一洞穿。
在村庄,谁能把往事看穿,谁能把世事看透,谁就是村庄的神仙。
我佩服老木匠的逻辑。我的确看到过两只乌鸦在村北的荒草丛中,对着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发表着各自的见解,它们熟悉历史,读得懂村庄的年轮。
我还见过两只乌鸦蹲在一座新坟上,表情从容而超脱,它们敬畏死亡,却不惧怕死亡,它们把生命参透,把死亡看做活着的另一种延续。
十三岁的时候,每当我在村北的小树林里发现了雪地上冻僵的乌鸦,我会挖个坑把它埋了,我知道它是村庄的神仙。
人应该敬畏神仙,像敬畏自己的村庄一样敬畏村庄的神仙。
敬畏神仙就是敬畏村庄,就是敬畏自己的生命。
5
我不能理解一只鸟为什么会抛弃五谷,抛弃村庄。
那年的雪特别大,大到我的记忆都被白挤占了,大到村庄的人不敢再信奉“瑞雪兆丰年”的俗语。
屋子被坚硬的雪光映得通明,祖母的火盆里,几根未燃尽的稻草吐着一缕缕轻烟的舌头。从祖母紧皱的眉头中,我读到了她全部的伤感,来自这场雪的伤感。
屋外砰的一声钝响,我抬头,又仿佛看到一只乌鸦从枝头跌落,划出了生命中最后一条优美的弧线。第八只了,我告诉祖母,祖母沉默着,没有再重复那句话:停上一宿就好了。
我知道祖母说的是雪,雪和乌鸦的命有关,乌鸦的命和害虫有关,和粮食有关。
村庄里我的先人就曾经说过,一定要把乌鸦当作神仙供着。
这么多年了,人们一直把乌鸦当做神仙供着,人们知道乌鸦能预知生死,保护收成,是一种神鸟。
埋葬那些乌鸦的时候,人们像在进行一种庄严的仪式,所有人的脸上都布满了一层阴云,总共一百六十二只,村庄所有的乌鸦基本都死了,人们叹息着,在它们僵硬的身体上撒下金灿灿的谷粒。
这一刻,人们埋葬的好像不是乌鸦,而是村庄的巫师。
所有的乌鸦都是冻死的,村庄里的乌鸦不会被饿死。
所以当雪终于停下来,西北风停下来,我不住地向那些空巢张望,我希望奇迹会出现,两只乌鸦拍拍翅膀飞出来,啄食撒在地上的苞米粒,或者用它们有力的飞翔,再一次把村庄上空悄然抹黑……
然而我终于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
乌鸦的死,成了我十四岁记忆中一块抹不掉的伤疤。
6
或许和那些乌鸦一样,人在抛弃村庄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无奈。
她的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我不敢去看,我怕我会哭出声来,我怕她的眼睛还睁着,却再也看不到我看她的眼神。
我曾经那么想遇到她,以至于绕道大半个村庄去上学;我曾经跟在那条大辫子后面走出老远,大半天也没打到半箩筐猪草;我曾经对着月光许下心愿……
老猎人说,那年他在村口遇到过一只狐狸,那只狐狸对着割草的她笑过,她被那只狐狸摄走了魄,现在她也变成了一只狐狸。
我不相信老猎人说的话,但我却非常想遇到一只狐狸,想让一只狐狸对着我笑。
于是我会走进麦田的最深处,那是村庄的坟场。我看到那些坟,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感到那么亲切,好像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故人,我不相信灵魂,但却希望坟墓里的人能走出来,和我面对面坐着,听我讲村庄的故事。
当然我会向他们打听她的下落,问那只和他们住在一起的狐狸是不是她幻化出来的。
我多想那只狐狸会对着我笑,然后嗖的一声摄走我的魄,然后广袤的麦地里就有了一前一后两只狐狸。两只狐狸被春风和麦浪紧紧包围着,被鲜花和嫩草紧紧包围着,被雨水亲切地拥抱着,被日月朗照,被星光洗浴。
麦地的尽头是村庄,它们可以到村口溜达溜达,向土著的狗打个招呼,向采蜜归来的蜜蜂问个好,它们甚至可以不躲避谁,大大方方走在村庄的街道上。
十五岁那年,当我走进麦田里的时候,我总感觉我不是我,我是一只狐狸。
7
村庄的老井干涸了。老木匠说,村庄没有了脉。
多么干旱的年份老井都没有干涸过,而现在,老井真的干涸了。井台上湿滑的苔藓也枯死了,老井像一只流干泪的眼,空洞\茫然。
有巫师从村庄里经过,他的马拒绝喝水,巫师也说,村庄没有了脉。
我不理解他们话的真正内涵,只幼稚地认为村庄将要遭遇大旱。
而事实是雨量充沛,蝉鸣和蛙鼓茂盛,麦子葱茏,苞米茁壮,稻谷飘香,高粱沉实,地瓜憨厚质朴,土豆饱满而圆润……
我依旧徘徊在麦田里,看清风流云,看远山雾霭,看两只雀儿从我视线中飞进又飞出。
但我没有注意到,村庄中又有一处宅子荒废了。
我是听老木匠说的,留根家的宅子在一场大雨中倒塌了。留根一家在城里扎下了根,村庄最终没能留住他的根。
六年前留根去城里捡破烂,捡着捡着他在村庄的地就撂荒了,捡着捡着全家就从村庄拔根而起了。我似乎想到的确有那么一块地荒着,枯草被秋风撕扯,呼啦飞起一群往南迁徙的野鸟。
我开始理解老木匠和巫师说的“脉”。
我问老木匠,村庄没有了脉,那村庄还能活多久?
老木匠沉默着,没有回答我的话。
其实他不用回答我的话。背弃村庄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有的丢下老小,有的连根拔起,消失在麦田的尽头。
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弃村庄的,尽管有人说起城市的繁华,尽管村庄的宅子又空下了几所,因为这里有我的麦田、乌鸦和狐狸,我要守着它们,像那只乌鸦,守着它风雨中飘摇的巢——
这是我十六岁时立下的志向。
8
老木匠死了,九十三岁的老木匠死了,村庄的神仙死了。
老木匠死的时候乌鸦没有落在他家的树上,老木匠死后也没有乌鸦蹲在他的坟上。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乌鸦了,它们的巢还挂在树上,在秋风中独自破败着,像秋天的一顶破毡帽,又像是一个大大的句号,标在村庄的史册里,那么醒目。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那只狐狸了,我想变成狐狸的想法也落空了,麦田里日夜响着挖掘机、打桩机的轰鸣,那只狐狸或许早已远走他乡,或许像老木匠一样老死在家中。
我不敢再去麦田里游荡,那里已生长起钢筋混凝土的庄稼,坚硬而冷漠。现在我更愿意在村庄里游荡,看看这家坍塌的老屋,看看那家紧闭的大门。我多想扶起那些折断的房梁,好让它们重新扛起落日;我多想焗好那些破碎的陶罐,好让它们重新荡漾起日子的水纹。我看到的每个面孔,都被时光重重地咬过,他们聚在一起谈生活,一脸满足的样子,但我却窥见他们心底难以言说的疼痛。
十七岁的年龄不适合怀旧,我这样劝告自己。
当我就要离开村庄的时候,我抚摸着村北荒草中的残碑,像抚摸着村庄的年轮,残碑上字迹模糊,我的双眼也渐渐模糊。
当我再次归来的时候,或许残碑也会不在了,或许我想找一样东西怀旧都不可能了。
村庄终于死了,在我离开的第二年。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将拿什么完成自我的救赎?
责任编辑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