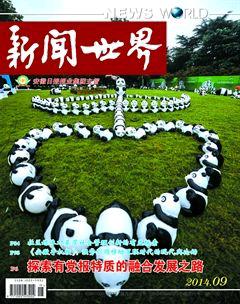“水”、“火”、“井”:《妻妾成群》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三种意象
王祎颜
【摘 要】尼采在《肉体是一个大的理性》中说到:“肉体是一个大的理性,是具有一个意义的多元,一个战争和一个和平,一群家畜和一个牧人。”《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本文将从肉体理性的多面即——多元的意义,战争与和平,家畜和牧人方面并从封建势力的代表陈佐千即“火”,弱势女性的代表颂莲即“水”,以及火为了防备水而筑井即陈府残忍的家规,探析小说与电影中命运相同而性格不同的两个颂莲形象。
【关键词】《妻妾成群》 《大红灯笼高高挂》 颂莲
尼采在《肉体是一个大的理性》中说到:“肉体是一个大的理性,是具有一个意义的多元,一个战争和一个和平,一群家畜和一个牧人。”《妻妾成群》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分别讲述了女大学生颂莲因家道中落无奈嫁入豪门陈府,在受尽了封建礼教和尔虞我诈的折磨之后精神崩溃,丧失了肉体的理性。虽然最后颂莲“身”未死,但从她踏进陈府起其心灵就在逼近着死亡。相比于小说揭示封建源自规矩和人心,电影更侧重于人往往是一步步沉沦最终自取灭亡这一主题。颂莲虽然在主观上是一个念过大学的新女性,但她更是一个客观命运争宠战中的失败者和在欲望中沉沦的堕落者。
一、肉体即“水”的多元意义
颂莲的肉体到了陈府后被赋予了多元的意义:在第一重意义上她是陈老爷的小妾,其次她也是陈府的主人之一。小说中的颂莲虽然是一个19岁的大学生,却具有超越其阅历与年龄的聪敏。父死家亡后,颂莲选择去给有钱人做妾。从此,她要走进一场阴暗的婚姻。但她要凭借这场婚姻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颂莲是一个如水般敏感的少女,同时她也颇有心机。无论是与陈老爷还是飞浦的初见,颂莲都用与众不同的言行令这对父子留下深刻印象。面对新婚之夜抢走陈老爷的三太太梅珊,颂莲在第二天“还是迎上去问梅珊的病情”。在陈老爷的寿宴前颂莲为自己的不懂事后悔,因为惹恼陈老爷“是她唯一不想干的事情”。于是她当众向陈老爷献吻。颂莲对陈老爷的讨好还表现在初见毓如后她“就挽住陈佐千的手臂”。而在电影中颂莲从未主动与陈老爷有身体上的接触。所以,小说中的颂莲是一个颇有心机,明确深闺大院生存法则的女子。
电影中表现颂莲多通过动作过程,而少表现心理过程的内心独白,因此对比小说,电影呈现的颂莲不是敏感多思的知识女性,而是泼辣十足的姨太太。①电影中的颂莲爱恨分明、自尊执拗。颂莲自以为聪明,实则不通世故。她只是被表象迷惑接受了卓云,却不知卓云是一个阴毒妇人。虽然颂莲认了做妾的命,也知道要不断提升地位,但她太过自尊不愿去献媚讨好,她只是在与姨太太们斗争着。后来,颂莲假孕争宠,直至打破家规让管家送饭到房间,都是为了更有力地占据在陈府的地位。拉康认为,个体人格结构有三个层面:第一是“想象界”,第二是“象征界”,第三是“实在界”。人们的行动和生活往往会受制于这样三个层面。
第一类是颂莲、梅珊,她们代表的是想象界错觉。颂莲和梅珊本来一个是穷学生,一个是戏子,都是陈府的妾,由于其鲜明强烈的个性,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感觉,但实则她们对命运无能为力,代表强而弱。第二类是雁儿,做着太太梦的丫环,她代表实在界的无能,弱而弱。第三类是陈老爷,代表象征界的眼力。他用行动赏罚分明,代表强而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三角意义的模式展现。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展现出了颂莲和雁儿的一种联系——雁儿就是被卖到陈府的颂莲,颂莲也就是雁儿想成为的太太。小说中颂莲偶然发现雁儿用草纸恶咒她,她便要挟雁儿吃草纸,与此同时颂莲就成为了陈府规矩有力的维护者。颂莲是封建制度的承接者、反叛者,同时也是牺牲品。但倘若颂莲以一个姐姐的身份去关怀雁儿,而不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那小说中雁儿也不会“没事就往梅珊屋里跑”,电影中雁儿也不至于成了卓云的眼线,将颂莲假孕的消息走漏。颂莲和雁儿的相似处在于,她们都想讨好老爷,而真心喜欢的又是少爷。另外,颂莲初到陈府时对梅珊非常好奇,她站在梅珊窗前“忽然忍不住心里偷窥的欲望。”这与雁儿偷窥陈老爷与颂莲一样。这两处偷窥的描写展现出颂莲和雁儿相同的偷窥私欲,这种欲望的根源就是自卑。
在小说和电影中颂莲都亲眼目睹了两次偷情,一次是陈老爷与雁儿——陈佐千“顺势在雁儿的乳房上摸了一把”。陈佐千与雁儿的暧昧一方面显示出雁儿甘心无名无分地讨好陈老爷,另一方面这也引发了颂莲后期的思考——“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另一次是梅珊与高医生——颂莲发现后“心情很复杂。”这两次偷情是颂莲肉体理性发生变化的一条明线,而暗线则是颂莲和飞浦之间的情愫。小说中颂莲与飞浦的交流较多,而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道具是萧。学习吹箫时,颂莲说她恐怕只有感伤这种心境。这其实就是对颂莲结局的一种暗示。因为颂莲本身就如同一只清瘦的萧,优美而感伤。但最后她被消磨得连感伤都不复存在。而电影将萧换成了笛子。萧与笛子最大的区别是,笛子需要笛膜才可以吹奏,萧则不需要膜。所以,电影将箫变成笛子一方面暗喻颂莲与飞浦之间的隔膜——飞浦是同性之恋;另一方面电影通过心到其境的笛声将颂莲和飞浦的关系塑造得更有意境。
二、“水”、“火”、“井”的关系:家畜和牧人
电影中陈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每每清晨管家就说:“老爷走了,灭灯。”这就反映出陈老爷是火,没有他,就没有火。而颂莲则是水,苏童在小说中写到:颂莲“每逢阴雨就会想念床笫之事”;颂莲“心里是一片秋水涟漪”;颂莲独饮庆生时飞浦的到来让她的“心里很潮湿”;寿宴上颂莲头疼起来“想喝水”,于是“那口井向她隐晦地呼唤着”等描述都展现出颂莲与水的关联。颂莲想喝的水就代表一种渴望自由、自在的欲望,而死人井里滿满都是被淹没的欲望。面对“明火”,颂莲的态度是强硬且厌恶的:“谁让你们烧树叶的?好好的树叶烧得那么难闻。”明火导致树叶焚烧从而产生刺鼻的气味,而这就是欲望被禁锢的灵魂的灰烬。对待“暗火”陈老爷,颂莲的态度是不想惹恼。而水火本就不相容,所以苏童在本质上就将颂莲与陈老爷置于了相对立的位置,火为了免遭水的侵害就筑造了井。这就是陈老爷与颂莲还有死人井的关系。牧人放牧后会把家畜赶回圏内,而陈家大宅就是陈老爷放牧的牧场,死人井就是不服从管理的姨太太的归宿。井比喻法度、条理,是约束人的东西。从井的字形来看, 它像古时犯人戴的枷锁。因此小说中设定“井”的意象, 本身就是苏童故意给陈府上空制造的一层浓重阴霾, 给故事中人物的身体和灵魂戴上的枷锁。②
颂莲一入陈府就与水井结缘,后来颂莲又在后花园紫藤架下发现一口井。紫藤让颂莲回想起校园时光,但也为下文这口井真正的用途埋下了伏笔——它是一座死亡的坟墓,而唯一的紫藤是为哀悼这些生命而存在。随后,卓云的话让颂莲吃了一惊:“你去死人井了? 那井里死过三个人。”这是第一次有人在颂莲面前揭示了井和死人的隐秘联系。颂莲在听到卓云的简介后没有继续追问,后来她在陈老爷处得知:“死了两个投井的”。井,不仅是井,它是加在陈府每个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是一口吞噬越轨者生命的坟墓。欲望越旺盛的人沉入井底的速度也越快。“我走到那口井边,一眼就看见两个女人浮在井底里,一个像我,另一个还是像我。”颂莲的自白昭示出她今后的命运——她在紫藤架下枯坐,对着井中说“我不跳井”。颂莲的确没有跳井,但是井中浮着她行尸走肉般的倒影。“我不跳井”是对颂莲生命由浮躁到萎谢的总结。颂莲一路的争宠是一种反抗,但反抗的最终结果只能凝结在“我不跳井”这四个字上。电影中将埋藏在地下的死人井变成了高筑在房顶的死人屋,营造出遗世独立之感,更彰显出陈府的权威,但却失去了深井所带来的阴森和厚重。
陈老爷和他四房太太的关系就是牧人与家畜的关系,陈老爷采取的放牧方式不是挥舞皮鞭而是通过点灯和捶脚这样竞赛制的享受来实现奴役。电影以点灯和捶脚作为争宠战的原动力,增强了戏剧性。卓云某次跟颂莲说:“你要是几天锤不上脚,连下人的眼色可都不一样。”象征着权位的点灯、捶脚不仅牵动着各位太太的心,就连丫环雁儿都在自己房间点了灯,脱了鞋摆出一副有人给她捶脚的姿态。颂莲自然也尝到了甜头,因为点灯、捶脚不仅骄傲、舒适,而且点灯就能点菜。可颂莲“不爱吃肉”,她点的菜是菠菜豆腐,这是电影中一个绝妙的隐喻:颂莲这样的素食主义者该如何在陈府这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存活。颂莲从“承受”点灯、捶脚到意识到别人的争宠会使她丧失此等福利时,最初的“承受”就转化成了“享受”。电影不仅通过颂莲在没有人给她捶脚时闭目回味那种舒坦,还通过她让丫环捏脚来代替捶脚展示出她的心灵在争宠飨宴中的复活。起初的颂莲面对点灯、捶脚这些规矩好奇却并不适应,但后来肉体上的舒适惬意和精神上的畸形满足,让一个死了心的女学生变形成了一个争风吃醋的四太太。颂莲经历了点灯、灭灯、长明灯和封灯,灯的状态也就是她的生存轨迹。在陈府这样一个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当中,为了能有一席之地,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欲望,颂莲的性格逐渐扭曲。点灯、捶脚为颂莲在陈府的生存做出了指引,但也将颂莲引上了一条不归路。所以,相较而言小说中的颂莲是通过本身性情中蕴含着的心机在陈府步步惊心地生存,而电影则是通过诸如点灯、捶脚这种形式上的享受和争宠吸引着颂莲的步步沉沦。
三、“水火”的战争与和平
因假孕颂莲被封灯,她开始思索人的价值:“人跟鬼就差一口气。人就是鬼,鬼就是人。”叔本華说:“人心的满足愈感欠缺,愈希望别人认为他是幸福的人。一个人的愚蠢到了这种地步,要以他人的所思所想,当做努力的主要目的,这种完全的空虚,从常言的虚荣一词,原意即为空虚表现出来。烦恼者有时很清楚地看到命运的捉弄,却只有接受它的慢慢宰割。”颂莲就是一个因虚荣而空虚的人,她为了保卫自身必须通过强制、奉承等手段抵御其他人。颂莲需要陈老爷的宠爱、下人们的敬爱来满足她作为四太太的虚荣,提高她在陈府的地位,所以她努力争宠。但最后只能接受命运的捉弄和宰割。颂莲在陈府的无能感和恐惧感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她必须通过争宠等手段抵御来自卓云、雁儿的明枪暗箭。所以她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感。从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分析颂莲与陈府诸人的关系可看出:
被压迫者颂莲处在X的位置,她代表受过大学教育的新女性,具有一定程度自觉反抗的意识。反X的位置就是压迫者陈老爷。在陈府,各房太太之间的争宠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陈老爷是唯一的指挥官,他可以决定哪位太太承宠,也可以决定越轨者的生死。“女人永远爬不到男人的头上来。”这是小说中陈老爷对于女性以及其四房太太地位的总结。电影中陈老爷对女人表面上的呵护实则是为了自己——“女人的脚最要紧,脚舒服了就什么都调理顺了,也就更会伺候男人了。”而且陈老爷不仅要霸占女人的身体还要禁锢她们的内心。小说中陈老爷偷翻颂莲的行李箱,取走并烧毁了颂莲父亲唯一留给她的一只萧。而他的理由居然是:“我怕你分心”。
毓如、卓云既属于被压迫者,但又用封建规矩对颂莲实施规范、形成打击,所以是非X。尤其是颂莲醉酒后毓如强行给她灌醒酒药,这就体现出毓如对颂莲的压迫。而卓云的两面三刀更是体现了她对颂莲的打击。小说中的毓如摆出了一副老爷之下众人之上的姿态。在陈老爷的寿宴上因为卓云的女儿忆容和梅珊的儿子飞澜打碎了花瓶,毓如便“一人掴了一巴掌。”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想必不会对年幼的孩子大打出手。与颂莲初见时,毓如手里的佛珠断了线,这预示着随后的一切: 颂莲美好的年华正如那串佛珠,在封建礼教和自身欲望的压迫下断裂了,难以再拼凑重来。电影中的毓如是个几乎已经退出争宠队伍的老古董,形象和言行都给人老态龙钟的感觉。在毓如房间里打扫的丫环也如动作缓慢的机器一般毫无生气。电影中虽然没有陈老爷的正面镜头,但是通过毓如衰老的面容就能让人想象出陈老爷的年迈。毓如手握佛珠,在颂莲走后念叨着“罪过”。这一细节展现出毓如已经不再想与各房太太发生过多联系,所以她将自己对于颂莲入府的态度放在了颂莲走后才表露出来。“到了府上慢慢就惯了”这是毓如个人态度的唯一表达。借劝导颂莲毓如表达出在陈府多年的感受——只有慢慢习惯陈府的一切才能维持住表面的平静。
颂莲在陈府唯一的知己就是飞浦,他处在非反X的位置上。但飞浦却无法帮助颂莲获得真正的自由,只能给予其短暂的精神寄托。与颂莲同命相怜的梅珊如果是X,那高医生则处在非反X的位置。梅珊曾在紫藤架下说道:“人跟鬼就差一口气,人就是鬼,鬼就是人。”随后颂莲问梅珊是否知道谁死在了井里,梅珊说:“一个是你,一个是我。”最后一语成谶——梅珊与高医生偷情被卓云抓住,梅珊被投了井。在小说中,梅姗的死和颂莲没有关系,但在电影中,是颂莲在酒醉后说出了梅珊与高医生有私情,于是颂莲就成为了梅姗之死的直接凶手。这也造成了颂莲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的双重悲剧身份。梅珊曾对颂莲说:“虽说你是个读书的,我是个唱戏的,但我们这种人都是一回事。”读书和唱戏乍看上去有着天壤之别,可书也好,戏也好,都是让人沉浸在一个纯粹的世界里。所以颂莲身上有着梅珊的狂傲气质,梅珊也曾经历颂莲初来乍到时的不安。但到了陈府,这两种命运的女子都转到了相同的生存轨道上。但梅珊是一只被割断了翅膀囚禁在金笼里的野鹰,她曾经在戏台上肆无忌惮地演绎悲欢离合。嫁入陈府后,梅珊深知羁绊她的规矩和旁人的居心,但她无法像毓如一样磨灭欲望和希望,也无法像卓云一样温和顺从,因为她的性情和感情就是直截了当,以自我为中心。梅珊用狂傲不羁的言行去撞击陈府的规矩,最终她败了。
结语
拜伦在《赠一位早年的朋友》一诗中写道:“进入成年,就完全变样:人本身变成了一样工具;私利左右着忧虑和希望,爱什么,恨什么,都得按规矩。”
这首诗可以看做是写给早年学生时期颂莲的一首悼词。刚刚成年的颂莲进入了陈府,她的青春和她接下来的人生就完全变了样,她按着规矩去“爱”她的丈夫,她按着规矩去惩治害她的丫环。颂莲的肉体变成了陈老爷的一个玩物,一个生育工具。与此同时颂莲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增强自己的地位不断地在争宠斗狠的战争中拼杀,在满是祖上规矩的环境中压抑限制着自己的本心。她的悲剧是旧时代妇女命运的缩影。《妻妾成群》塑造的颂莲是生活在封建背景下经过拼争,但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牺牲品。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着重展现了颂莲在欲望中的沉沦。但小说和电影都对封建社会的规矩和女性的卑微地位进行了深刻的挖掘,无数个颂莲成为了妻妾成群这一畸形民俗的牺牲品,引人深思。但是,在那样一种浸润着角色困惑的社会意识和拘束性灵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悲剧依然延续。小说中第二年春天时五太太文竹被娶进了陈府,小说将文竹入府设定在第二年春天是为了与梅珊在冬天的死去相呼应。而电影中只有夏秋冬这几个季节并没有春天则意指在陈府没有希望,所以无所谓复苏重生的春天。文竹的入府是一种典型的无动于衷的自然主义形态的表现,使作品对封建民族文化的批判由此得到了进一步深化。③□
参考文献
①李妙晴,《改编电影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J].《电影文学》,2007(15)
②郭颖杰,《〈妻妾成群〉:欲望和生命的悲情演绎》[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7)
③柯晓兰,《电影改编:如何在镣铐中舞蹈——以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妻妾成群的改编为例》[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1)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