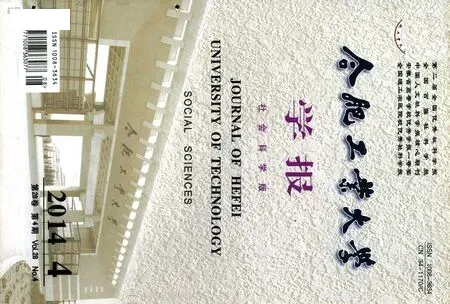合唱的艺术巨献——评译作生产阶段的创造性叛逆
汪 健, 田德蓓
(1.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2.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最早由法国学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在其专著《文学社会学》中,他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由此可见,埃斯卡皮已经意识到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同时也探索了创造性叛逆的原因。不过,他所提到的“参照体系”显然还是将研究的视角拘泥于语言层面上,这未免简单化了创造性叛逆的原因。
国内研究创造性叛逆的先驱应首推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20世纪90年代他在著作《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有过较为系统地阐释:“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说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2]137在该书中,谢天振教授详细研究了创造性叛逆,将创造性叛逆划分为三个版块,即媒介者(译者)创造性叛逆、读者创造性叛逆以及接受环境创造性叛逆,并逐个分析各版块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虽然这便于当时初次接触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中国学者学习与接受,但同时也为今后学术界误解误读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埋下隐患——一提到创造性叛逆就模式化地强行将其分成这三个版块,并简单地认为创造性叛逆就是译者与原作、读者与译作、接受环境与译作之间双边对话碰撞的结果,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在我们看来,只有打破这种平行、孤立的版块划分,才能让我们的研究视角同时关注到其他参与创造性叛逆的因素,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阐释创造性叛逆。为此,笔者将创造性叛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是译作生产阶段的创造性叛逆,不妨称其为一级创造性叛逆;第二阶段则是译作产生之后的创造性叛逆,称之为二级创造性叛逆。二级创造性叛逆显然要以译作的完成为前提,也就是说,二级创造性叛逆是以一级创造性叛逆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级创造性叛逆要比二级创造性叛逆更重要,更有价值。本文将着重论述一级创造性叛逆。从译作生产阶段探究创造性叛逆,我们的研究视角不会仅仅禁锢在译者、译作两个方面,我们还能观察到其他因素在创造性叛逆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一个多维影响系统,它们的合力最后呈现出一级创造性叛逆的最终形态。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四个部分:译者的个体特性、赞助人(强制性干预主体)、隐含读者(参与性干预主体)以及干预客体(语言、文化、时代背景)。
二、译者的个体特性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谢天振教授率先在《外国语》期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媒介者(译者)创造性叛逆,将其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大类型,并具体细化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和“转译与改编”。他认为译者“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独特的追求目标”以及“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了解程度导致了创造性叛逆[3]。可以说,谢天振教授开创国内学术界先河,首次较为详细系统地论述了译者在创造性叛逆产生中的作用。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虽然谢教授论述“媒介者创造性叛逆”时涉及了接受国读者的趣味、文化,但毕竟是放在媒介者创造性叛逆的框架内,容易给研究者产生一个错觉:创造性叛逆的产生只是译者一人的独角戏。
香港翻译家、学者金圣华在她的著作中这样表述过:“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迎风飘荡。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4]金圣华教授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创造性叛逆,但是已经触及译者的个性特征在创造性叛逆中所发挥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会“毫无主见”,不会“放弃立场”,译者的“学养、经验”必然在翻译取舍中作出选择。诚如许钧所言,“翻译主体”(译者)具有“主观能动性”[5]9,译者自身的特性必然融入到创造性叛逆之中。
至于译者个体特性在一级创造性叛逆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理论。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理解者总是带有自己的历史性;历史性是人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无法消除或抹杀的;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任何人在进入阐释的过程中都不是如同一块白板,必然会将自己的历史性带入理解之中[6]。将该理论引入到翻译领域,我们会发现:在与原作的对话过程中,译者的个体特性,如译者的个人经历、修养、知识结构、意识形态、道德观、审美情趣等必然参与其中,不断影响着创造性叛逆。
譬如,清末民初周桂笙翻译法国小说《毒蛇圈》时,由于译者本人十分推崇中国的章回式小说,便强行将原作分成几十回,又为每一回拟了一个章回体标题,如“几文钱夫妻成陌路,一杯酒朋友托交情”[2]170等。更不可思议的是,译者为了迎合自己所认可的道德评价标准还在其译作中凭空增添了一大段描写女主人公妙儿思念其父的话语。
再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举世公认的译界精品,至今影响颇大。其中有段译文:“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7]当我们阅读至此,脑海中立刻会联想到以古朴典雅、气势恢宏为特征的桐城派古文风。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译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事实上,严复不仅非常推崇桐城派文风,而且与不少桐城派知名人士来往密切,当时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就是他的忘年之交。
有必要指出,本文引用译者个体特性这个概念,目的在于强调:虽然译者的个体特性在一级创造性叛逆中具有很大作用,发挥着最积极的因素,但是译者的个体特性参与创造性叛逆并不等同于译者创造性叛逆,更不等同于创造性叛逆全部,它只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创造性叛逆不是某个因素的独角戏,而是众多因素集体合唱的艺术巨献。
三、赞助人——强制性干预主体
在译作的生产过程中,除了译者个体特征参与到创造性叛逆之外,赞助人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赞助人一般通过对译者施加压迫性影响,参与到一级创造性叛逆中,因此我们可以将赞助人视为强制性干预主体。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在译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谢天振教授曾指出:“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8]在《多元系统论》中,埃文-佐哈尔指出“决定多元系统内的过程,而且决定形式库(repertoire)层次上的程序,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其实同样有效于该多元系统的实际产品(包括文字与非文字产品)的程序,例如选择、操纵、扩展、取消等等”[9],后来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将这种“制约”概括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2]239。由此可见,多元系统论的提出者与发展者已经注意到赞助人在译介过程中的作用,只不过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赞助人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文化要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2]240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创造性叛逆上。
谢天振教授在《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对赞助人作出如下界定:“‘赞助人’并不指某一个给予具体‘赞助’的个人,而是包括政府或政党的有关行政部门或权力(如审查)机构,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社等。”[10]250同时他对赞助人的作用进行了陈述:“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如宣传部、文化部或教育部等,鼓励或倡导翻译出版某部或某些外国作品,那么这些作品自然会得到大力的译介。”[10]250谢教授充分肯定了赞助人的作用,不过他关注的重点在于“赢得市场”的角度,而非赞助人在创造性叛逆中的作用。
实际上,一部译作的诞生,往往离不开赞助人的认可与支持,赞助人在译作的生产过程中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源。郑晔博士曾将赞助人对译者的制约归纳为三个要素:“意识形态、经济、地位。”[11]54赞助人正是通过对译者的有效制约,参与到译作的创造性叛逆之中。同是翻译《红楼梦》中的“贾夫人仙逝扬州城”,杨宪益译文为“Lady Jia Dies in the city of Yangzhou”,而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Hawkes)则将其译为“A daughter of the Jias ends her days in Yangchow city”。不难看出,对原文“仙逝”的翻译,两位译者存在较大差异。霍克斯的译文为“ends her days”,基本保留了原文委婉的意蕴;而杨宪益则直接用“dies”翻译,致使原文对逝者恭敬之意在译文中很难得到体现。按常理,作为谙熟汉英语言文化的学者,杨宪益先生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若想一探其中的缘由,就得挖掘翻译背后的赞助人的影响作用。1953年杨宪益被调入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根据上级的指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翻译《红楼梦》,并最终于1974年完成。众所周知,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内政治形势并不稳定,国家特别重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国家赞助人(如出版社)会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来肃清或区分背离其意识形态”[11]55,并通过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经济(工资、奖金),地位来制约译者的翻译行为,参与到译作的生产过程中。“在杨译的(《红楼梦》)出版说明中,也多次引用了毛泽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等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明确指出这是我们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12]可见,杨宪益没有使用委婉语翻译“仙逝”,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赞助人意识的影响。虽然小说中贾夫人并非恶人,但她毕竟同属封建权贵,属于剥削阶级,是人民斗争的对象,所以译文无需表达尊重。相比较而言,与霍克斯签约的英国出版社对《红楼梦》的译介要求不同,它的目的主要在于让英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因此对于“仙逝”的翻译也不同。
四、隐含读者——参与性干预主体
关于读者在创造性叛逆中的作用,谢天振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作《译介学》中便有论述:“当译者把完成了的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也加入到了这个再创造之中。”[2]165不难看出,谢教授主要论述的是读者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属于二级创造性叛逆。虽然在专著中也提到了“为迎合接收国读者的趣味”[2]155,但也是限制在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框架内。在此之后,有不少学者就读者对译作的创造性叛逆、读者在创造性叛逆中的作用作了不少研究。不过,笔者认为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绝大部分研究依然将读者的作用局限在二级创造性叛逆阶段探讨;二是将读者作为一个笼统概念,没有细分读者群体在创造性叛逆中的作用,造成表述不清的现象。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西方叙事学的“隐含读者”理论加以解决。“隐含读者”是指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或者说是文本预设的读者”,“‘隐含读者’强调的是作者的创作目的和体现这种目的的文本规范”[13]。
实际上,译者决定翻译一部作品时,他或她心目中也有预设读者即“隐含读者”,因此“隐含读者”同样制约着译者的翻译行为与译本规范。不过“隐含读者”往往没有赞助人那样具有强制力,而是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参与到译作生产过程的创造性叛逆中,故可以视其为参与性干预主体。这种参与性干预作用主要是通过“隐含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方面对译者施加影响来实现的。
20世纪初,蟠溪子将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Joan Haste译介到中国,即译本《迎因小传》,译者心目中的“隐含读者”为当时社会读者主体——接受封建正统思想的读者。为了避免与其“隐含读者”道德观念相悖,蟠溪子故意把原著中男女主人公两情相悦、未婚先孕等情节完全删除。五四运动前夕,胡适将美国女诗人萨拉·悌斯代的诗歌Over the Roofs译为《关不住了》,并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3期上,译诗一改以往重格律平仄的古文风,率先使用白话文翻译诗歌,而且还将原诗的标题Over the Roofs创造性地译为《关不住了》。很明显,这是胡适为了迎合他心目中预设读者的审美趣味。胡适的“隐含读者”并非社会上仍占主体地位的传统读者,而是当时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新青年,他们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僵固不化。胡适没有将原题忠实地译为《在屋顶之上》而是译为《关不住了》,具有一语双关之用,既表达了原诗本意——爱情是关不住的,又暗示落后愚昧的旧传统禁锢不住社会的进步。这与新青年所推崇的精神相契合。
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曾经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这样写道:“每译一段,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14]由此可见,译者在心中始终装有自己的预设读者。译者在针对原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隐含读者”必然会加入到译作的生产过程之中,势必会参与到创造性叛逆之中。
五、干预客体
在译作生产过程中,参与创造性叛逆的还有干预客体,主要表现为语言、文化、时代背景等。翻译需要跨越两种语言,“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15],语言差异必然会导致创造性叛逆,而且往往差异越大,创造性叛逆就越明显。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将翻译过程中可译性限度的障碍划分为:语言文字机构障碍、惯用法障碍、表达法障碍、语义表述障碍、文化障碍[16]。他认为语言差异是翻译的很大阻碍,而这种阻碍势必会影响创造性叛逆。例如,英语与汉语分属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仅语言结构上就存在很大差异,“前者的句法结构侧重形合(hypotaxis),后者的句法结构侧重意合(parataxis);前者结构缜密严谨,各个部分之间通过关联词丝丝入扣地连成整体,后者结构松散灵活,各部分的连接靠的是语义与逻辑”[17]。
英汉互译过程中语言结构转换的艰难性在诗歌翻译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往往独特的语言结构本身就是诗歌艺术瑰宝的一部分。如李清照诗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汉语所独有的重叠组合结构,即使是最优秀的翻译家也难以在译文中完整再现原文语言结构与蕴意。曾经就有多位翻译大师做过努力,包括徐渊冲、林语堂两位先生:
许渊冲的译文为:“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so drear,so lonely,without cheer.”
林语堂的译文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
细细品读,不难发现两位大家的译诗在语言结构上还是与原诗存在很大差异,无法呈现原诗所展现的结构美。再如,美国诗人卡明斯(e.e.cummings)的诗歌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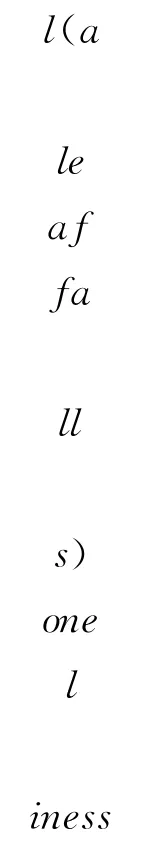
诗人依据英语独特的结构特点,巧妙地运用绘画技巧,将“a leaf falls”(一片树叶飘落了)与“loneliness”(孤独)四个词拆开,排成垂直的一列,勾勒出一片叶子孤独下落的图形,达到了内涵与图式高度融合的效果。要想将该诗完好无损地译为汉语,同样是高不可攀,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理解,创造性地进行阐发。许钧曾感言:“即使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忠实的仆人,也必须去面对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这一脱胎换骨的变易。”[5]8语言的差异(包括语言结构、词汇空缺,语义空缺等),往往迫使译者必须作出取舍,创造性叛逆也就不可避免了。
同样,翻译也要跨越文化界限,必然将原著引入一个全新的文化圈中。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的心理与知识沉淀,与各民族的历史、宗教、习俗、地域等息息相关。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两种文化激烈的碰撞、扭曲、变形是无法避免的,它会以创造性叛逆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龙,在汉语文化中,是高贵、威严、神圣的象征,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残暴邪恶的象征,是应该被消灭的对象。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要注意到这种差异,采取创造性的措施加以应对。又如,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这样描述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在中国“比干”、“西子”(西施)都是历史名人,分别是智慧与美人的象征。在向西方译介时,译者不得不面对西方读者对“比干”、“西子”毫不知晓的窘境。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文化阻隔有所减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碰撞。例如,东方人现在能完全理解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人也能明白中国的春节、功夫等。
任何一个翻译行为都是处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而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势必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所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崇尚求变创新,译者纷纷抛弃古文风,而采用白话文翻译外国作品。上世纪中期,阶级性、革命性成为时代的重要特点,这也影响到了译者的翻译行为,如法文翻译家罗玉君先生翻译的《红与黑》,对比法文原文,不难发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显然受到了当时革命意识、阶级意识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郝运先生翻译的《红与黑》译本则更加体现出新时期的风格。
六、结束语
从译作生产阶段研究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我们不会陷入只注重译者作用的研究窠臼,不仅能看到译者个体特性的作用,也能注视到赞助人、隐含读者以及干预客体的作用,从而能做到比较全面客观地审视各因素在创造性叛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强调,虽然创造性叛逆无法避免,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强调创造性叛逆而肆意不尊重原作,“译者应是一个修正者(revisionist),而不是一个背叛者(traitor),因为前者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在坚持原文基础之上的一种修正,而后者却是在故意脱离原文,借以创建新的文本”[18]6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时刻提醒自己所担负的神圣使命,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 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30-37.
[4]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15.
[5]许 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60.
[7]赫胥黎.天演论[M].严 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
[8]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249.
[9]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20-25.
[10]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1]郑 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12]周文娟.解读译者的创造性叛逆[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27.
[13]申 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7.
[14]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全集[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365.
[15]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96.
[16]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117-135.
[17]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38.
[18]王 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