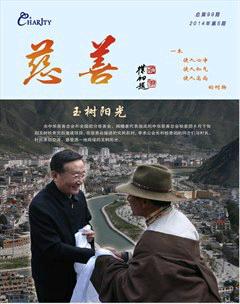大姨娘
张庆安
我的家乡坐落在具有五大淡水湖之称的巢湖之滨北麓试刀山下。每当南下出差或归来,车辆途经试刀山隧道的时候,偶尔透过路旁翠绿婆娑的枝叶缝隙,可以看到镶嵌在山墙上“大王举”村名的标牌,不由得会勾起往事,追溯儿时的记忆。我的亲姑妈就住在与大王举村并排的小王举村。
“大姨娘”通常是晚辈对长辈的尊称。从我懂事起,只有我叫这位“大姨娘”的人为姑妈。其他不分年长年幼、辈分大小的人都叫她“大姨娘”。她虽然去世多年,仍是我一直崇敬并深深怀念着的人。
“大姨娘”的家只有三间茅草房。门前是南来北往上街赶集的通衢要道,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过往行人络绎不绝。无论晴天丽日,还是风雨雪天她家的门都是敞开的。乡邻走累了,会到她家歇歇脚,凑凑热闹。“大姨娘”不论在忙什么,都会放下手头的活,招呼熟悉或不熟悉的客人,让他们喝上一口热茶。
“大姨娘”家的堂屋按常规只能坐八、九、十来个人,可常常拥挤着几十号。四个长条凳子经常“超载”,就连前后门的门槛上也挤着好几个人。人们拥在这里谈天说地,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传递着南来北往的信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电视,她家的天线喇叭就是人们认知世界,了解国家大事的“窗口”。乡亲们在谈笑声中消除忙碌困顿的疲劳,在风趣幽默的“段子”中享受着欢乐和愉悦。
“大姨娘”心地善良,为人亲和,人缘特好。活到80多岁,从没和乡邻们“拌过嘴”、“红过脸”。无论是村子里上了岁数的老人,还是一些害羞的姑娘和嫁过来的媳妇,谁有心里话、私房话,都会主动对她说,请她拿主意。但什么话到她那儿就到头了,她从不搬弄是非。谁家有困难,或者缺个什么的,她都会帮衬。在那吃饭靠“分口粮”的年代,“大姨娘”一家人勤劳节俭,加上人缘好,生活还算过得去。谁家没有“米”下锅,没有“油”炒菜,都会到她家里去“借”,村东头“二狗子”家没米下锅了,会到她家去借;村西头“小兔子”家没油炒菜了,也会到她家去借。讲信用的过几天就还,不讲信用的就“装呆”不还了,可她从不计较。有时候她从菜园里采回瓜果蔬菜,碰到家庭困难的、或没有妇女帮衬的男丁家庭,她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一把扁豆,几个辣椒、茄子,这些事习以为常。
“大姨娘”的家分明就是个“说事室”。每当家里有“贵客”(木匠、瓦匠、裁缝等)上门,到了中饭或晚饭的时候,房前屋后,常有“闹门子”的人端着饭碗边看“客人”们“喝酒吃菜”、“划拳行令”,边“嚷嚷着”家长里短。她看到孩子们碗里没菜了,免不了要挟块“鸡、鸭”什么的放在他们碗里。她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忙前忙后,做着这些无谓的没有一句怨言的琐事。在这里,可以听到邻村甚至邻乡的趣闻轶事。谁家姑娘要出嫁,哪家儿子30多岁了还没有对象,就连村东头谁家的咸肉被哪家的猫叼走了,在“大姨娘”家也能找到“线索”和“答案”。
“大姨娘”接济人“路子”广。因为得过她“接济”的人,有的招工进城当了工人,有的当兵提了干部,有的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当了一官半职。知道“大姨娘”人缘好,有路子,有“心计”的人就会抓住机遇托她说个人情,找“后门”办一些“难办”的事。比如“小光头”谈了个对象要结婚,姑娘提出要一台缝纫机,“大姨娘”就会放在心上,遇到“顶能”的人回来,就会主动说情要一张“缝纫机票”。人家看在“大姨娘”的情分上,真把事情办妥了。
“大姨娘”还是个“和事佬”。邻里闹纠纷,她一出面就能把事情平息。无论是不讲理的“三犟子”,还是遇到“夹食”(巢湖方言意为不大讲道理)的新媳妇,人人信服。她虽然没有文化,可她劝架说和讲道理,乡亲们都听她的;她虽不发脾气,可再淘气调皮的孩子都服她、听她的话;她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按乡邻们的话说“她的德行有目共睹”。她乐于助人,乐于奉献。她就是这个小村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稳定器”。邻家两口子“闹别扭”,只要她“上前”劝说,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快就没了“声音”。
数十年过去了,人们渐渐地把“大姨娘”的名字忘记了。可“大姨娘”是个“大好人”还常被人提起。我知道她的真名叫张永华,因为她是我的亲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