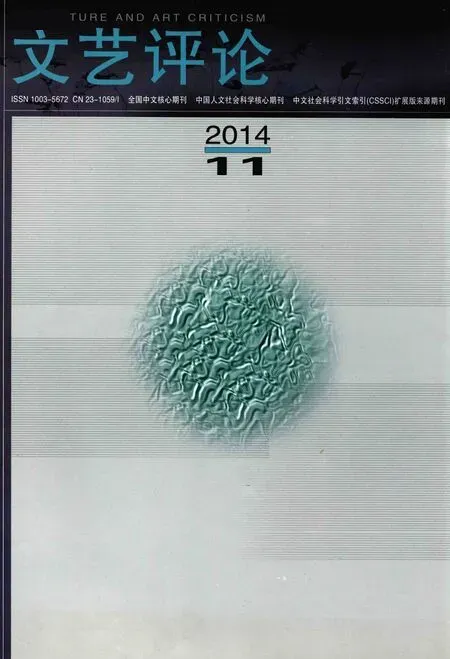从尼采到福柯:系谱学的知识谱系
○张守海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系谱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都促成了学界研究的范式革命和格局更新。系谱学最具颠覆性的一面在于,它质疑整个话语等级体系的理论霸权,解构一切看起来可以自圆其说的本质设定,并且通过一系列还原瓦解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追溯系谱学的学术渊源,福柯强调自己系谱学的灵感主要来自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张扬了一种完全区别于西方传统道德的全新思维,不把理性作为道德规范的基础,而是强调最自然的感情、欲望、心理甚至病理因素的作用,认为这些才是探索和揭示道德的根本出发点。《论道德的谱系》中的这些思想都对福柯有直接的启发,成为福柯的系谱学思想方法的重要源头和理论背景。在福柯的研究中,尼采提出的问题与其自身的思考进行了新一轮的整合,谱系的概念和运用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微妙的走向。
一、谱系的所指
法国著名学者吉尔·德勒兹曾经这样归纳系谱学的定义:“系谱学既指起源的价值,又指价值的起源。它既反对绝对价值,又不赞成相对主义或功利主义价值。系谱学意指价值的区分性因素,正是从这些因素中价值获得自身价值。因此,系谱学意味着起源或出身,同时又意味着起源时的差异或距离。它意指起源中的高贵与卑微、高贵与粗俗、高贵与颓废、高等与低等——这些是真正具有系谱学意义和批判意义的因素”。①福柯在考察尼采的谱系学概念的时候,在“出身”和“源起”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与德勒兹相似的判断,福柯认为尼采曾经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起源、来源、诞生等等词汇。福柯注意到《论道德的谱系》序言中使用“起源”时出现了微妙变化:“在尼采那里,我们发现对Ursprung(起源)一词有两种用法。第一种不加强调,而且它可以与其他术语例如Entstehung(出现)、Herkunft(出身),Abkunft(来源),Geburt(诞生)替换使用。例如在《道德谱系学》一书中,Entstehung或Ursprung都同样可以用来指义务或负罪感的起源;并且在《快乐的科学》中讨论逻辑和知识时,尼采对这两者的起源都不加区别地使用了Ursprung、ntstehung或者是Herkunft。②当尼采试图考察道德偏见的起源时,他用的是‘出身’这个独立的术语而并非以‘起源’来表达它的意思”。③福柯在这一能指的调整中领悟到尼采的用心:尼采希望可以明白准确地显示出他对‘出身’和‘源起’两个概念的有意区分。这种差别化的处理在一本提出“谱系学”命题的著作中显得意味深长。福柯没有同德勒兹一样在谱系学的意义上衡量“起源”和“出身”,而是敏感地发现这代表了尼采本人对本源观念稍嫌暧昧的立场——尼采对事物“本源”的执著,在某种程度上这昭示出尼采对个体权力意志和抽象主体性问题的关注。
这种对词意的敏锐的观察和体悟上的差异,让福柯的系谱学与尼采的谱系概念之间既存在关联,也出现分野。尼采的系谱学主要用来分析道德的起源,而且尼采本人依然保持对具有一致性的本源的强烈倾向性,尽管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用各种放肆的嘲笑和离经叛道的表述来彰显作者对于现世道德的僭越,并且这种思想观念的革命已经演化成深刻的颠覆,但是尼采依然对古希腊的悲剧精神保持着长久的好感,字里行间回荡着古希腊时代的英雄主义情怀;福柯把主要用于道德分析的系谱学处理成一种应用更为广泛的哲学方法,为各种事物重新建立关系图谱,相信系谱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主要运用于关系或者事件的考证,这种方法放弃了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深层的二元模式和常见的因果逻辑。与实证主义方法不同,福柯拒绝了社会事件的连续性、同一性的宏大叙事方式,试图从微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构成庞大复杂社会系统的每个局部环节,尤其是关注那些被历史长期遗忘了的、受到误解的、遭到社会排斥的、处于权力边缘的所谓话语。
在尼采的谱系学框架中,道德谱系方法通过追本溯源,区分了奴隶道德、教士道德、群畜道德和主人道德、高贵者道德等几种道德类型,完成了对欧洲社会道德谱系的梳理。在这种整体爬梳中尼采创造出一种谱系学的观念论,这就是后来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界定的一种乌托邦式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尼采的谱系是一种观念的虚构和人格的类型学,而且在尼采的研究中他只肯定一种希腊罗马的人格精神类型的首要地位,肯定这种人格类型在历史上的永恒轮回。在上述重点文献中,尼采表明他创建这一道德谱系的使命在于建立一种有别于基督教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并且以古希腊罗马的精神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张,提倡灵肉的完美结合。而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放弃了尼采的道理谱系这样一个预设好的起点以及先知的教导立场,另辟蹊径完成了一个审美的客观立场转换,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尼采常常把道德与社会制度建立在个体行为者的策略中,而福柯视一切主观意图动机为没有主体的策略性结果,不是其源泉,正是尼采对于起源的关注和出身问题的差别化处理,显露出系谱学作为历史分析方法的目的所在。
二、关于历史的认知
作为哲学家,福柯没有表现出对于史上大哲学家思想的迷恋,也不热衷讨论传统的哲学概念,而是关注考察疯癫、疾病、犯罪和性的历史。他从西方文化的微末处来审视考量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其权力关系,法国著名史学家韦纳称福柯为“纯粹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德吕兹称福柯为“一种哲学研究方式的开创者,这种研究方式本身是全新的,同时也复兴了历史学”。在尼采和福柯的学术视野中,历史都占有重要比重,但是在谱系确立的过程中两者则呈现出对本源的不同构想,这种差异进而彰显出研究者不同的历史观念和思考基点。
立足强调历史的意义与客观性的时代,尼采在历史研究中更坚持强调历史的“限度”。在历史研究中,尼采相信无论针对民族还是个体历史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要有分寸感,如果人们的历史感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伤害个人、民族,甚至整个文化体系,因此,历史书写的导向一定是具体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生活的客观性促成了“回忆”应有的底线和幅度。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序言中,尼采借歌德之言开门见山地指出历史作为奢侈品是必须痛恨的,并且将传统历史依据其作用划分为三种: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④
因此,在这样的整体认知层面下,尼采认为对于拥有行动力与斗争欲望的人,纪念的历史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有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务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⑤历史铭记苦难不断激励后来者,并且给予人们榜样、鼓励和安慰。正因如此,纪念的历史永远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必须将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并且通过史实的处理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怀古的历史对于保守和虔敬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通过怀旧问候当下,小心翼翼地保存各种时间的遗迹,为后人复制自己的生长条件。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大的价值在于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加进了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但是,问题同样会产生,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或精神都被摒弃。怀古的历史往往善于保存生活,而不懂如何创造生活,它阻碍了采取新行动的冲动,并麻痹行动者。人们在一种历史回归的狂热中产生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此产生了第三种方式,即批判的方式。批判的历史也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它审慎挑剔地评价过去,只是这个过程无疑是危险的,因为人作为历史的产物,携带着先天的历史错误所作出的历史判断也很难是科学的。尼采坚信:不管这种了解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的历史而取得,它们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因为我们总是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并称其为“客观”,其实这是对历史的创作。
针对尼采的这种历史观念,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强调:“我们将谱系学定义为对‘出身’和‘出现’进行的研究,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尼采经常把把谱系学看作是效果史(wirkliche Historie),在很多情况下他也将谱系学概括为历史‘精神’或‘历史感’。在他的研究中从《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二部分开始,尼采一直在批判引入超历史观的历史学,这种历史的作用是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些动荡;这种历史带着世界的终极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一些事物。这种历史学家的历史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妄称其判断的基础是一种预示世界终极(apocalyptic)的客观性。然而,这种历史却假定存在了永恒真理、灵魂不朽以及始终自我同一的意识。一旦历史感为一种超历史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而另一方面,如果历史感不承认这些绝对项是确定无疑的,它就规避了这种形而上学,从而就成了谱系学的特有工具。”⑥尼采指出来这种超历史的历史学的一切弊端都获得了福柯的共鸣,福柯由此构架了系谱学的根本要义,即并不是仅仅要为事物重新建立系谱,建构全新的历史,而是希望可以质疑打破一直以来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传统系谱,为事物重新定位,给予事物一个新的历史坐标。对一切历史传统和现实都加以考察,都提出质疑,在新的框架中理清历史修正误区,这是福柯系谱学视野中的历史观念的典型特征。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申明了自身历史观与传统历史观念的距离,他明确表示:“我为什么要写这祥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撰写一部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撰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从这些表述上不难看出福柯认为,现代的历史才是历史研究的要义所在。“当人们考察古典时期时人们只需要描述它。但是说到现代——始于1790-1810年延续到1950年问题则是如何从中解脱出来。这种明显的争议性质源出于这个事实:人们不得不挖掘脚下积累的大量话语……考古学家不得不像尼采主义哲学家一样拿起榔头来敲击它们”。⑦在这方面,作为尼采主义者的福柯认同尼采的观点——即历史就是“使过去服从现在和未来的需要”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传统的历史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历史是围绕着所谓的必然性的单线展开的。但是福柯认为,历史只是一个能提供复合元素的系统,每一元素都是复合的截然不同的,非常偶然的,不为任何综合的威力所统摄,所以,系谱学的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际历史,而不是超验的历史,不是历史学家虚构的历史,福柯认定的历史拒斥形而上学的“整体”,“同一”,“开端”,“发展”和“目的”这些历史的模式语言,反对总括历史,反对追溯历史的内在发展,反对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在此基础上,福柯反对所谓“历史连续性原则”,主张历史是“非连续事物的有组织的游戏”、“非连续事物的实践”,与传统历史观形成了天然的界限。
福柯的“系谱学”与尼采的“谱系学”有着相同的立场和大体一致的走向,福柯用“谱系”来代表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建立更为丰富的历史认知,并策略性地运用这一知识。系谱学的任务则是要关注局部的、间断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换言之“系谱学”要取消知识的等级制度,突出知识生产的偶然性,将那些处于边缘、被压迫状态的非法的知识解救出来,以获得与处于中心的强势知识一样的合法地位。在承继尼采谱系学的基础上,福柯对谱系学进行了发展,并赋予新的内蕴与研究的逻辑,从而使其成为一种负有盛名的研究方法。通过“系谱学”,福柯不断向人们揭示了他惊人的发现:整个西方的历史是偶然的,实际历史的领域仅仅是偶然和机遇,仅仅是不同权力/知识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