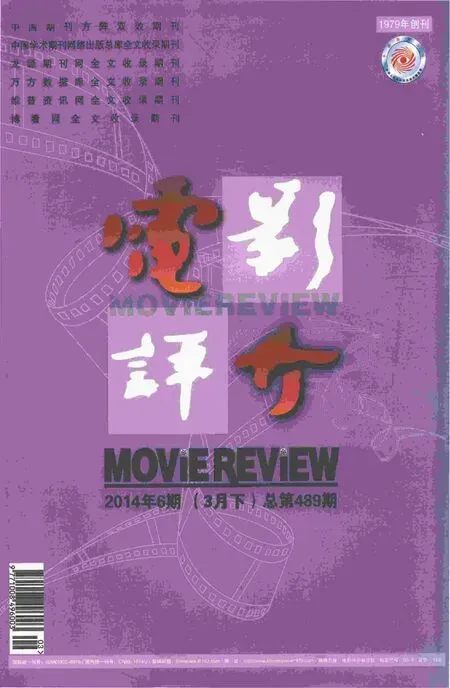漫画改编电影《美国队长》的媒介暴力分析
□文/叶 珲,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生

电影《美国队长2》剧照
一、媒介暴力的定义
从早期的研究来看,对于媒介暴力的定义广为采用的是格伯纳等人提出的“暴力是借助或不借助武器、诉诸于己或针对他人的身体力量的公开表达,是违背他人意愿、造成伤害或杀害的强制性行动。”[1](erbner,Gross,Jackson - Beeck,Jeffries -Fox,& Signorielli,1978,p.179)后来的媒介暴力内容研究,就是此基础上不断修正、拓展这一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媒介暴力可以从内容、机构、效果等多个维度进行界定,话语分析、符号学、媒介社会学等等都可以成为其研究路径,可以说媒介暴力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有学者对媒介暴力从媒介主体、媒介主体和媒介环境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将媒介暴力具体分为媒介化暴力、暴力化媒介、虚拟化暴力三个方面[2],在笔者看来更具有分析的可操作性。媒介化的暴力主要从内容暴力的方面考量,即“大众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是经由媒介筛选、制作并传播的暴力事件,是现实中的暴力行为被媒介转述和图景化了的暴力故事。由于媒介转述和图景化的过程往往会为了引人注目而凸现暴力的刺激性内容,所以可称之为‘媒介化的暴力’。”[3]暴力化的媒介属于形式暴力层面,即大众媒介利用其组织、技术和渠道上的传播强势,单向、集权地掌握社会话语权、诠释社会与社会现象、占用传播资源以宣传特定观点、价值。暴力化媒介的存在前提,是在传播媒介发展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后出现的。
虚拟化的暴力的概念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有同构性,也就是说,大众媒介运用暴力的传播手段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电影所建构的世界里,无论对于显性暴力的展示还是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隐性暴力的隐喻,都是通过对于特定语境下赋予暴力内容一定的合法性而展开,这样能消解受众对于暴力内容的不适感,从而达到通过暴力手段建构受众的目的。
二、《美国队长》电影个案分析
(一)漫画以及漫画改编电影内容框架分析
针对漫画的媒介暴力研究,早在50年代精神病专家沃瑟姆开始关注这种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一、漫画书的内容囊括了犯罪、暴力、恐怖和性,许多儿童都阅读了漫画书,那么,儿童必然会产生犯罪、暴力以及不正常的性行为等倾向;二、犯罪漫画书会改变儿童对世界的看法,大量的犯罪和暴力的内容会使儿童认为世界就是如此。这些结论描述最后被纳入了格伯纳涵化理论的框架内,是描述媒介暴力对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重要研究成果。好莱坞著名导演奈特·沙马南曾说,美国漫画永恒不变的公式就是“二元对立”。英雄与坏蛋、正义与邪恶,与好莱坞电影亘古不变的原则一样。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辩证性,是一种典型的利用自身的传播强势而施展的媒介话语暴力。
而美国漫画文化在当代最重要的一次转向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凭借日益先进的电影制作技术,好莱坞电影制作商不断地将经典超级英雄漫画搬上大银幕。漫画翻拍电影,不仅在美国文化产业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也为媒介暴力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课题。因为,电影是时空连续的艺术,而漫画是静止的艺术,虽然都是用画面来讲述故事,用镜头(漫画分镜)结构整体;但是漫画和电影的传播方式不太一样,漫画针对的是个体受众,因此反馈意见出现的时间和方式一般比较分散。电影是通过集体体验进行传播的,而且在现代的视听技术的冲击下,更加能混淆真实世界和拟态世界的区别,在心理上更容易形成“媒介等同效应”。在媒介效果上更容易产生葛伯纳等人提出的主流化(main streaming)的效果。可以说,在电影媒介下,媒介暴力对于受众影响将会更加直接和深远。
(二)《美国队长》个案分析
美国队长是美国两大漫画巨头之一漫威(Marvel)旗下的经典人物形象,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与超人齐名,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漫画人物。在先后几任美国队长中,最著名,最为读者所认同的是史蒂夫·罗杰斯,他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和美国梦的完美践行者。
1.美国队长的形象分析
美国队长身着源于美国国旗的蓝白红三色紧身战斗服,颜色鲜亮,手持号称世界上最坚硬金属亚德曼金锻造盾牌,身材健硕,身手敏捷,被称为“拥有人类体能极限的运动能力”,精通多种格斗术,且具有出色的战斗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他集合了积极向上、忠诚、善良、同情弱者、正义、富有爱国主义和人文主义情怀等优良品质。
从广义上说,美国队长的形象是一系列在电影(漫画)的语境带有所指意义的符号所构成的。按照约翰·菲斯克的说法,美国队长身上所有符号聚合而成一种“系统架构”(syntagma)。[4]——美国队长首先的是军人身份,其符号所指的是美国军队的代表;蓝白红三色紧身战斗服代表了美国国家意志;敏捷的身手、出众的格斗术代表了美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而一系列优秀的品质代表了美国深远的清教徒精神传统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尤其是美国队长的标志——他手里的盾牌,其材料本身就是极具杀伤潜力的金属材料,但是最终锻造成为盾牌,意指美国队长的防守型战斗原则。而无论是电影中还是漫画中,就是面对敌人的威胁,将自己的盾牌掷出击倒敌人。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视域内反复呈现各种“武器”图片,会强化被试的暴躁情绪和攻击行为。同时,国内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对“攻击性图片”的学习记忆使被试产生了“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的启动效应。在攻击图式处于激活状态下,个体更容易将交往对象知觉为具有攻击性,并相应的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动作。[5]所以,美国队长的盾牌只是符号学意义上“防御性质的正义暴力”的表征,在实际的媒介暴力内容展示中,其效果也可能是负面的。
如果结合电影里的语境进行交换检测的工作——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意志对应的是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共同敌人纳粹法西斯势力;盾牌对应的是在美国本土和全世界正义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正义的自卫反击;清教徒精神传统和自由民主的理念对应的是纳粹种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精神传统。因此,电影里特定历史语境的局限下,上述的编解码过程就赋予了合理的表意秩序。进而,依据这种语境下的符号编解码,美国队长的形象为电影中媒介暴力的实施赋予了合法性。
如果进一步对其形象进行政治诗学层面的分析,有人认为,美国队长其超人的力量并非来自血统,也非个人意志,而是科学技术——科技把他从自然的劣等人变成人工的超人。但科学技术并非与其灵魂不发生关系,其所承载的是二战中美国以科技和工业仲裁轴心国以实现世界正义的大叙事,其爱国主义的意志精神与国家共同体具有同构性,而美国队长的核心品质其实就是美国军队的集体意志,一种集体化、科技化了的意志生存论结构。美国队长除了身体素质和盾牌,其最大的特别之处也就在于他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淳朴的美国军人精神,对荣誉、集体、严肃、道德、牺牲的看重对于今天的美国军队来说,这些淳朴的老美国精神是具有神话性质的,而那块以保护为原则的盾,所代表着的一种更富道义与防御性的全球战略,也是今天美国所缺失的。在这一维度上对于美国队长的形象解构,体现出是电影媒介掌握媒介话语的符号暴力。
2.《美国队长》的电影叙事分析
易受影视暴力影响的青少年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对影视中故事情节的确信度高;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对实施暴力的所谓“英雄”角色高度认同。国内有研究表明,偏爱暴力节目的青少年对暴力赞成程度高于不喜爱暴力节目的青少年,而赞许度与认可度通常是暴力倾向形成的前提。[6]在笔者看来,这种赞许度与认可度的获得主要是源自受众对于其暴力行为的合法性认可而形成的。
在追求法治精神发达的美国,法律的程序正义是正常社会秩序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表征,但是物极必反,判例法系下的美国,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存在着客观上纵容事实犯罪的弊端。现实的司法体系神圣而不容侵犯,漫画和电影成为了民众心理的宣泄口,因此,一大批游走于司法体系边缘、用个人能力惩治罪犯,维护西方法理学意义上的“vigilante justice”的超级英雄形象应运而生。“媒体文化的文本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文化的恐惧和希望、梦想和梦魇,它因而是一种崭新的、重要的社会——心理洞见力的源泉,展示了特定时机中的受众的感受和想法。”[7]贾磊磊认为,电影中经过叙事逻辑“校正”后的暴力,正为观众的心理需求提供了一个正常的“出口”,使他们受到压抑的“心理冲动”通过电影中“故事化”的表述得到某种缓解。[8]
电影中,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在接受基因改造之前,是一个身材瘦小,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青年,屡次参军体检都没有获得通过。但是主持超级士兵血清项目的厄斯金博士认为他具有控制自己超级能力为正义事业所用的精神品质,遂私自篡改了体检报告,让罗杰斯得以参与超级士兵血清项目,最终赋予了罗杰斯实施暴力的能力,这是的“程序非法、结果正义”典型例子。同样,在影片中间部分,包括罗杰斯好友巴基在内的上百名美军士兵为敌军所俘虏,已经拥有上尉军衔的罗杰斯违反军令,只身潜入敌军后方基地,不仅成功将战友救出,还一举捣毁了重兵布防的敌军基地。
在这个过程中,在简单的善恶二元、行为正义等典型好莱坞叙事手法装饰下的暴力行为,成为宣泄观众的敌对情绪或满足他们的攻击欲望的“心理出口”,掩盖了以忠诚、富有集体主义觉悟著称的美国队长事实上违反了“军令如山”的现实世界的基本原则。在这种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价值判断和行为上能够简单有效解决问题的暴力行为渲染下,或许就会产生伯克维兹提出的“解禁暗示”效果,即暴力内容会产生解禁的作用,媒介展示出过多的暴力内容,会使人们对暴力无动于衷,会减弱人们对侵略性行为的抑止,从而更容易行使暴力。
伯克维兹在60年代提出“解禁暗示”效果其后续研究强调了侵略性产生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来自于内部的因素(如挫折或愤怒)和外部环境(合适的暗示)。与伯克维茨理论相似的,Anderson等人根据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在整合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既强调外部因素,又关注个体特征的一般攻击模型(GAM)。该模型强调,攻击行为的出现决定于个人内部变量(如敌意特质、对攻击行为的态度)和外部情境变量(如失败、挫折、暴力或激惹性事件和药物等)。[9]
在《美国队长》电影中,主人公的所有暴力性行为都“事出有因”,如德国间谍刺杀了掌握超级士兵血清核心技术的厄斯金博士、数百名战友被俘、亲密战友巴基在执行任务中殉职、面临敌军死亡威胁等等,这都符合上述侵略性行为产生的内外因。此外埋在“营救人质”这场戏之前,美国队长刚刚在对前线将士的慰问演出中受到了奚落,在叙事层面上也赋予了他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身价值的动因。
3.《美国队长》电影媒介暴力综述
电影的媒介化暴力是吸引受众的重要审美元素,《美国队长》中大量的打斗、战争场面是该类型电影最主要的美学表征,也是最重要的卖点。该类电影以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使得剧情变得十分易于预测,故事走向成为仅仅为了支撑描写展示暴力内容的大框架,因此,对剧情的理解和对矛盾复杂性的解读在这类电影的观看体验中被消解,因而将观众对暴力内容的观看最大化。
总结来说,《美国队长》中宣扬的是媒介暴力研究中典型的以“正义”形象进行的“合理化”暴力,在接受心理学上看,这种对暴力内容的展示和对暴力行为的前提建构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可接受的道德准则内,而且感官性的暴力刺激也充当了媒介作为“减压阀”的作用。尤其是超级英雄题材往往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正常的法律程序和国家暴力机构已经无法保护弱者,解决社会矛盾的情况下,超级英雄运用其超人类的能力保护了需要保护的群体。在美国,这一类与超级英雄暴力文本相关的案例不胜枚举,最近一次就是震惊世界的丹佛枪击案。
除了内容的暴力外,意识形态层面的形式暴力在《美国队长》的电影也有所表现。首先,在媒介话语表达上传递了这么一类价值,即美国是世界整体和平稳定不二的维护者,电影中美国队长的小队里集结了黑人、亚裔、东欧人、法国人等世界上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人,其中隐喻的就是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绝对领导者。其实在大多数好莱坞英雄题材、科幻题材类型片中,这类隐喻屡见不鲜。放眼全球该类影片生产情况,美国无疑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比例;而同时,这类影片又恰恰是电影产业中最为卖座的类型。美国正是通过本国领先于世界的电影技术和电影营销能力,掌握了在电影媒介上绝对统治性的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范围上的全球化,实现了美国的娱乐产业与美国的国家叙事的合谋。
[1]Gerbner,Gross,Jackson-Beeck,Jeffries-Fox&Signorielli:Cultural Indicators[M]Violence Profile No.9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28,1978:176-207.
[2][3]郝雨、王祎:《媒介暴力:类型、效应及控制》,[J]新闻记者,2009(9):15 -17,16.
[4](英)泰勒,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5]杨治良,刘素珍.“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1996(2):75 -78.
[6]王玲宁,张国良.媒介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J]青年研究,2005(3):32-40.
[7]徐明君.论暴力的媒介叙事逻辑与表达机制[J]电影文学,2008(1):31.
[8]贾磊磊.消解暴力——中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J].当代电影,2003(5):50.
[9]ANDERSON.A,BUSHMAN.J.Human aggression[J].Annu Rew Psychol,2002(1):27 -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