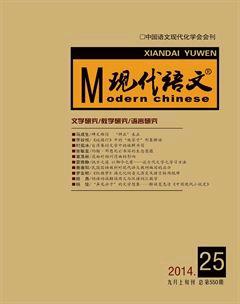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母亲”记忆
摘 要:以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物对“母亲”及母系传统的特殊崇拜之情,指出“母亲”或母系传统是维系黑人民族的脊梁。人物对“母亲”或母系传统的传承与爱慕是对黑人文化的崇拜,是对民族历史的恒久记忆。
关键词:黑人女性文学 黑人文化 母亲 记忆
一、引言
黑人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长远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其文学魅力更是突显出来,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黑色”力量。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更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朵骄阳。当代黑人女性作家用独特的笔调书写黑人民族发展的历史,其笔下的主人公大多为黑人女性,她们寻求自我﹑争取解放,捍卫着祖辈们传下来的黑人文化传统。这些黑人传统大多由“母亲”这一形象或人们对女性祖辈们的崇拜眷恋而一代代传递下来,因而“母亲”的形象与记忆不仅维系着黑人文化传统,也承载着对黑人民族历史的不能忘却之重。黑人女性文学的重要先驱人物,如托尼·莫里森﹑盖尔·琼斯﹑佐拉·尼尔·赫斯顿及艾丽斯·沃克,都致力于对黑人女性的描写刻画。她们作品里有饱受历史创伤的黑人母亲形象,如莫里森《乐园》(Paradise)[1]中的母亲和琼斯《考瑞基多拉》(Corregidora)[2]中的母亲;也有寻求解放并获得自由独立的“母亲”或女性形象,如赫斯顿《她们眼望上苍》中的珍妮及沃克《紫色》中的西丽。记忆中饱受创伤的“母亲”或追寻自由解放的“母亲”都是在传递黑人文化过程中承受着不能忘却历史的母系祖辈们,也是黑人女性作家在寻找母系文学遗产过程中对“母亲”的深刻认识。
二、记忆中饱受历史创伤的“母亲”
盖·杜格斯认为“正是由于母亲,通过母亲作为一种记忆的源泉,个体才被置于家庭谱系之中。”[3](P144)黑人群体通过母亲的记忆与叙述来了解民族历史,寻找民族归属感。母亲形象无疑对黑人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通过对母亲的情感记忆或母亲这一角色的扮演而建立与女性祖辈们的联系,并将自己置身于整个黑人民族谱系中。
作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先驱人物,莫里森和琼斯将黑人女性置于作品中的核心位置,女性形象(母亲形象)贯穿故事的始末。在她们笔下,黑人女性承受着双重的苦难——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即使身处于以白人为主导和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女性(母亲)依然积极地构建种族文化身份,寻找自我解放道路。莫里森《乐园》中的母亲和琼斯《考瑞基多拉》中的母亲都是饱受历史创伤的黑人母亲形象。从经受痛苦的肉体到饱受折磨的心灵﹑从种族歧视到性别压迫,莫里森和琼斯刻画出承载着历史记忆的黑人女性祖辈们的困境。这些“母亲”肩负着传承历史文化记忆的责任。
母亲是记忆的直接源泉,通过母亲,一个人才得以被置于家庭谱系之中。“母亲”(女性)这一形象常被置于过往的历史之中,也常被置于历史之外。小说《乐园》和《考瑞基多拉》中的两个家庭都经历着历史的创伤,这些创伤的故事通过母亲(女性)们的叙述而传递给后辈女儿们。通过叙述,母亲或女性承担着见证历史的责任,也突显出黑人女性这一特殊身份在构建民族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莫里森和琼斯分别描绘了一个讲述和传承家族历史的母亲(女性)形象。《乐园》中的帕特丽莎·贝斯特用文字记录着她的母亲(女性)祖辈们经历的历史创伤。帕特丽莎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这一职业给予她用文字重构家庭历史与黑人社区历史的能力。帕特丽莎并没有经历过经济剥夺与种族歧视的历史创伤,但对母亲的记忆使她产生了一股矛盾的情感——历史归属感和历史隔离感。在记录祖辈们故事的过程里,她似乎找到了内在的对黑人民族的认同意识,而对祖辈们的经历产生向往。然而,亲身经历的缺乏也使她对家庭的历史萌生一种疏远。这矛盾的情感形成了帕特丽莎特殊的家庭及社区身份。她成长在小镇上,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也是社区活动的参与者。她既是社区的一份子,又不能跨越社区的界限获得其他的认同感。琼斯的小说《考瑞基多拉》中的考瑞基多拉承担着“繁衍后代”的家庭责任,这一责任也是她保持对女性祖辈记忆﹑见证祖辈历史创伤的重要形式。詹妮弗·弗雷切纳所说“抱着孩子的母亲承载着她孩子的记忆。”[4](P2)考瑞基多拉希望通过母亲的角色来继承与传递祖辈们的记忆。对于生活在20世纪美国的考瑞基多拉来说,祖辈的历史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她迫切地想要记住那段历史,因而采取“繁衍后代”的形式。她认为“母亲”的角色是记忆历史最好的方式,希望自己可以通过“母亲”角色来感受祖辈的历史。《乐园》和《考瑞基多拉》中的女性都是创伤经历者的后代,她们记忆中的母性祖辈饱受着历史的伤痛,因而在讲述母亲或女性先辈们的故事时充斥着悲伤的情感。她们虽不能完全融入家庭的历史记忆里,却能很好地认识自己在家庭谱系中的重要性,而选择某种方式为自己和后辈们传承不可忘却的家庭历史记忆。女性祖辈经历的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在这些后辈们(考瑞基多拉和帕特丽莎)的传承过程里就是一个个饱受历史创伤的黑人女性记忆片段。
三、记忆中寻求自由解放的“母亲”
20世纪70年代的黑人女性作家在革新传统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展现出鲜明的写作特色。在她们笔下,黑人女性不再永远依附黑人男性。面对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她们中的一些人虽有痛苦与迷茫,却敢于进行反抗并在反抗的过程里寻找到沉默已久的声音与独立的人格,最终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她们是黑人女性作家笔下寻求自由解放的母亲(女性)形象代表,是对漫长的黑人历史长河中敢于斗争﹑敢于寻求自我的母亲(女性)祖辈们的历史记忆,也是黑人历史文化里的新“母亲”形象。
赫斯顿是黑人文学史上第一个以黑人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家,在作品里大胆地表达黑人女性寻求自我﹑争取解放的思想。她的先河之举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建构了基本框架。沃克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黑人女性文学创作遗产,其作品也大多以黑人女性为主,她们争取自我解放,是黑人女性对女性祖辈们的崇拜表现。
赫斯顿的《她们眼望上苍》中的珍妮和沃克《紫色》中的西丽就是这样的女性代表。珍妮从小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外祖母是典型的在男权社会中饱受创伤的黑人妇女。她向珍妮灌输黑人妇女等于奴隶的概念:“黑人妇女就是世界上的骡子。”[5](P29)这种古老守旧的观念阻碍着珍妮的自我寻找道路。贝索指出,“外祖母南妮忠实地屈服于男权统治,又将其受伤的心理作为遗产传给珍妮,这充分显示出男权社会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具有可悲的连续性。”[6](P176)外祖母的“奴隶”思想使珍妮步入了不幸的婚姻。她将珍妮嫁给拥有较多地产的老男人罗根,她认为那会给珍妮提供安全与保护。珍妮的第一次婚姻与她寻求浪漫爱情的本能不相符。在步入婚姻前的一天,珍妮偶然地观察着一颗盛开着花朵的梨树,她“看到每个花瓣,每个细小的枝叶都狂喜得震颤。这就是婚姻。她仿佛得到了神明的启示”[5](P24)。她觉得婚姻应像梨花般美好甜蜜,但她的婚姻却与理想相去甚远。心怀着梨花般的美好爱情,珍妮勇敢地摆脱男权代表人物——老男人罗根,满心期待地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然而,珍妮还是没能如愿地到达心中理想的地平线。她被束缚在家里,成为男权丈夫奴役的对象。身为镇长夫人,她却没有任何话语权,丈夫甚至公开宣布“我的妻子不会演讲。我不是因为这个娶她的。她是个女人,她的位置在家庭里。”[5](P46)珍妮只是一件有价值的装饰品。压抑的婚姻让珍妮感到不满,她反抗着,“纵有千种情感,纵有万条思绪,她从不向他诉说。她将它们存放在内心深处,一个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她同时扮演两个人:一个内‘我,一个外‘我,而且从不混淆。”[6](P113)内心对美好爱情与婚姻的渴望愈加激励着她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镇长丈夫死后,珍妮大胆地嫁给了农民茶点。在第三次婚姻里,珍妮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梨花般美好的爱情。茶点带给珍妮从未有过的快乐与幸福。他和她下棋﹑带她钓鱼﹑看棒球赛﹑教她射击。她做着一切男人能做的事情,甚至做得还要好。茶点待人的平等态度让珍妮感受到人的尊严。茶点虽一无所有,但却让珍妮找到内心期盼的美好爱情。她们的婚姻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成功挑战,她获得了精神的自由。赫斯顿对这样一个敢于反抗而寻求自我的黑人女性的着墨也是对黑人历史上寻求独立与解放的女性祖辈们的赞美。她们是黑人记忆中寻求自由的勇敢母亲(女性)形象。endprint
沃克继承并发展了赫斯顿的文学传统,其代表作《紫色》就如同《她们眼望上苍》的姐妹篇。《紫色》中的西丽也经历着从麻木到觉醒﹑从反抗男权到实现自我价值艰辛的自由之路,西丽是新一代黑人女性的代表人物。
最初的西丽是一个传统的黑人女性,她被继父强奸,遭受百般凌辱。继父对她感到厌倦后,就把她嫁给了某某先生,而这个丈夫只是为从她继父那得到一头母牛和一个可以照看孩子的保姆。西丽默默地忍受着,从不反抗,内心的痛楚只能通过向上帝写信来倾诉。她“让自己像一块木头一样”[7](P2)活着,麻木地尽着妻子和继母的义务。直到莎格的出现,处于绝望里的西丽才开始有了改变的机会。莎格是一个布鲁斯歌手,自由独立,事业的成功使她享受着各种“特权”。她的女性独立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西丽,西丽渴望自己能像莎格一样漂亮﹑一样能唱歌﹑一样能做想做的事情。莎格不但保护着西丽免受某某先生的欺负,还唤醒了她的性意识,西丽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帮助西丽摆脱男人的暴力,改变西丽的世界观,激励她寻求人格的独立与自我价值。西丽慢慢地意识到给上帝写信是毫无意义的,于是转而写信给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耐蒂。她还勇敢地与莎格一起去北方生活,维护自己做人的权益。西丽的离开和事业的成功是她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标志,是自立自强的开端。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才能,创立了大众裤子公司,为人们做起了裤子。小说结尾,西丽带着莎格参观房间,“房间里除了地板外,所有的东西都是紫色的和红色的”[7](P191)。西丽的世界不再只有黑色,而是多彩的颜色,这是快乐与幸福的颜色,是西丽对人生的自信。
西丽的自我解放也改变着周围的人。小说结尾,某某先生认识到自己的封建男权思想﹑认识到西丽作为“母亲”(家庭女性)的伟大。他开始与西丽坐在一起谈话,还接受西丽的各种想法。他主动地反思﹑和社区的人一起帮助他人治病。后来某某先生送给西丽一只自己雕刻的紫色青蛙,也认可了西丽的人格魅力和价值。转变后的他们建立着平等的关系,西丽亲切地叫他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也静静地陪着西丽等待耐蒂的归来。
西丽这一“母亲”(女性)角色是沃克在寻找母亲的花园过程中对母亲形象的描绘与记忆。获得新生的西丽是小说里的母亲形象,也是现实中黑人女性对“母亲”或女性祖辈的深刻记忆。她们是黑人后辈记忆中敢于寻求自由、争取解放的“母亲”们。
四、结语
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对母系文学遗产的重视体现在其创作过程里。作品中的“母亲”(女性)形象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她们继承和发展着女性祖辈们的文化传统,也革新着古老守旧的观念。儿女后代们正是通过对母亲的记忆而认清家庭历史和传递历史文化遗产。黑人女性作家以黑人妇女为核心人物进行创作是对母系文学遗产的寻找与回归,也是对黑人历史上母系祖辈们的深刻记忆。
注释:
[1]Toni,Morrison.Paradise,New York:Knopf,1998.
[2]Gayl,Jones.Corregidora,Boston:Beacon,1975.
[3]Guy,Dugas.La Litterature judeo-maghrebine dexpression fransaise:entre D jeha et Cagayous,Paris:LHarmattan,1991.
[4]Jennifer,Fleischner.Mastering Slavery:Memory, Family,and Identity in Womens Slave Narrative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
[5]Hurston,Zora Neale.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8.
[6]Bethel,Lorraine. Zora Neale Hurston and the Black Female Literary Tradition,New York:Feminist Press, 1982.
[7]Walker,Alice.The Color Purple,New York:Harcourt, 1982.
(刘青 广东广州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51054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