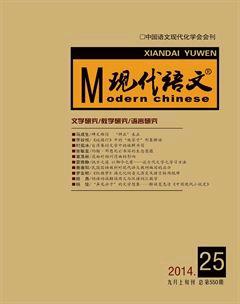台湾眷村文学中的族群书写
摘 要:族群关系是台湾无法回避的一个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生存的眷村文学亦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族群关系的变迁对台湾外省眷村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眷村作家的族群书写和族群意识建构体现了他们的族群自觉意识。
关键词:台湾族群关系 眷村文学 族群书写 族群意识建构
眷村文学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有着特殊的地域指向性,学界一般认为以眷村为主要叙述对象,或以眷村为叙述背景或涉及到眷村的人、事、物及感思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列为眷村文学。眷村文学是台湾族群关系背景下的产物,长期以来,眷村文学的发展受到台湾族群关系的深刻影响,同样,眷村作家的族群书写也催生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发展变化。
一、战后台湾族群关系的发展演变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最早由西方提出,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展开对族群的研究。对“族群”的定义,历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美国学者马丁·N.麦格综合了西方学界的多种解释,归纳了一个结论:“基本上来说,族群是一种次级社会群体,它具有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共享传统的群体归属感、群体成员中的族群优越感、所属群体的成员资格,甚至拥有特定的领域为基础。”[1]但同时他也指出:“现在一般被称作族群的群体在以前被认为是种族(race)或民族(nation),但是这几个术语在意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2]20世纪50年代,台湾民族学界引用“族群”一词并初用于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到了70年代后期,这一概念不再是民族学界的使用专利,“族群”一词开始被台湾学界广泛使用。而后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动荡,族群理论开始为一些政客所利用为区分社会群体的工具,族群的概念内涵失去了确指性,开始泛化,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成为台湾社会最主要的议题之一。
台湾的族群关系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台湾的政治格局变迁密不可分。战前,台湾社会的族群关系表现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战后,随着“外省”人群的到来却使得台湾社会的族群关系出现复杂化:“不仅有基于血缘、文化等关系的‘族的区分(如汉族和高山族之分别),而且有缘于其它因素的‘群的组合(如汉族内部的再划分)”[3],族群之说无形中把台湾人群划分了几个阶层,从而也导致了省籍矛盾的出现。所谓“省籍矛盾”,是指1945年以前移居台湾的“本省人”同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外省人”之间的矛盾。这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形成所谓“支配者常常为外省人、而台湾人处于被支配的现象”[4]。在族群术语中,这种现象叫做“移民上位”,即移民群体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优势地位。对于台湾本土人来说,痛苦的战争年代才刚刚过去,和平的果实就被外来人口接替,这难以避免地造成了台湾社会的省籍隔阂。
到了70—80年代,台湾的省籍矛盾开始加剧。一系列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中美关系解冻,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等,使台湾民众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反攻之梦”破灭,民众怨声载道,国民党台湾政权遭受沉重打击。随后1980-1986年间,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反对运动”,“党外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为了缓和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蒋经国时期意图“通过大量吸纳‘本省人加入国民党等‘亲民方式以缓和社会矛盾和扩大国民党在台湾民众中的基础,这类缓解‘省籍矛盾的措施虽然使国民党政权渡过了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内外交困危机,但是也开启了国民党的所谓‘本土化过程。”[5]
20世纪90年代末,本土上位,“外省人”群体从过去的中心地位转向边缘化。民进党在1989年提出了‘台湾的四大族群概念,即“原住民族群、闽南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之说。至此,省籍矛盾形成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四大族群是‘省籍矛盾的人为放大和在汉、原族际关系基础上的扩展”[6],是“台湾政治多元化和汉族群体在‘差异政治条件下的‘省籍分化”[7],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族群而是为政党服务的政治族群。
为了应对民进党的强硬措施,国民党提出了之于族群关系的一个新论述——“新本土”,“新本土”之于过去的“本土”论述不仅同样强调族群融合,同时还强调对台湾的地缘认同和社会认同。有论者指出“这是马英九与民进党进行本土诠释权争夺的重要举措,也是国民党对台湾主体意识重新建构的重要支点。同年10月,国民党在修改党章时将台湾写入党章,并宣示以台湾为主,对台湾有利的基本信念。2008年马英九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这一信念,并将其作为施政原则。”[8]“新本土”政策同样是国民党为了缓和族群矛盾所做的一个新举措,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台湾社会的复杂情况和对立党派的多般阻挠,无论国民党在族群论述上怎样努力,直至目前,台湾的族群关系仍然呈现着互相攻讦、混乱异常的局面,并且这种现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一直持续。
二、“眷村”作家的族群书写
台湾族群关系不仅摆弄着台湾的政治、社会环境。在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股风暴,岛内族群关系格局的变迁对台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的创作心态,尤其是眷村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眷村是国民党对来台军官及其眷属的安置区,除少数嫁进来的本省媳妇以外,村子里几乎都是外省人,作为为外省族群代言的眷村作家成为一批敏锐并极有生命力的创作队伍,剧本编剧方面有侯孝贤、朱天文,散文有苏伟贞、苦苓,小说方面更为突出,张大春、朱天心、张启疆、郝誉翔、袁琼琼、苏伟贞、骆以军等都是优秀的眷村小说家。
在族际冲突加剧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眷村作家多写眷村的风土人情,年少记事等等。正如朱双一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眷村小说因展现了特有的‘眷村文化而获得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在当时,它们主要是一些成长于眷村的女作家的感性之作,并没有族群关系问题的严峻背景,或者说作家并非有意识地想通过作品表现某种有关族群的意识形态。”[9]然而随着族群关系的加剧,眷村作家写作发生了变化,作品中的族群意识和反思意识加强。他们审视过去,明辨眷村同政治集团的关系,同时关注未来,思考本族群的生存前景。虽然眷村作家的创作各具特色,但因为相似的身份背景,他们在族群书写方面呈现出一些共同的主题。endprint
(一)族群偏见和歧视
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委婉含蓄,关于“省籍隔阂”的描述或多或少都会在眷村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究其原因是族群背景使然。这种因省籍不同的族群偏见最明显地表现在身份歧视上,许多眷村作品对此都有所揭露,如苏伟贞的《沉默之岛》、郝誉翔的《逆旅》、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张启疆《君自他乡来》等。在《沉默之岛》中,苏伟贞对女主人公晨勉心理的描述其实是对自己省籍情结最真实的刻画:“她想念她的岛。她第一次发觉,新的歧视观点,歧视你是歧视你的籍贯,而不是出生,更不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10],类似的论述还可见于郝誉翔的《逆旅》:“ 直到今天,别人问起我的籍贯,我照旧会说山东,这当然是一种顽固、无可救药,而且最糟糕的是非常‘不正确的省籍情结。”[11]在这里,山东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地域象征,而是一种政治符号,本省人与外省人因为族群身份不同而相互排斥,尤其是外省人常常受到外界的误解和偏见。
因为族群偏见导致的婚姻、爱情的不幸也是眷村作家常常表达的一个主题。在《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中,惠理对丈夫的埋怨是朱天心对外省人爱情婚姻受阻现象很好的影射:“好比惠理,女中时也曾跟着他读了很多翻译小说,对他似乎事事景从,近几年电话中话题贫乏地老是抱怨她丈夫‘他们外省人……,惠理当初因为父母的反对外省人,恋爱的过程极痛苦。”[12]再如郝誉翔的《逆旅》,作品记述了父亲多次失败的婚姻,这种婚姻的不幸固然和父亲的天性有莫大关系,但追根到底,实也是“漂泊者”身份的真实写照。
(二)身份认同的危机
这些眷村作家们,或生在大陆,长在台湾;或生在台湾,长在眷村。他们鲜有对大陆的记忆,但是又不被台湾这个社会所认可。他们是无根的一代,既不是纯粹的大陆人,也不能把台湾称作是故乡,他们是无根的一代。在他们身上,普遍遭遇着身份认同的危机。
对身世身份的追寻化作满腔郁结并诉诸于笔尖,是眷村作家们心灵得以暂时排遣的一个港湾。郝誉翔在《逆旅》中无奈地感慨道:“他们不但被毕生的信仰所放逐,又被台湾这块岛屿所放逐,然后在本土论述越来越强势的今天,历史就预备这样子悄悄地把他们遗忘了。”[13]这里的他们,虽是指作为外省第一代的父辈们,但其实也是眷村作家们等外省第二代心境的写照。同样是外省第二代的苏伟贞,在《沉默之岛》中也借晨勉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是哪一种文化认同呢?她没有反驳,她自己这些年早已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了,不是台湾省或山东省;就像香港人,你问他是哪里人,他就是香港人,他不说广东人。”[14]再如《古都》中,朱天心委屈地控诉:“你从未试图整理过这种感觉,你也不敢对任何人说,尤其在这动不动老有人要检查你们爱不爱这里,甚至要你们不喜欢这里的就要走快走的时候。要走快走,或滚回哪哪哪,仿佛你们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可住,只是死皮赖脸不去似的。”[15]
(三)家族书写与历史记忆
几乎所有眷村作家都有着这样共同的历史记忆:那就是听父辈们诉说过去,诉说对大陆的记忆、诉说自己的身世经历。在这样的诉说与聆听过程中,虽谈不上感同身受的内在交流,但父辈们那种对故乡深切的思念,对坎坷身世的无奈,却是每一个眷村作家都难以忘怀的。陆续的,一些眷村作家开始着手家族书写,如张大春的《聆听父亲》、郝誉翔的《逆旅》、朱天心的《漫游者》、张启疆的《君自故乡来》、苏伟贞的《老爸关云短》、骆以军的《月球姓氏》,他们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安顿那些因此漂泊无所归依的灵魂”[16]。就像《逆旅》中郝誉翔父亲所说的那样“当年怎么想得到,一离开就是几十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7]父辈们从未遗忘过去,因此,和郝誉翔一样,眷村作家们“站在一个边缘又边缘的位置”,为父辈代言,开始了家族书写的起点。
三、“眷村”作家的族群意识建构
正如为家族书写一样,眷村作家的族群意识随着族群关系的日益紧张而日渐觉醒,他们突破了“写眷村”的牢笼并树立了“我为眷村写”、“我为族群写”的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眷村作家们不仅个人自觉意识增强,而且主动承担起族群文化重构的重任。
在重构族群文化的过程中,眷村作家主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面对外部族群冲突的大环境,眷村作家与本土“福佬沙文主义”展开了抗争。“福佬沙文主义”,或称“闽南沙文主义”、“福佬中心主义”,概括来说就是:“台湾人即福佬人,台湾话即福佬话”[18]。这是一种过分、不正确、极端的爱国主义,是一部分闽南人激进势力妄图构建“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阴谋。同是本省人的“客家”、“原住民”族群因为不符合其政治规则也被排挤在了边缘之外,眷村作家和众客家、原住民作家一道,秉承着建构族群文化的立场,为保留本族群语言、文化和历史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抗争的同时,眷村作家也在努力召唤集体认同,建构族群历史。马丁·N.麦格指出族群有五个主要特征:①独特的文化特征②领地③族群中心主义或族群优越感④与生俱来的成员品格⑤社群意识。因为台湾政治环境的变迁,外省族群渐趋成为弱势族群,有些外省人甚至不愿承认自己的族群身份,从前的族群优越感也转变成自卑意识。再加上眷村的陨落,先前地标性的领地范围也已不复存在,外省族群失去了可以依附的族群生活环境,族群文化日渐式微。眷村作家在致力于族群文化的建设中,努力唤醒族群认知,凝聚社群意识。“一个群体之所以成为一个族群,并不是由于它可以被测量的或被观察到的区别于其他族群的差异程度,相反,这是因为在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族群;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们的语言、感觉和行为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19]为了挽救这个独立的群体,眷村作家开始了寻“根”之旅。
进行文化抗争仅能够为族群文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要真正使族群文化繁荣起来,还需要重塑族群文化。在这一方面,外省第二代作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是文学刊物的开拓,在1977年,朱天文、朱天心两姐妹和其他一些外省成员创立了《三三集刊》,随后又成立了与《三三集刊》有着共同“正统中国”信仰的“三三书坊”,呼吁用“情”、“爱”的理想包纳国家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等争议。《三三集刊》的创刊和“三三书坊”的成立,使外省作家有了可以交流思想、诠释族群文化的园地。二是对眷村作家的扶植。苏伟贞编选的《台湾眷村小说选》收录了朱天心、朱天文、孙玮芒、苦苓等眷村作家的作品,使这些优秀的眷村作品得以更广泛地传扬。除了苏伟贞,还有许多眷村人士通过各种方式表现了对眷村文学的支持,如侯孝贤和朱天文合作电影,各种眷村名人访谈等。三是重塑族群文化,致力于族群文化的搜集保存工作。随着眷村的拆迁重建,关于眷村的记忆也将随着篱笆院落的消失而慢慢在人们脑海中淡化,眷村文化濒临着消亡的危险,眷村作家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或书写回忆文章,如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孙玮芒的《回首故园,眷村生活素描》;或以族群的语言为工具,记录本族群的历史记忆,很多山东籍作家在这方面非常突出,作品中不时穿插着独具特色的山东方言,张大春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无论是“鸡鸡歪歪”、“狗屁倒灶”、“我他妈”式的诙谐脏话,还是“不赖呆”、“光子”、“闹俚戏”之类的山东土话,都被他运用得收放自如,他无意于玩弄语言游戏,只是为了祭奠那远去的故土情结。同样身为山东籍作家的郝誉翔,虽没有张大春来的激烈,却多了一份深情,在她为父代言的《逆旅》中,舅舅见到郝福祯的开场白从来都是“你他奶奶个小兔崽子,你他奶奶的懂啥东西?”[20]“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小杂种啊”[21],这个在书中出现了五次的开场白,是舅舅含泪含愤的哭诉,虽带着些山东话的粗鲁,确是人性最真的声音。眷村作家用笔写历史,用言说历史,他们用自己的鲜明特色,诠释族群文化,为族群正名。
虽然族群关系是台湾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在台独势力的操纵下,族群关系在不断地变质、异化,但是与之抗争的力量一直存在。不仅在文化领域外省作家、眷村作家的族群认同意识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在政治领域,一批坚决的反台独、反分裂的政治人士也在不断地进行政治诉求,和平协商。而且在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在渴望早日统一的共同呼声中,冲突和对抗不会一直存在,合作和融合将是族群关系新的特征。
注释:
[1][2][19][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第9页,第10页。
[3][9]朱双一:《从老兵悲歌到眷村史乘——有关族群关系的一个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3期。
[4][18]施正锋:《族群政治与政策》,台湾: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第27页。
[5][6][7]郝时远,陈建樾主编:《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第272页。
[8]陈星,相靖:《“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性解析》,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4期。
[10][14]苏伟贞:《沉默之岛》,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1][13][16][17][20][21]郝誉翔:《逆旅》,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57页,第157-158页,第156-157页,第5页,第51页,第58页。
[12][15]朱天心:《古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第149页。
(时茹冰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