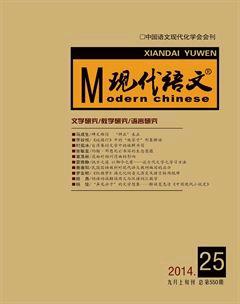论老舍对邪恶人物的书写
摘 要:有感于现实社会普遍的道德失范风气,老舍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塑造出欧阳天风、小赵等一批邪恶人物。对“恶”的书写和对“恶”的摧毁不仅彰显出老舍爱憎分明的道德判断,更承载着老舍拯救国民灵魂的社会使命感。
关键词:老舍 邪恶人物 道德失范 救世热忱
不似张爱玲“参差的对照”的美学观念,老舍的创作常常带有明显的道德倾向性。他主要以道德去度量人物,善与恶的对比和一胜一败,是老舍创作基本的人物组合结构。本文旨在考察老舍笔下的邪恶人物,从其“恶”态着手,试图理清这些问题:老舍书写邪恶人物的缘由何在?他们是如何被塑造的?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作家怎样的道德判断和创作态度?
一、“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
老舍笔下的邪恶人物皆是一副新式打扮,混迹于学界或官场,然而品行恶劣,毫无道德可言。他们或是《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或是《离婚》中的小赵,或是《骆驼祥子》里的阮明。欧阳天风外表俊俏,内心却肮脏不堪。他为取悦赵子曰这位“财神爷”,极尽谄媚之能事,待卑贱如车夫者流,则凶相毕露。表面为赵子曰走上仕途引介入会,暗中私吞筹款反倒打一耙;表面为赵王二人搭桥牵线,实则胁迫王女士为其赚钱。《离婚》中的小赵更是下流龌龊,机关算尽。他以取笑捉弄他人为乐趣,凡不入“法眼”者皆除之而后快。小赵爱钱,为此他可以买卖妇女,敲诈勒索;小赵嗜权,他时刻窥探着财政所的职务调动,随时准备利用自己的裙带关系升官进爵;小赵好色,女人是专等着他“瞧”的,“他作梦的时候,女子全是裸体的。”《骆驼祥子》中的阮明读书时想拿和教员的交往换得及格分数,事与愿违便出卖老师。作官后立刻抛却先前的激进思想,融入了恶劣社会,去嫖,去赌,甚至吸鸦片。钱不够用时又组织洋车夫宣传革命,出卖思想。可以说,无论是混迹学界的欧阳天风,还是身居官场的小赵或阮明,钱、权、名,乃是他们一致膜拜的图腾崇拜,至于道德良知云云,皆弃之如履。
虽然老舍对这些邪恶人物的塑造不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想象,但人物身上所呈现的道德失范并非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通过决绝的“重估一切价值”宣判了陈旧道德的死刑。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们高喊“打倒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口号下,五四“新青年”们纷纷走出“家”,奔向“十字街头”摇旗呐喊,几乎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作为“局外人”的老舍却为这场“道德革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祛魅”化处理。他以“反五四”的姿态,解构着现代“学生”形象。例如小说《赵子曰》以“五四”退潮期为背景,塑造了几个混沌于世的学生形象,他们除了学问,吃喝玩乐无一不精,其中既有赵子曰这样的纨绔子弟,也有欧阳天风这样的流氓无赖。接受新思想洗礼的青年学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痛苦挣扎在生死存亡线上的普通民众。在老舍看来,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等美好的道德新名词,都是值得反思批判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素质并没有因为这场伦理道德革命而提升,相反,旧的道德规范被破坏,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这实际形成了一种暂时的道德真空状态。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连同本土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乘虚而入,恶人恶行肆无忌惮,与前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灵魂”缺失、道德沦丧,仍是民众普遍的精神状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洪流此起彼伏。当救亡压过启蒙,这种道德失范的状态并未解除,反而愈演愈烈。老舍发表于1941年2月1日的演讲稿《灵的文学与佛教》写道:
大家都着重于做人,然而着重于做人的人,却有很多简直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叫他吃点儿亏都不肯,专门想讨便宜,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中国社会的每阶层,无不充满了这种气氛。
正是这“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的气氛凝聚成小赵等邪恶人物的魂魄。老舍说自己“因为穷,所以作事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1]现实穷困抹去了青年老舍身上朝气蓬勃的明快色彩,而过早染上了中年人的沉郁心态,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更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深有体悟。所以,老舍对邪恶人物想象书写的背后正指涉着现实社会中普遍的道德失范风气,它是孕育小赵等人胚胎的土壤和助其成长的温房。
二、“使人物从纸上跳出,而永存于读者的记忆中”
小说毕竟不是现实,如何将笔下的人物写得惟妙惟肖,从艺术形象中生发对现实的深切感悟,有赖于作家高超的艺术手法。老舍从“恶”这一特性出发,塑造了欧阳、小赵、阮明这样的邪恶人物,他们基本上属于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作出来。”[2]他们容易辨认和记忆,但缺乏深刻性。对于这批肤浅卑鄙、没有“灵魂”的邪恶人物,以漫画式的讽刺笔调刻画是再适合不过了。但老舍并不局限于此,他在写作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一套人物描写方法,把这些缺乏性格深度的人物也能写得鲜明、贴切、活泼,“使人物从纸上跳出,而永存于读者的记忆中。”[3]
《赵子曰》是老舍的早期作品,艺术上还没有完全成熟,对欧阳天风基本上都是侧面描写,难免略显单薄。但欧阳的俊美外表和卑劣灵魂的强烈对比,两副面孔(趋炎附势的谄媚态和咒骂持刀的凶恶相)的适时转换,使这一恶人形象深入人心。到了《离婚》,老舍的艺术手法臻于完满,人物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塑造小赵这个流氓无赖型人物的:首先,老舍以叙述者的口吻一一道出小赵的三个特点以求大致印象:消息通、有特权,看女人。接着便以夸张讽刺的笔法绘出一张小赵像:
赵科员的长相与举动,和白听戏的红票差不多,有实际上的用处,而没有分毫的价值。因此,耳目口鼻都没有一定地位的必要,事实上,他说话的时节五官也确随便挪动位置。眼珠象俩炒豆似的,满脸上蹦。笑的时候,小尖下巴能和脑门挨上。
小赵的相貌可谓特色十足:有实用而无价值,五官可以随便挪动位置,尤其是一双眼珠,“俩炒豆似的,满脸上蹦”,更是抓住了小赵的面部特征,为他贴上一个专属“标签”,其油滑奸诈之态简直呼之欲出。有了对小赵的印象式轮廓后,还需“随时的用动作表现出他来。每个动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现出他一点来,他便越来越活泼,越实在。”[4]耍弄李太太饭局出丑、请客老李探听虚实、买卖失手狗急跳墙、敲诈财物诱骗秀真、怂恿“方墩”衙门闹事……老舍将小赵置于种种事件,以行动逐渐丰富形象,使其“恶”态一步步暴露。前面的篇章从侧面刻画小赵,到了行文至半处则将小赵从大背景中抽离,放置前台进行了正面亮相,并且在叙述中展现出人物的一系列内心活动。老舍没有把小赵处理成一个干瘪的符号,在突出其“恶”的同时,也写出“人”的一面。由此可见,老舍刻画人物不似中国工笔画之繁琐细致,亦不取西方油画之浓墨重彩,他先以写意之笔勾勒出大致轮廓,再着以浅淡颜色,而后随手点染,使个性充实。这便是他刻画人物的绝妙处。所以,即便是作为反面人物刻画的小赵,老舍也没有将他简单化、脸谱化,而力求生动形象。endprint
阮明在《骆驼祥子》中只是作为背景人物出现,所以用墨极少,行文至半时,我们才从叙述人口中知道阮明的身份。但老舍却在强烈的对比及反讽中使这一“恶人”形象深入人心。首先对阮明中场悬置式的空白处理和结尾众星拱月般的烘托出场,使读者产生强烈的突然性刺激。其次,众人狂欢观望的期待与阮明平淡无奇的现身使“看客”和读者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对“小矮个儿”、“病猴”似的阮明印象深刻。而阮明以出卖始、以被出卖终的结局无疑构成对人物的最大反讽。所以,尽管老舍对阮明着墨不多,却在一幕幕出其不意的场景中,使“出卖者”阮明的形象在人们脑海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三、“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毋庸置疑,老舍对小赵等人嘲弄讽刺的笔调中渗透着作者强烈的道德批判。但问题在于,作家塑造这批邪恶人物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正义人物与之相抗衡。“欧阳天风——李景纯”、“小赵——丁二爷”、“阮明——曹先生”,无疑构成了小说文本中正/邪(善/恶)的二元对立。无论这些邪恶人物之前如何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其结局往往被引向毁灭,正义和良善终将取得胜利。欧阳天风的虚伪面孔被层层撕破,李景纯的殉国之举唤回了赵子曰们沉睡的良知;丁二爷从一个无用的食客型人物化身民间侠士,杀死小赵,除暴安良;阮明以出卖始,以被出卖终,逃不出游街枪毙的命运,而曹先生的温情成为祥子灰暗人生的一抹亮色。也就是说,老舍并不是为写恶而写恶,他写恶是为了以善劝恶或惩恶扬善。从艺术手法上看,“恶”的每一次蠢蠢欲动,都是主人公陷入生命低谷的征兆,推动情节一次次进入高潮,同时正义与邪恶的交锋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或许我们可以说,老舍以邪不压正的大团圆结局充当残酷现实的安慰剂,继而推出老舍思想的天真和平庸自然顺理成章。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老舍创作中的社会使命感和救世热忱。这一方面是对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的承继,更多则来自老舍的宗教情怀。
1922年夏,老舍在北京缸瓦市伦敦基督教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是“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世界。鲁迅为放青年们去“宽阔光明的地方”,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老舍也说,“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需要“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一样的有毒的文化,我们需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5]面对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国民的道德素质日益堕落。老舍痛感:
中国文学作品里没有一部写劝善改恶的东西,很多的书本里,虽也有些写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字眼,但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灵的文字。(《灵的文学与佛教》)
“灵”即指和“肉体”相对的灵魂,对“灵”的要求即是对良心、道德的要求。显然,老舍试图以“灵”的生活对抗“恶”的人心,而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灵的文字”正承担着这样的启蒙工作。鲁迅以文化医者的姿态,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层层肌理,最终发出“掀掉这人肉的筵席”的振聋发聩之声!茅盾则以社会科学家的姿态,从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为错综复杂的中国弊病寻求良方。老舍始终是一个心灵关照者,透视着人的灵魂,正因痛感民众的“善恶不辨”、“是非不分”,他渴望以强烈的道德力量阻击险恶,拯救社会。其作品中对邪恶人物“被毁灭”的结局书写正秉持着这一信念。尽管老舍把当时社会的堕落和黑暗归结为道德败坏、人心不古没有抓住真正根源,但他的忧患意识和道义承担理应被充分理解。“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义,使老舍宁愿暂时牺牲文艺,而成全一种宗教担当精神。
老舍对宗教的理解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天职感,“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物的义务进行评价。”[6]“上帝应允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他的天职。”[7]从这一意义上说,老舍正是将文艺作为他的“天职”,鞭挞丑恶、歌赞良善,“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8]
现实社会的道德失范触发老舍塑造出欧阳天风、小赵等一批邪恶人物,“以善胜恶”的宗教情怀又促使老舍塑造出李景纯、丁二爷等一批正义人物与之抗衡。所以,对“恶”的书写和对“恶”的摧毁,不仅彰显出老舍爱憎分明的道德判断,更承载着老舍重建民族道德的社会使命感和救世热忱。
注释:
[1]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2]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3][4]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第243-244页。
[5]老舍:《双十》,《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6][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9页。
[8]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页。
(潘晶晶 江苏扬州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2)endprint